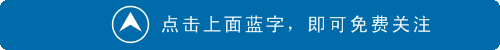

“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这是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的描述,当时曾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谁偷走了中国人的信任感?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到了一个段子。说是在如今的中国,卖包子的不吃自己做的包子,种菜不吃自己种的菜,卖药的不敢吃自己生产的药,卖奶粉则从不吃国产的奶粉......
这个段子本身就很好地从一个侧面回答了我的这个问题。当造假作假、坑蒙拐骗成为一种风气,甚至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时尚,每个人能做的就只剩两件事了。一个是只相信自己,另一个是绝不相信别人。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被患上了欺骗恐惧症,他们从小就被无数次教训告诫,不要跟陌生人说话,而现实又强化了这个版本的判断。从前天灾多人祸少,现在天灾不少人祸则更多,每个人都不愿意轻易将信任赠送给别人。连回家过年,长辈们也不免一概地会唠叨上一句,“出门在外可得长点心”。
“快递来了不敢开门,查水表的不让进屋,入户人口普查不得不改成去居委会报到......”这些被拿来当做是信任感缺失的推举案例,在我看来,不过是群情汹涌的现世社会里普通人正常而基本的自我保护罢了。
更可怕的不信任,在于群体心理的巨大分裂:官民之间,人们不信辟谣,偏信传谣;商民之间,不信国货,一味青睐洋品牌;家长不信任老师,患者不信任医生,观光客不信任店家……
悲催!人们遇到事情,遇到人,总是将质疑放置在信任前面之时,而这根本不正常。但说到谁应该对此负责,公平来讲这是整个社会的共同失败。每个人都该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巨大透支负责。官方的监督缺位,民众价值观的异化,客观上都起到了为社会的负面与病态“添砖加瓦”的作用。
想起那句充满正能量的网络名言:“你所站立的便是你的中国,你怎样,中国便怎样。”这话当然不完全对,但我们可以以此为鉴的是,应该放弃那种“一切假丑恶都是体制的错”的公知思维怪圈。修补社会信任的裂缝,需要民众调整心态,用善心、平常心看待外部世界。当然,更需要有关部门承担起自身的责任,通过法律和制度手段规范社会秩序与道德,重建社会的公平与信任。
附:中国人的信任从未超出过家庭范畴(深度思考)

经济学家阿罗曾经这样断言,世界上很多经济落后可以通过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而在中国社会中,社会中间组织一直处于缺位状态。中国社会的信任依然停留在家族信任阶段。
1、没有信任,就没有社会秩序
社会学家齐美尔说:“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现代生活远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诚实的信任之上。”
信任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之所以能发挥这一功能,是因为信任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增加行为的确定性又是通过信任在习俗与互惠性合作中扮演的角色来完成的。信任早已成为人格中的重要品德而进入习俗,而习俗不仅在成长期塑造着人格,并且在其后,靠着对违约和失信者施加的社会压力,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2、中国社会依然是“低度信任社会”
信任产生于社会中间组织。社会中间组织是政治权威之外的社会力量建立的群体或组织,在社会结构中承担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创造一个健全的社会,光靠国家机器和公民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自由集合的“群”很可能将于人类共始终。
在这方面,美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按照日裔美国学者弗郎西斯·福山的说法,美国有着双重的文化遗产:个人主义与社区主义。美国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社会,美国人非常喜欢社交,是对他人信任程度很高的民族,建立了极其发达的民间组织。
福山敏锐地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人是反中央集权主义者,但是那些同样是反中央集权主义的美国人却自愿服从各种中间社会团体的权威,包括家庭、教会、本地社区、工作场所、工会和专业组织等,他们是社团主义的支持者。”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具有高度自发的社群倾向的社会,普遍地存在高度的社会信任,因而可以建立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在这种组织中,非血亲人员可以轻轻松松地为着共同的经济目标合作。美国的个人主义与社团主义互相促进和制约,共同塑造着美国的文明。
在中国社会中,社会中间组织一直处于缺位状态。中国社会的信任依然停留在家族信任阶段。
几千年来,儒家文明虽然一直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低度信任社会”。在这套文化观念中,没有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而只有严格的等级秩序。由于没有彼岸的“信仰”和此岸的“契约”,其结果便是一种奇特的“二律背反”——表面上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质上整个帝国都是一盘散沙;表面上家庭成为社会纽带的核心,实际上信任从来也没有超出过家庭范畴之外。
由于信任只是局限于家庭之中,使得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来与陌生人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信任”——这不仅对经济的良性运行造成了显著的伤害,也在很大程度上伤害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3、信任一旦打碎,恢复起来难上加难
简化复杂,是人类从生存中进化出的战略。而人类社会中的信任,则具体承担着简化复杂的功能。
总体而言,信任可以分为三类:人格信任、货币信任、专家信任。人格信任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信任,在原始时代,在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圈子比较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信任,基本上都是人格信任。那时候挑选合作伙伴,挑选的都是某个人,而不是某个角色、某个分数、某个大学毕业的。某人我知根知底,这就意味着他是可信赖的。这种类型的信任,叫做人格信任。
随着生活圈子的扩大,当我们走出了血缘和熟人的圈子之后,就不再能够找到所信赖的人保护我们,和我们交换,和我们合作。我们走到了陌生的圈子里,在很大程度上告别了熟人,但是还需要合作,还需要交换,因为社会生活就是建立在社会交换的基础上的。这时候人们就只好寻找建立另外一种社会信任机制,其中之一是货币。
当你拿着货币的时候,这地方你谁也不认识,不要紧,你可以靠你的钞票来住店,靠你的钞票来坐船、坐车、坐飞机,都不会有问题。货币信任的结构是从众,即货币(尤其是纸币)在流通过程中已被证明是可行的,通过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检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第三种信任机制是专家系统。当“熟人”当中没有能帮你解决特定问题的人时,就需要求助于“专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生病了,就要找一个好大夫去看。找谁看?你说不清楚,不认识人,更不认识这样的大夫。那怎么办呢?你会找一个好医院,找这家医院里一个大牌医生,教授级大夫,主治医生,挂一个14块钱的号,这样你就会觉得心里踏实了。这就是专家信任。
人格、货币、专家,这样三个系统支撑着我们社会中的全部信任。而目前中国发生的信任危机,就是在这三个系统里,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正如上文提到的,同发达社会中的系统信任相比,我们社会的系统信任还远不完善。我们在更大程度上还必须依赖人格信任,熟人间的信任仍是我们社会赖以立足的基石。从“杀熟”成为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现象开始,我们赖以存在的最基础的信任结构开始瓦解。“杀熟”标志着不仅在陌生人中缺乏信任,而且熟人中的信任也日益丧失,意味着社会信任降到了最低点。
福山认为,一个社会当中的信任,是该社会数千年文明的结果,所造就了有些社会的成员信任度比较高,有些社会的成员之间信任度稍低一些,但是每个社会都享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这个是几千年文明的产物。但是当社会一旦把它打碎,要想恢复的话难乎其难,甚至要以“代”为单位才能得以转变。
本文摘编自《信任论》;来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