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马建标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到了1917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进行了将近三周年。这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不仅把协约国和同盟国的国力消耗殆尽,而且还为远东地区的新兴国家日本提供了向中国扩张的宝贵良机。自1914年一战爆发以来,日本已经确立了其在东亚地区的实际霸权地位。日本这种东亚霸主地位的获得,是通过武力和外交的双重手段来获取的:1914年8月日本对德宣战,击败驻守青岛的德军,实现对青岛的军事统治;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在同年5月逼迫袁世凯政府签署了《民四条约》,确立了日本在中国对外关系上的特殊地位。随着1916年6月袁世凯的去世,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继任国务总理,并逐渐形成了以段祺瑞为核心的军阀政治集团,史称“皖系”。
1917年7月张勋复辟,段祺瑞出兵北京,由于“再造共和”之功而继续担任国务总理。这一年,不仅是中国政局动荡,世界局势也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同年初,德国宣布无限制潜水艇战,导致德美关系恶化,最终促使美国参战。沙皇俄国也因战争致使民不聊生,导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环视全球,唯有日本国强民富,成为一战的最大获利者。但是,日本的东亚霸主地位仍然不牢固,故而它仍需通过条约的方式来获得欧美列强的认可。1917年春,日本利用英法两国的战争困难,与英法两国签署秘密协定,成功地获得英法两国对日本东亚霸权地位的支持。同年11月,日本又与美国签署《蓝辛-石井协定》,争取美国承认了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利益”。按照日本的理解,这个“特殊利益”是指日本在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蓝辛-石井协定》的签署也向中国领导人释放了一个可怕的信号:那就是美国已经抛弃了中国!于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所控制的北京政府,采取了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即联合日本。日本政府也有意扶持段祺瑞政权,通过“西原借款”来武装段祺瑞的“参战军”,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中国政策。但是,皖系军阀的强大引发了北洋集团的另一派势力,也就是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的担忧。到了1918年春,直皖两系的矛盾因皖系军阀主导的中日军事结盟计划而再次爆发。
北洋系的分裂与皖系“联日”
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率军进入北京,总计不满半个月的张勋复辟,由此宣告闭幕。随之,中国政治格局发生新的变化。两位北洋系的首领冯国璋、段祺瑞分别出任北京政府总统和总理。冯国璋以副总统资格而取得总统位置以及段祺瑞的再起,被时人称为“一场大骗局”。因为,前总统黎元洪是受直隶籍贯军人的骗而罢免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从而“替冯国璋造成取得总统位置的机会”;张勋是受段祺瑞属下的欺骗而冒然复辟,从而“替段氏造成恢复政权的机会”。 张勋失败之后,发表通电说:“已获巨罪,人庆大勋,恨当世无直道,怨民国鲜公刑。” 这弦外之音,透露出张勋自知落入段祺瑞圈套之后的无奈与愤恨之情。
在复辟未宣告时,研究系已与段派联合一气。段氏在马厂誓师时,梁启超已入其幕府,除发表反对张勋复辟电外,还“亲入段军,直接参赞其事”。 研究系另一要人汤化龙则随同段祺瑞入京。7月17日,段祺瑞组阁,其阁员名单如下: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外交汪大燮、内务汤化龙、财政梁启超、司法林长民、农商张国淦、教育范源濂、交通曹汝霖、海军刘冠雄。这些阁员中,属于研究系的是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此外范源濂、汪大燮、张国淦等人都与研究系亲近。曹汝霖是新交通系的首领,政治上依附于段祺瑞,而海军总长刘冠雄也属于段派。 所以,此届内阁是段派军阀与研究系、新交通系的联合内阁。
冯国璋虽然得以就任大总统,但是他无法插手段内阁。在拟定阁员名单时,冯国璋原本反对刘冠雄和曹汝霖入阁,但为段祺瑞拒绝。1917年7月13日,张君劢致书梁启超,告知:“此次内阁名单,河间极不以刘冠雄长海军为然,于润田则云此人于国内舆论中颇有非之者,以此列阁员中,总嫌不漂亮。” 河间,即冯国璋;润田,指曹汝霖。黎元洪任总统时,因参战问题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冲突,是为“府院之争”。现在,冯国璋与段祺瑞依然不和,两人“关系始终未融洽”。 黎元洪在段氏到京后,因段氏的劝诱,由东交民巷外国公使馆区域回居私宅,通电宣告“此后不再与闻政事,推冯副总统继任大总统”。 然而,段祺瑞内心并不满意冯氏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在7月8日发出冯国璋以“副座代行总统职权”的电文之后,故意拖延此项电报由北京到达南京的时间,于7月13日才到达南京的冯国璋手中。此时,南下敦请冯国璋北上的张君劢埋怨说:“近来北方来电较少,而日期又多,凡非加急电必待三日或五日后方到”,因此,“河间颇以合肥不受商量”。 合肥,即段祺瑞。
南京是冯国璋的老巢,冯不想因为北上就任总统而将江苏地盘让与他人。长江流域是冯国璋的势力范围,尤以江苏省为重心所在。此时,传说段祺瑞亲信倪嗣冲将担任江苏督军,引起冯国璋的担忧。冯遂命心腹干将、江西督军李纯出面反对。李氏在九江演说复辟源流,将张勋与倪嗣冲“并为一谈”,除派遣重军到南京之外,尚在九江驻扎一师,表示对倪的示威运动。 所以,冯国璋一面谦让,请黎元洪复职,一面暗中与段祺瑞接洽江苏督军的后继人选。最后,冯国璋如愿以偿,调江西督军李纯为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与湖北督军王占元联结为一,合称“长江三督”,构成直系在长江流域的基本势力范围。于是,冯国璋于1917年8月1日到京任职,冯段之争的序幕也由此开启。
段祺瑞新政府成立之日,也是中国南北分裂之始。研究系是造成此次南北分裂的始作俑者。当时,段祺瑞新政府面临两个最紧要的问题是,“对外的参战问题和对内的国会改造问题”。国会改造问题是由参战问题而引起。旧国会分子多对段不满意,现在,段祺瑞要巩固其统治地位,必须解决国会问题。这时,研究系要人梁启超向段祺瑞献策,召集临时参议院以改造旧国会,置旧国会法统于不顾。孙中山因此率领海军南下广东,组织军政府,竖起护法大旗,中国南北由此形成对立局面。

段祺瑞
梁启超改造旧国会的主张,完全是政治考虑,丝毫没有顾及法律的尊严。7月21日,《申报》记者访问梁启超,谈论国会问题。梁说,“对于国会主张,恢复之不能,改选之不可,而以召集临时参院为比较的无上上策”。至于旧国会不能恢复的理由,梁列出两条:第一是旧国会为各省督军所破坏,一旦恢复,必然得罪各省督军,所谓“政治上将生莫大之反动”;第二即使督军同意恢复旧国会,也无法确保督军“一改从前之态度”,不再破坏国会。质言之,这两条理由仍然是政治考虑。梁自己也承认召集临时参议院,不过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他说:“盖以严格之法律言,则改选亦无根据,而又不能去国会组织不改之弊,如是之国会,再过三年,国家不能危险乎?至于召集临时参议院,有改良组织之利,而约法上亦可以勉强比附,似此三者之中可行而比较有利者,莫此若也。” 临时参议院,从法理上本属自相矛盾。李剑农批评说,旧国会自“第一次灭亡(指袁世凯复辟帝制,取消旧国会)恢复之后,为何不照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偏要恢复已经满了期限的旧国会?若说前此恢复旧国会是因为袁氏的解散国会不合法,黎氏的解散国会又岂合法么?这是纯就他们所持的理论而言”。 旧国会中也有研究系议员,但是研究系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惜联合段祺瑞否定他们的合法存在——旧国会,借以制服敌党,实为超越政治常规的举动。
7月24日,北京国务院通电各省,征求对于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据说,这份文电是梁启超的手笔。这封通电,先是说明恢复旧国会为不可能,并援引唐继尧督军的“破甑之喻”,说明旧国会威信已失,最后特别引用陆荣廷改组国会的主张,申论“非先有临时参议院不可”。 然而,社会舆论对于梁启超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极端主张,深以为异,批评梁氏因“一部分之利益与感情,置国家根本法于不顾”。 后来,段祺瑞依梁启超计,改组旧国会,成立新国会。新国会实际由安福系王揖唐所控制,因此又称安福国会,研究系被边缘化。研究系被皖系所抛弃,遂与亲近皖系的安福系、旧交通系成为政敌。正如李剑农所言:“故在研究系召集临时参议院的主张,是因为要贯彻改造国会的目的,与煽动督军团干宪的目的前后是一致的,谁知这个问题是一具不能开的死锁。后来国会虽然被他们在北方强迫改造了,却又被安福系所盘踞;安福系的骄横恶劣,竟超过他们所目为暴徒的无数倍;而南方又始终不承认他们的改造,遂演成长时期的纷争惨剧。”
南北对峙局面形成后,北方的冯段因统一问题发生分歧。总统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总理段祺瑞坚持武力征南,双方各执一端,势同水火。1917年底,段祺瑞在川湘方面用兵失败,武力征南政策遭到非议。同年11月17日,直系督军曹锟、王占元、李纯、陈光远等联名通电,主张与西南和平解决,并声明愿作调人。 据此消息,时在北京政府陆军部任职的徐永昌判断,“段内阁将倒,南北似有调停之机”。11月20日,总统冯国璋准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以汪大燮暂代国务总理。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几位研究系阁员也随段氏去职,段内阁瓦解。12月1日,冯国璋任命直隶籍同乡王士珍为国务总理。王士珍也是主和派,颇赞成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这就是冯段之争的第一幕。冯段之争直接导致北洋系内部的分裂,而无兵无权的研究系既然已经被段派所排斥,现在也与冯派貌合神离,实际处于一种不尴不尬的第三方境地。
在此期间,南方也是四分五裂。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诸人对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颇不满意。从1917年9月到1918年春,西南军阀一直在酝酿改组军政府。至1918年4月后旬,军政府改组形势成熟。5月4日,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务,离粤赴沪;同日,孙中山发布《辞大元帅职通电》,极为痛心地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在北方直皖两系的斗争中,日本站在皖系一边,压制和打击直系,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对南方发动战争的一系列作法,又得到了日本的支持。1918年2月3日,徐树铮致电各省督军,指出:“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芝揆(指段祺瑞)去职,彼邦时相问询,称以各省不挽留为疑。……寺内已训令渠系内有力诸要人,并达林公使谓段虽暂时去职,北系实力并无堕落,此后对支方针,仍认定东海、合肥为政局之中心,遇事力尽友谊援助等语。” 3月20日,西原龟三奉日本政府之命访问段祺瑞,力促段祺瑞出山组阁,西原说:“阁下既已握有兵力,只需掌握权力,倘若财力不足,本人可设法资助。如欲为日中友好奠基,舍今日又待何时,切勿失此千载难遇之良机,毅然拟定计划,出任总理。” 与此同时,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也会见大总统冯国璋,表示日本政府对北方政局的态度,劝告北洋各派应团结一致,解决政局纠纷。 在此期间,徐树铮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联络,引奉军入关,进驻直隶。 一则声援皖系,一则威逼冯氏。3月19日,段派督军又发出一道联名威胁的通电,要求段祺瑞组阁。
在这内外压力之下,冯国璋不得不与段祺瑞暂时妥协。1918年3月23日,王士珍辞职,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这是段祺瑞第三次组阁。段祺瑞此次成功组阁,日本和奉系是其外援,而其内援则是皖系将领以及曹汝霖为首的新交通系。曹汝霖在段祺瑞内阁中身兼交通总长和财政总长两个“肥缺”,这实在令被排斥出局的梁启超的研究系人士艳羡不已。故而,洞悉时局内幕的北洋军人徐永昌说:“今日名流自知无分,故梁(启超)著书,汤(化龙)出洋,此所谓灰心丧气。”
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之后,为继续推行其武力征南计划,立即与日本联络,秘密进行中日军事协定交涉。既然皖系段祺瑞以日本为靠山,那么直系冯国璋势必寻求英美的支持,双方都在借助外力。冯国璋的心腹爱将、江苏督军李纯是典型的亲美派,冯的亲美深受其影响。早在1917年12月12日,李纯在给冯国璋的密函中,建议“应与英、美相互提携”,以便借助英美之力抵制日本。 李纯与英美人士交往向来密切,他手下的顾问和秘书人员,几乎全是受美式教育者,李与美国人时常往来。所以,当时上海竟有舆论认为,李纯的态度“完全为美国人所左右”。 因此,冯段之争的结果,最终促使皖系与直系各寻外援,加剧北洋派内争的国际化。
中日军事结盟及其被泄密
皖系军阀与日本政府进行中日军事协定交涉(当时报纸称之为“中日新交涉”,以别于1915年的二十一条交涉),是互取所需。日本希望通过中日“同盟”的方式进一步巩固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而皖系则希望利用日本提供的军事援助,推行其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
拉拢皖系军阀,日本蓄谋已久。早在1917年11月14日,皖系干将靳云鹏、曲同丰前往日本参观日本陆军大演习时,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西原龟三等人即向靳、曲二人游说,提议中日“有必要加强日中军事合作,以防止德国势力东侵”。 1918年2月1日,田中义一致电坂西利八郎,指示坂西与段祺瑞接洽军事同盟事项。 次日,坂西回电报告,他已经和参战督办段祺瑞及陆军总长段芝贵“寻求某种机会以个人名义向章公使极力陈述军事协同的必要性,并让他(章)向大总统冯国璋报告。这正是不拘泥于形式的做法”,但是,“敝人已与段祺瑞、段芝贵等人已经拟定大体计划”。 2月5日,田中义一向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议,中日两国应迅速谋取“军事上的共同行动,防止德国势力东渐,维持东亚和平”。 2月14日国务会议上,外交总长陆征祥陈述了俄国远东局势以及德奥势力东渐的情况,说明此际中国方面为了自卫,需加强边境的警备,尤其是东三省的警备要更加完善。陆征祥认为“中日协同合作”是必要的,全体阁员没有什么异议。王士珍总理决定与冯国璋总统熟商“中日军事结盟问题”。 2月16日,国务会议继续对西伯利亚防卫及中日结盟问题进行讨论,仍没有达成具体意见。随后,陆征祥等人亲自访问段祺瑞,征询段的意见。段说:“此问题很紧急,不容耽误。此问题是外交总长专管事项,因此你(陆征祥)应作为主要责任人,促成中日达成军事协定”。
随后,坂西利八郎、青木宣纯等日本顾问分别向冯国璋、王士珍疏通。2月19日,青木宣纯拜访冯国璋,探询冯氏对于中日军事结盟的意见,冯表示“他从内心非常赞成,特别是在今日中国国内混乱之际,一旦与外国发生冲突时,中国能够依赖的唯有日本”。 2月22日,冯国璋对坂西说,“参战督办决不仅仅是为了出兵法国而设立的,是为了参战而发生国际性军事事件而设立的。至于中日应否结盟,完全是政府的事情,而不是段祺瑞参战督办一个人的事情”,据此,坂西认为“现在,从表面上看,冯段两派相互倾轧,日甚一日,几近破裂”。 日方和段派不断地向冯国璋施加压力。冯氏无可奈何,但他提出一条反建议,即把中日军事合作限制在中国国境之外,以搪塞日本的催逼。2月22日,北京政府致电驻日公使章宗祥,指出:“今日馆迭派员探询对于俄边境紧急情形,中国是否愿与日提携,共同干涉;青木中将并谒见主座。经面告以华境内事,中国自行处理;华境外事宜,可与日本共同处理。”

冯国璋
由于冯国璋及王士珍的拖延,中日军事协定交涉进展缓慢。在此期间,中国北方政局发生变化。3月23日,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之后,中日军事协定交涉进入新阶段。此前一日,经段祺瑞授意,北京政府参谋总长荫昌等人将精心准备的《预筹中日联合出兵防俄条拟》呈报大总统冯国璋,以“俄国内乱,影响东亚,德、奥俘虏,又复东侵”为由,提议中国“与日本联合出兵共同防俄”。 3月25日,驻日公使章宗祥致函日本外相本野一郎,按照日本条件提出中日共同防敌要求:“中国政府鉴于目下时局,依左列纲领与贵国政府协同处置,信为贵我两国之必要。茲依本国政府之训令,特行贵国政府提议,本使深为荣幸。”有关具体条件,由中日双方指定的军事委员讨论议定。换文后,日本即通过坂西将日方拟定的草案交给靳云鹏,双方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修正。
然而,就在中日军事协定谈判刚刚展开之际,其内幕就被泄露出去,直接导致中国留日学生发起反对中日军事结盟的抗议运动。根据日方要求,谈判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在交涉过程中,其内幕仍不时为中外报刊所揭露。3月22日,京津《泰晤士报》以《日本对华劝告》为题,透露了中日共同防敌换文的内容。 3月26日,上海《大陆报》也发布类似报道。 4月2日,研究系喉舌《晨钟报》刊文呼吁国人注意日本“对我之重要新交涉”。 4月23日,上海37个商民团体以及全国商会联合会纷纷通电,表示反对。
此项谈判内容的泄密,显然是有人故意为之。中日军事协定谈判是在冯、段之争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所以皖系方面认为总统冯国璋是此次中日新交涉被泄密的罪魁祸首。 5月16日,中日正式签署《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5月19日又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在段派看来,中日军事协定的签署,也有万不得已的隐衷。5月17日,徐树铮密电段祺瑞,指出:“今与东邦幸缔此约,为嘉为怨,即难断言,而关联较深,则无疑义。盼其嘉,则必极意经营以希惠助。虑其怨,亦必小心翼翼以遏怒锋。”
5月19日,北京《大中华日报》头版刊登陆军军事协定全文,除文字稍加改动外,与原协定文本雷同,次日北京《中华新报》、《国是报》、《国民公报》等报刊纷纷转载。5月20日,中日陆军军事协定交涉中方委员长靳云鹏向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斋藤季治郎透露,“此系总统府所为,无法追究”。 5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致电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告知“中方陆军军事协商委员会中有总统府冯国璋的代表”,判断冯国璋在陆军军事协商委员会的代表可能是《陆军军事协定》被泄露的渠道。
此时,在华英美报纸也参与进来,敦促段祺瑞政府早日公布中日军事交涉内容。5月6日,上海美国侨民的喉舌《大陆报》评论说:“大众对于中日新交涉之疑团,政府今始觉悟,然无悔祸之心。昨日阁议讨论应否公布全案,结果全体主张目前政府不应信任公众。而各方面之电信迭来询问政府交涉之内容与手续。” 5月11日,《大陆报》又批评说:“京中舆论对于此事实不甘心,磋商详情,外间茫然。所知者,有一种概况之合同,内容必与一九一五年第五款相同。” 5月22日,上海英国人的《字林西报》发表社论,指出,“华人对于中日所有磋商每信其将不利于中国,然而今次磋商之情节,实亦发生同样之恶感想。其故有三:磋商之开始有军人而不经外交部;出兵西比利亚,无论如何必要,而磋商之严密不泄,实令人不得不疑也;二十一条要求之往事,人犹忆之”。
中日军事协定交涉被泄露,不过是冯、段之争的一个征兆。作为主和派,冯国璋当然反对段祺瑞与日本实现军事结盟。但是,冯国璋并不希望与段祺瑞彻底决裂。所以,冯氏对于外界反对中日军事交涉的声音,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防止与段派的矛盾激化。当时,社会各界纷纷致电总统冯国璋,要求宣布中日交涉内幕。5月25日,社会名流张謇由南通致电冯国璋、段祺瑞,“请宣布外交,以释群疑”。 冯国璋在给张謇的回电中,说:“共同出兵条件互有利益,谣传殊不足信,稍缓自当宣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段祺瑞内阁决定,“新外交案决不宣布”。 在这种情况下,冯段之间的分歧逐渐大白于天下。
自1917年下半年护法战争兴起后,北方冯国璋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已经滋生,遂有直皖分派之说。当时,徐树铮为顾全北洋系大局,曾向段祺瑞“详陈数次”,劝其与冯派谋和。 此次中日军事协定交涉发生,冯段分歧再次彰显,徐树铮又致电段祺瑞,力主与冯妥协。5月23日,徐树铮致电段祺瑞,详陈直皖分裂之利害关系:“直人布置直派,是直之自杀直人。若皖人布置皖派,以为抵直之计,是皖之自杀皖人。直人果自成派,是自外于国家也。为总理计者,能消而弭之,诚属至善。”徐树铮这封电报,劝服了段祺瑞。5月31日,段祺瑞亲自到总统府,谒见冯国璋,“面陈新交涉经过情形”。 段此举意在向冯妥协,冯氏乃“始复原状”,重新开始办理公事。
冯国璋既反对段祺瑞,又害怕与段派决裂。冯氏这种微妙心理,已经为敏感的媒体觉察。5月26日,上海《时报》报道了冯段之争的分歧所在,指出:“某派方疑大树(指冯国璋)暗中运动和平,并利用外交二次倒木(指段祺瑞),自不能不表此态度,以避嫌疑。大树曰总理做主,又说千万为我留一面子,词义大可玩味也。” 在中日军事交涉期间,冯国璋故意采取消极的回避态度,表示反对之意,而段祺瑞也有意不理睬冯氏。6月2日,《时报》报道说,段祺瑞“不入公府,将近一个月”。 6月4日,《时报》又报道:“冯国璋前数日不看公事,秘书长代办。”
从3月至5月底,是中日军事协定交涉的关键阶段,这期间府院两方处于僵持状态。在此关头,中国兴起了反对中日军事协定交涉的运动(简称反日运动)。段祺瑞的亲日政策,令有识之士深表忧虑。如北洋军人徐永昌所言,“段的‘新外交’对于练兵则曰互相聘用人员,训练双方军队;如兵工厂,则曰彼此派员管理;如军械军费则曰互相接济,直不如说代练兵,代管兵工厂之为间捷了当耳!此与日韩合并之说,同一调门。”徐永昌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他所担心的段祺瑞政府的亲日政策将使中国沦落为日本的附庸国,这也正是中国留日学生发起反日运动的根本理由。
留日学生与反日运动的兴起
此次反日运动,之所以首先由中国留日学生发起,并非偶然。留日学生身处异邦,他们的国家认同意识与国内同胞相比,是更加强烈。留日学生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与日本的留学环境有直接关系。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翻然改态,蔑视中国人。如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所言,“蔑视中国留学生的不只是他们的日本同学,社会上一般日本人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态度更是等而下之”,而且,“日本当政者的国家优越感及其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影响著一般的日本国民,使人人都怀着对中国和中国人轻蔑的态度”,特别是民国以后,“日本人对中国人轻蔑(或憎恶)变得更厉害,这一点当局也承认”。许多留日学生已经看穿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留日学生在上北京政府教育部的呈文中指出:“十年以来,彼何日不以亡我为事,封豕长蛇之心,路人皆见。第生等羁处异邦,见闻较切,刺激尤深耳。”所以,当他们得知北京政府在与日本进行中日秘密军事交涉时,异常愤慨,遂发起声势浩大的罢学归国运动。
日本政府严格保守中日军事协定交涉秘密,因此日本各报对于此项秘密交涉,“均一言不露”。3月21日,东京《朝日新闻》才隐约透露,“中日间开始某种重大交涉”。 如前所言,3月22日,京津《泰晤士报》也有类似报道。直至4月3日,有关中日新交涉的新闻报道才引起中国留日学生周恩来的注意。是日,周恩来“晨起,阅英文报,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条’要求于中国矣”! 这则新闻触动了周恩来的爱国心。4月4日,周恩来日记写道:“早晨,因思昨日日本要求事,我政府尚愦愦,奈何?”表达了对北京政府的失望之情。在东京留日学生中,周恩来是较早得知中日军事协定交涉一事,广大留日学生此时尚未注意及此。
5月初,上海报界关于中日军事协定交涉的系列报道,在东京留学生中间大范围传播开来。东京留学生界在致国内的公开信中,指出:“同人等前此以此间各报受日政府之意,对于向我国近来交涉中之秘约,均一言不露,是以同人等对于此中真相颇多不明。至上海各报揭载以后,同人等始得于此知之。”与此同时,留日学生开始商讨应对策略。5月2日,周恩来记载:“观报多时,国事益坏矣!近一二日内,因中日新约行将成立,此间留学生有全体归国之议论。” 5月1日、2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留日学生殷汝潮率先倡议留日学生应该全体归国,得到该校“同窗会赞成”,遂推举代表“四处游说,发布传单,征集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意见”。
东京北神保町的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中华青年会馆)是中国留日学生反对中日新交涉的聚会场所。 孙中山曾说,“中国人的乡党观念强而国家观念弱”。不过,这句话对于留日学生来说并不确切。中国人的“乡党观念”强确属事实,但正是这种朴素的“乡党观念”成为留日学生国家观念滋生的重要源泉。实际上,中国学生到日本后,由于彼此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便产生了作为“中国人”的意识,因此也就感到有团结起来的必要。晚清末年,中国早期留日学生领袖曹汝霖、章宗祥、范源濂等人就组织“励志会”,团结留日学生中的有志青年。1902年,曹汝霖等留日学生领袖成立“清国留学生会馆”。1910年以后,中国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留日学生新的聚会大本营。 此外,留日学生以各省为单位,成立了各种同乡会。此次反日运动中,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成为留日学生大串联的有力纽带,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动员作用。
1918年5月4日,下午,吉林同乡会首先开会,赞成归国主张,奉天省(今辽宁省)同乡会也相继赞成。同日晚,“有数省表决赞同”。 次日,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代表聚议“大高俱乐部”,有直隶、河南、江苏、湖北、湖南、云南、四川、贵州、山西、山东、陕西等11省留日学生代表赞成归国。会议决定组织全体留日学生组织“大中华民国救国团”,规定以“一致对外,决不干涉内政”为宗旨,商定留日学生归国时,由“各省同乡会会长及其代表,统率该省学生一致行动”,要求各省派出四人以上的“先锋队”,分别前往北京与上海筹备一切。
尽管留日学生极力反对中日新交涉,但是他们并不主张采取极端行动与政府对抗。5月12日,十一所留日学生所在学校的代表开会,一致宣布“告留东中华民国学生”书,表示此次行动为“爱国,愿与政府交涉解决”。 5月14日,留日学生派出代表四人会见了日本文相、外相以及警察总监,询问中日新交涉情况。日本外相后藤新平发言,谎称,“中日协约无他事,仅关系于西北利亚出兵问题。军事行动当然得守秘密,报纸尽属虚构”。这种答复,自然令留日学生代表不能满意。同日,周恩来等留日学生领袖接到前期到达上海的400名留日学生来信,“催全体速归”。 据日本警视厅5月15日调查资料,东京36所大专院校,中国留学生共2783人(据中文资料统计当时在日中国留学生约有3548人),罢课者2680人,罢课学生占全体留学生总数96%强。
1918年5月16日,《大阪朝日新闻》及《东京国民新闻》报道,北京政府将在一周内签署中日军事协定,上述报道令留日学生震惊不已。 次日,留日学生“大中华民国救国团”东京支部发出警告,呼吁全体留日学生尽速回国,挽救祖国。 随后,救国团不断催促留日学生“不归者速归,切勿逗留”。 据日本警视厅统计,截止6月12日,已有1207名留日学生回国。留日学生大批归国之后,即动员国内各界,一起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签约。随后,反日运动的中心从日本东京转移到国内京、沪两地。
留日学生归国直接推动国内反对中日新交涉运动的兴起,但国内各界对此反应不一,这种差异是由各自的核心利益、政治态度及其与当局的关系诸因素造成的。大中华民国救国团是负责留日学生归国的核心组织,留日学生王兆荣担任干事长,阮湘、张有桐是副干事长,他们是救国团的领导者。1918年5月12日晚,负责北京联络任务的留日学生阮湘一行三人抵达天津。5月14日,阮湘等人与天津《益世报》接洽两次,又三次拜访湖南同乡、社会名流熊希龄,因其“外出未晤”。此外,又与天津各校接洽,受到各校代表的欢迎。 5月15日,阮湘等人抵达北京,以正阳门外的湖南会馆为活动据点,其对外态度仍本前旨意,即“此次回国实欲促政府之反省,将中日共同出兵交涉根本撤消,对于内政绝不干涉”,而上海留日学生则因受“一方面之潮流,主持变为激烈”。 阮相是留日学生中的稳健派,他不赞成与政府对抗的主张。阮曾致信上海留日学生代表,反复告诫他们“言动务请稳健,必须反复申明无干涉政治之意”。
留日归国学生抵达北京、上海是在5月中旬,此时正值中日军事协定签字之日。这两件事情都成为国内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随之,以京、津、沪等大城市为先导,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一场以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为主旨的民众运动。留日学生回国代表与国内学生界联合起来,推进反日运动的开展。5月20日,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代表阮湘等人与北京大学等学生团体共同组织一次声势浩大的和平请愿活动。同日晚间,2000余学生聚集北京大学,留日学生代表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会议决定次日到总统府请愿。 5月21日,北京2000余学生前往总统府,上午12时,学生代表见到总统冯国璋。 冯对学生们说:“诸生当亦知予之经验资格岂肯卖国乎?不过弱国与强国结条约,稍有损失,亦所难免。且日本极力与我国提携,表示一种亲善状态,我国人岂可一脚跌他出去乎?”学生代表被冯国璋几句官话即打发回去,请愿毫无结果。随后,北京政府即对留日归国学生采取严厉措施,勒令他们返回日本,继续留学生涯。5月21日请愿当日,北京教育部就向直辖各校和私立学校发出训令,同时密电各省行政长官,要求严加取缔所有学生集会和请愿活动。 次日,教育总长傅增湘发出第五号训令,指出“闻力学以救国者矣,未闻废学以救国者也,”劝告归国留日学生早日东渡,镇静求学。
到5月底,全国大部分省市都有学生团体举行抗议活动,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学生罢课和示威请愿。虽然此次排日运动波及诸多城市,但始终局限于学生界,其他阶层没有真正卷入。 5月28日,教育部下达第7号训令,限令留日学生6月10日以前回院校,否则“一经查明,不能不予开除学籍,以示惩儆”。 同时,教育部还通电全国各校,“禁止学校干预政治”。 在政府压力下,6月下旬以后,北方各地学生运动开始转入低潮。
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江苏省教育会、浙江省教育会会长经亨颐等为代表的教育界领袖对于此次学界发起的反日运动,也怀抱消极的态度。5月25日,浙江省教育会会长经亨颐向留日回国学生潘锡九、陈俊晖、王兆全等人表示:“因近日中日交涉,留学生全体归,以爱国之目的被利用,而为害国之方便。”经氏劝他们早日返回日本。次日晚,经亨颐又邀集留日学生王兆全、陈俊晖、潘西九等人在寓所便膳,探询“留学生被动情形,并劝其切勿附和,适可而止,早[作]返东之计”。 其后,经亨颐还向江苏省教育会表示了他的主张是:“留学生事,亦无何等办法。以赞而不助,使即返东。”在江浙两省教育会的劝说下,浙江留日学生已开始动摇,准备返回日本。6月1日,范寿康告诉经亨颐,留学生“已愿返东,前提是教育部要取消六月十日之限”。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国民党媒体对学生界的反日运动,至始就采取鲜明的支持态度。国民党的党媒《民国日报》及时报道留日学生的爱国举动,并发表社论积极声援。据统计,从1918年4月至6月,上海《民国日报》刊登留日学生活动的各种文电100多篇;另外专载学生发表的文电38篇;为归国留日学生团体刊登启事100余次。简言之,国民党媒体对于此番学生抗议运动的积极支持,由此可见一斑。
为五四运动预热
此次学生界的反日运动,实际上只存在一月有余,为时甚短。所以如此,原因是学生界基本上是在孤军奋战,除了国民党人给予积极的支持外,其他党派和社会团体基本采取了中立的态度。特别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及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派人物没有参与进来。此时,《新青年》杂志坚持胡适的不谈政治主张,而专注于文艺思想的革新,对现实政治“有意回避”。 江浙两省的教育界领袖沈信卿、黄炎培、经亨颐等人对学生爱国举动则采取“赞而不助”的保守态度。没有广大社会力量的支持,单凭一些血气旺盛、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要想把反日运动扩大化,显然是不现实的。
从政府层面看,大总统冯国璋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尚未到公开决裂的地步。冯、段虽然明争暗斗,还不至于水火不容。冯曾试图利用学生运动迫使段祺瑞放弃中日军事同盟,但是段派的立场强硬,使其未能如愿。不过,此次反日运动为后来的五四运动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政治思想遗产——青年学生组织动员思想的强化。五四运动的健将匡互生回忆说:“自民国七年上期中日军事协定成立以后,……于是那些热烈的学生,因此觉悟到做事以前大有组织坚固的有力量的小团体的必要。几个月以内,各校学生独立自由组织和联合组织的小团体,相继成立的至少在二十以上。”
历史的前进,是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合力推进的结果。学生界通过此次反日运动强化了他们的组织观念,学生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18年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秩序发生重大变革。欧美列强重返远东,中国国内政治也深受这一国际局势变动的影响。中国国内政治派系力量进行新的重组,亲美派与亲日派,也借助外援以强化其政治地位。与此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五四时期的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愈益密切。尽管1918年学生界的反日运动如同昙花一现,但是此次运动客观上为即将爆发的五四运动进行了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作者授权,原文标题为“国家之敌:1918年的反对中日军事结盟运动”,《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刊发时有改编,注释略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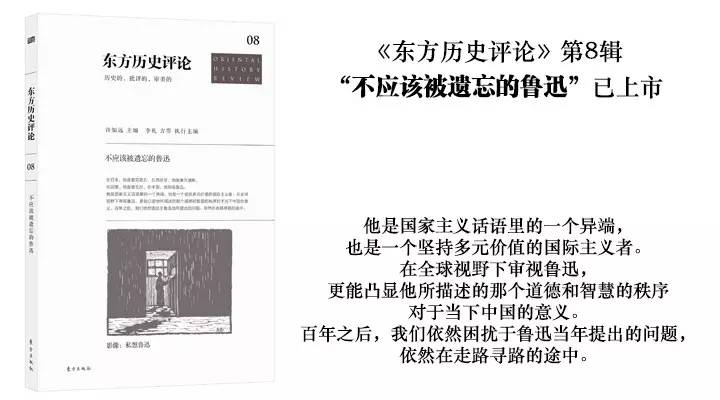
点击下方 蓝色文字 查看往期精选内容
人物|李鸿章|鲁迅|聂绀弩|俾斯麦|列宁|胡志明|昂山素季|裕仁天皇|维特根斯坦|希拉里|特朗普|性学大师|时间|1215|1894|1915|1968|1979|1991|4338|地点|北京曾是水乡|滇缅公路|莫高窟|香港|缅甸|苏联|土耳其|熊本城|事件|走出帝制|革命|一战|北伐战争|南京大屠杀|整风|朝鲜战争|反右|纳粹反腐|影像|朝鲜|古巴|苏联航天海报|首钢消失|新疆足球少年|你不认识的汉字|学人|余英时|高华|秦晖|黄仁宇|王汎森|严耕望|罗志田|赵鼎新|高全喜|史景迁|安德森|拉纳・米特|福山|尼尔・弗格森|巴巴拉・塔奇曼|榜单|2015年度历史书|2014年度历史书|2015最受欢迎文章|2016年最受欢迎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