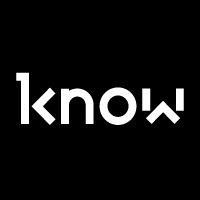我认为,疯癫可以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如果事情不尽如人意,你也许就想要幻想出更美好的事情来。
在我的疯癫中,我曾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人。
——约翰·纳什
约翰·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是电影《美丽心灵》男主角的原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数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是他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学术成果。然而,就在这些光鲜成就的背后,人们所不知道的是,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遭受着精神分裂症的困扰。
如果说,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了解,并接纳它们为:正常人”也可能遭受的困扰;那么
精神分裂症,就是那个仍然被无情划分在“疯子”世界里的精神障碍。
精神分裂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人人都听过,却不一定真正了解的精神诊断。

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迷思(myths)
迷思1:误以为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十分罕见的。
事实1:每100人中,就有1人可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世界范围内,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约为1%(Insel, 2010)。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受精神分裂症困扰的人超过2100万(WHO, 2016)。
迷思2:误以为精神分裂症,就是一个人分裂出很多不同的人格/个性。
事实2:精神分裂与人格分裂是两种不同的精神障碍。
“分裂出很多不同人格”,在临床诊断中被称为“分离性身份障碍”(DissociativeIdentity Disorder, DID),指的是人格的分裂,如《24个比利》中,男主人公时而是一名成年男子,时而又是一名青春期少女,就是一种人格分裂的表现。
不同于人格分裂,
“精神分裂”更多指的是一个人
认知与感官的统合失调,是感知与现实之间的分裂
(Smith & Segal, 2016),比如,出现幻觉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
迷思3:人们误以为精神分裂症是突发的,以为如果一个人受了特别大的刺激,就会患上精神分裂症。
事实3: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受到个体本身的基因、生物学及环境因素的影响。
基因、生理与环境因素,
都被认为是导致人们患上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因素(DSM-5, 2013)。
父母中的一方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其自身的患病风险达13%,而若父母双方都患有精神分裂症时,其风险则高达50%(Picchioni & Murray, 2007)。另外,父亲年龄过大、母亲在孕期的压力、病毒感染、营养不良、糖尿病等,也被认为与孩子患精神分裂症相关(DSM-5, 2013)。
突发的创伤性事件,并不一定会导致一个人患上精神分裂症
(Mental Health America, MHA, 2016)。此外,临床证据显示,大多数情况下,患者都是
逐渐地、缓慢地发展出一系列具有诊断意义的症状
的(DSM-5, 2013)。精神分裂
症
并非
一种突发性的疾病。
迷思4:误以为精神分裂症的人都有暴力倾向,对社会危害很大。
事实4:精神分裂症作为疾病本身,并不与暴力行为直接相关。精神分裂症患者自伤的风险远高于伤害他人。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发病时,有很大一部分症状为阴性症状,如情感表达、行动意志的减少。换句话说,一个人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并不意味着ta会有更多的攻击性。
另外,据统计显示,
比起伤害他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更经常伤害自己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IMH, 2016)。不仅如此,他们也
更经常是暴力行为的受害者
(DSM-5,2013)。
迷思5:误以为精神分裂症是不治之症。
事实5:世界上目前已经存在对精神分裂症有效的治疗方案。
众多临床证据显示,在抗精神病性药物、社会心理支持等相关专业服务的帮助下,
大多数
精神分裂症患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社会功能,如
生活自理
等,20%的人预后较好,并
有少数个体能够完全康复
(recover completely)(DSM-5, 2013; NIMH, 2016;Smith & Segal, 2016)。

精神分裂,是感知与现实的分裂
Schizophrenia,源于希腊语词根“schizein”,意为“分开”(to split),和“phren”,意为“心灵”(mind)
(Kuhn, 2004)。该词最早由瑞士的精神科医生Eugen Bleuler所创造,以此来描述他的病人中所出现的感受与想法之间统合失调的状况(Stotz-Ingenlath, 2000)。
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 2013)中,精神分裂症,被列为精神分裂症谱系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中的一种严重的、长期性的精神障碍;其发病的高峰在青少年晚期至成年早期(16-30岁)(NIMH, 2016)。
越来越多的研究与临床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是由一系列
神经发育问题
所导致的、一种
存在生理基础
的精神疾病(Insel, 2010),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情绪、行为、语言及对自我的感知(sense of self),使人们的感知与真实世界逐渐被割裂开来。
* 精神分裂症患者主要的症状表现
目前,在DSM-5中,对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包括了这类患者常表现出的一些阳性与阴性的症状。
阳性症状
(Positive Symptoms):
阳性症状,也称为精神病性症状,它们被认为体现了患者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距离(NIHM,2016)。主要包括:
-
妄想(如被害妄想、关系妄想、钟情妄想等等)
-
幻觉(主要以幻听为主)
-
言语紊乱
-
明显紊乱或紧张症的行为(如僵硬的动作或姿势)
阴性症状
(Negative Symptoms):
阴性症状并不仅仅出现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还可能出现于如抑郁等其他情绪或精神障碍中(NIMH,2016),如
情绪表达减少,意志减退(没有兴趣参与到工作或社交活动中)等。
通常,阳性症状更容易被药物治疗,也更能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症状减少,而阴性症状存在的更持久,也对患者的预后与生活质量影响更大(Velligan & Alphs, 2008)。
此外,精神分裂症还表现为一些其他的症状,如认知能力的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短时记忆出现问题(即刚学到的东西,转眼就忘)等。同时,认知能力的下降,还可能使得精神分裂症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觉察力变弱(DSM-5, 2013)。所以有些时候,可能
并不是他们不愿意就医,而是他们无法察觉到自己的异样。

在以上的症状中,值得一提的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那些固执的想法之所以被称为
“妄想”
(一般人也可能会有一些固执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想法通常比较古怪,更重要的则是因为,
即便现实中存在确凿的客观证据与他们所持的观点相悖,也无法动摇他们的心中的那些想法
(DSM-5, 2013)。
这些症状,在
Daniel的案例
中都有所体现(Smith & Segal, 2016):
Daniel是一个21岁的大学生,课余时间在一家商店的仓库做兼职。渐渐地,周围人发现他变得很古怪。一开始,他总觉得某教授会在下课之后跟踪自己,因为自己上课常常不认真听讲。后来他告诉室友,全班同学都已经在教授的监视之下,尽管其他同学都没有人有类似的感受和看法,教授也并没有在他所说的时间地点出现过(妄想)。
此后,他便辍学在家,情况也随之变得更加糟糕。Daniel连续几个星期不洗澡、不换衣服、不出门、不与任何人往来(阴性症状)。他的耳边逐渐出现一个声音,告诉他,仓库里的电视机被装上了监视器,他必须将这些监视器找出(幻听)。于是,他开始一台一台地砸电视机,试图按照那个声音的指示找出监视器。
* 也有最新的研究认为,精神分裂症这一诊断应该被取消
尽管近年来相关的研究让人们对精神分裂症的了解越来越多,但却有学者指出,诊断标准中所谓的“精神分裂症”,可能并不存在(Hickey, 2010; van Os, 2016)。
在现有的诊断标准下,一个人可能因为出现言语紊乱、幻觉及社交能力丧失而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而另一个人则可能因为出现妄想、情绪表达减少而被确诊。
Hickey(2010)指出,
并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这些症状背后的致病原因或机制是相同的,然而,具有这些症状的人却被诊断成为了同一种病症。
同时,这些病人身上,也没有发现某个一致的风险性基因,也就是说,有些病人是由某a基因导致出现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而另一些病人则由某b基因导致。从神经科学角度上来说,也不能证明这些疾病有着同一个起源(Picchioni & Murray, 2007; NIMH, 2016)。
Hickey(2010)认为,总之目前这种由一系列症状组合而成的诊断标准,可能需要更充足的科学依据来证明它们或者它们的组合,都是所谓的“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表现,而“精神分裂症”这个诊断不只是人们为了解释一些不同寻常的行为举止而创造出来的标签而已(Hickey, 2010)。

精神分裂症给人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