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申放榜季刚刚结束,大洋彼岸却传来几则令人震惊错愕的新闻:
全部都是考入藤校的学生,陆续收到大学的“学术警告”,面临退学!
先是一位哥大妈妈在社交媒体发的求助帖。孩子在哥大读书,一天凌晨2点他接到了孩子高中同学的电话,被告知孩子在
考试中挂了三门课,已经收到校方的退学信。
后来是一位进入美国Top5大学的女生,在上学期拿到了
F的成绩后被大学“学术警告”
;
还有一位藤校生在学术和社交压力下陷入无限的负能量循环,已经有抑郁症状(没办法自己起床上课),
两门课拿到了C的成绩,选择休学。

△2021-2022学年,哈佛大学有51名本科生因学业成绩未达要求被劝退,另外还有149名学生处于“学术缓刑”状态,面临被劝退风险。
而在去年年底,也有一则关于退学的新闻在留学生家长圈讨论度很高:
北京的学霸女孩以SAT近乎满分的成绩进入MIT,原本应该风光无限,
却因旷课和挂科被MIT退学,只能回国重新参加高考。
不光是父母几百万的教育费用打了水漂,退学后,孩子更是患上了轻度抑郁症,一家三口都需要接受心理治疗。
我们为孩子可惜之余也在反思,这背后,父母的教育一定出了问题,让孩子沦为了分数至上的“考试机器”。
而我们的专栏作者维舟在深入分析了中美两国不同的“鸡娃”方式后也发现——
“中国式鸡娃法”可能并不适合国际赛道。

这驱使着无数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重视从娘胎里就开始抓起,也有人指责正是这一说法造成了“鸡娃”的全民焦虑。
但不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拼娃”早就成了一场无法退出的军备竞赛,因为人们都意识到,
当下是一个竞争导向的社会,没有谁愿意自家孩子成为输家
。
怎样培养孩子的竞争力?这是当下家长们无不关心的问题。不过,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底下,规则不同,人们对“竞争”和“竞争力”有着相去甚远的理解,最终塑造出来的“学霸”精英当然也会有所不同。

美国式鸡娃
世上并不只有中国家长才“鸡娃”,美国也是一个高度竞争性的社会,偏爱赢家。而高等教育也同样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为了确保孩子能在竞争中获胜,美国家庭同样被驱使着向各种竞赛投入大量钱财、时间和资源。
然而,美式教育有一个关键的不同,那就是并不像中国家长那样看重智力因素,而是积极为子女塑造某种社会资本。
社会学家希拉里·弗里德曼将这种竞争文化称为
“为赢而玩”
(playing to win),指出美国家长对孩子获取文凭的需求驱动了相应的教育投入,使得“要赢”成为美国童年生活的核心。
基于对各种培训班的长期跟踪调研,她提出了“童年竞争资本”这一概念,指出美国家长为了能让孩子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竞争,期望他们从小就养成一些特殊的品质,而那是建立在五种技能和经验之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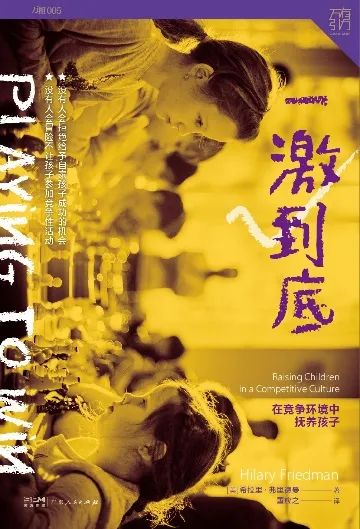
△《一激到底:在竞争环境中抚养孩子》
[美]希拉里·弗里德曼著,董应之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第一版
正如这项研究发现的,在与儿童的互动中,有三个主题不断出现:
总的来说,这些品质,乍看起来似乎都和成绩没啥关系,而更多地涉及如何面对输赢的心理素质(尤其是在竞争时保持冷静)、团队协作竞争等“虚”的东西。
为什么这些美国家长不是把孩子赶去补课,而是把精力放在足球、国际象棋、舞蹈这些兴趣爱好上?
因为美国的大学不像中国这样看重全国统一考试时的录取分数,而更倾向于看申请者个人的整体素质,而像这种素质还不是能突击抓一下就能马上提升的,这么一来,为了让孩子在大学申请的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课外活动就十分关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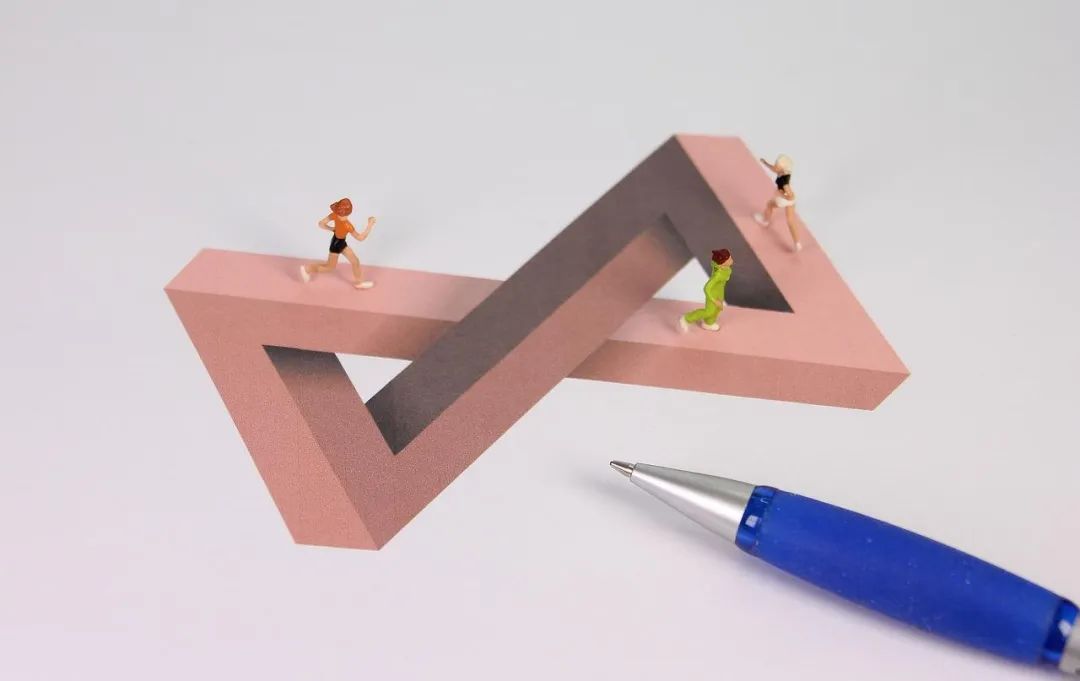
不仅如此,美国的职场精英选拔也特别看重社会资本,尤其是你能与团队相处的能力,仅仅考试成绩好并不足以让你跻身精英阶层。所以希拉里·弗里德曼才强调:
“童年竞争资本也带有社会资本的成分,因为它将儿童和他们的家庭联系了起来,使他们得以进入社会圈子。
此外,它还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符号资本,这主要是因为孩子们所赢得的荣誉和喝彩可以给他们带来额外的社会认可。
由于童年竞争资本所包含的这些不同的元素,它被认为极大地助长了竞争习惯的形成,特别是因为与之相关的很多文化资本都是具象且制度化的。”
不难看出,这种教育模式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品格、社交能力,有时甚至是形象塑造能力。因为在这样的竞争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学习如何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赢家,并表现得像个赢家”。
不仅如此,这种竞争与其说是为了争夺一个确定的名次、资格而拼搏,不如说是为了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面对国际性的就业竞争而强化自身的内在素质。
然而,中国式“鸡娃”可不是这样。


中国的学霸养成之路
社会学者姜以琳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追踪访谈了27位超级精英学生,并通过其家庭、学校和人脉圈,了解其成长经历,解释他们何以能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中脱颖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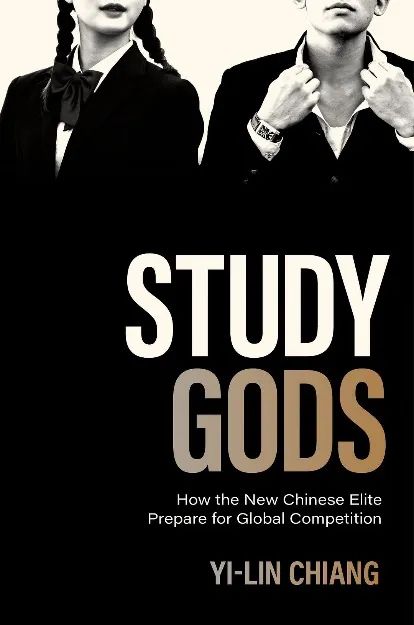
△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Yi-Lin Chia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8
对比美国的情形,就能看出中国式的精英培养模式在机制上的差异:
这些学生之所以能名列前茅,固然也离不开家庭的社会阶层的资源,但他们精英身份的获得,主要并非源于其血统和文化资本,
倒不如说更多依靠的是高强度的学习、家长和学校协同的精英选拔和教育模式。
中国之所以能催生出“学神”,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在“分数为王”的教育体系里,大量资源向这些精英学生倾注。
这其中隐约可见科举的传统和“赶超型现代化”的“遗产”:落后国家中的社会较低阶层,要想翻身,唯一可取的就是选拔少数智力超群的天才学子,去接受最好的现代教育,让他们成为国家建设所急需的栋梁之材,以一个“少而精”的团体来弥补差距。
这一思路从晚清选派留美幼童,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大学少年班、各地都有的重点学校或强化班,使精英学生的选拔形成了一套覆盖全国的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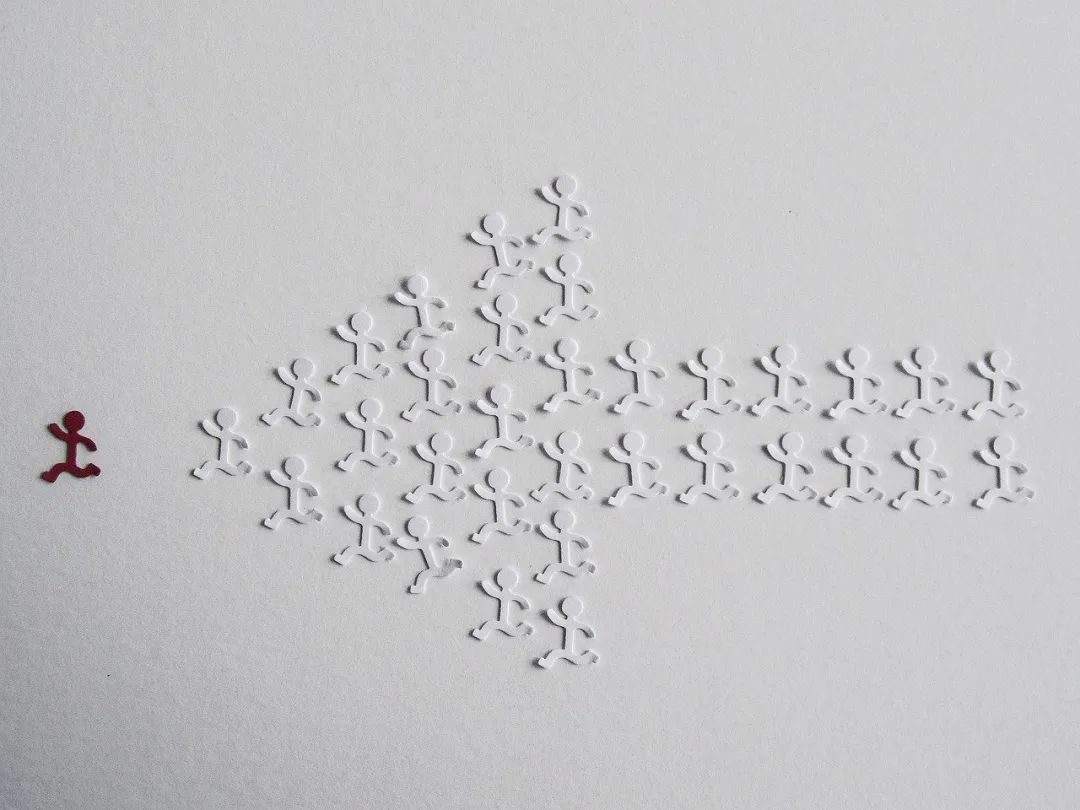
和西方不同,这一精英教育原本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社会阶层的再生产,而是国家建设的需要。至少在很长时间里,国内重点学校的精英选拔不仅仅来自那些上层家庭,而是根据学生的成绩择优录取,从社会各阶层选拔。
正因此,这一模式虽然明显倾向少数精英学生,但人们却普遍认为它是“公平”的,决定性的因素似乎并非家长的资源和人脉,而是学生本人的天赋和努力。
就此而言,当下的“学神”群体其实是旧体系变异后的新现象:虽然重点学校仍一如既往选拔成绩优异的好学生,然而现在的竞技场上,单靠学生自身已不够,城市中上阶层的父母能为此调动的资源(无论是金钱、时间、人脉还是信息)远非一般家庭所能比,以至于有人哀叹“寒门再难出贵子”。
这些年来,人人都苦于“内卷”这种白热化的竞争,但又别无办法,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系统里,教育已经成为获取精英地位的最重要(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也就是说,“学习这件事太重要,以至于不能只是学生自己的事了”,竞争早已不单单只是个人天赋和努力的问题,而成了一项高耗能的集体投入,所有人都得为学神们的前途让路。在这样的总动员机制下,那些相对弱势的家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
这样一个精英选拔体系,原本就是一项国家战略,近年来超级中学的扩张尤其得益于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
和一般人设想的不同,这些重点学校的起飞,不完全是依靠高强度的学习和管理,而是借助自主招生、贫困生专项计划等搜罗到的优质生源。
学校、老师之所以支持学霸,也是因为这些直接牵涉到自身的绩效、奖金等一系列利益。
也就是说,无论是重点学校还是精英学生,所得到的资源都谈不上公平,而是相关政策和各级利益有意无意推动的结果。


你的孩子为国际竞争做好准备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