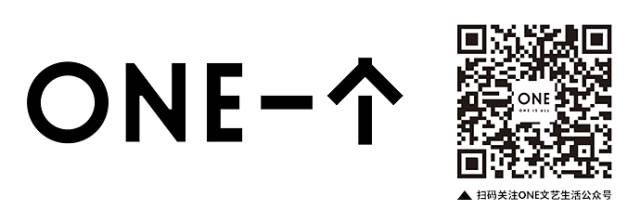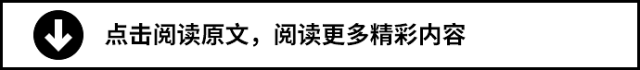那些你放不下的梦想...是会回来找你的。


你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你最疯狂的梦想是什么?你先想一会儿,待会儿我再来问你。
我想先告诉你一件事:这会儿,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大四学生们已经在接收第一份工作的Offer,而他们明年才毕业。
不出意外,他们都会进入最好的银行、投行、私募、VC……拿着远高于本科毕业生平均四五千的工资,10年后,很可能年薪千万。
除了吴呈杰。他是2014年江苏省高考理科状元,北大光华学院大四学生。他如今放弃了保研的机会,决定做一名记者。
他可能是疯了。
1
我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想给这个96年的天秤男,泼一桶冷水。我大他4岁,当过记者,有过新闻理想,到现在还有。但我不得不吐槽,这条路很坑。
后来发现,他没少被泼冷水。
3年前,吴呈杰成了江苏高考理科状元,大批记者到无锡找到他,问他想学什么。
他说:我想做记者。他那种状态就像,终于做到了世俗的优秀,熬出了头,现在总算可以去做真正喜欢的事了。
每个记者都告诉他:千万不要。
他们说,新闻是被时代抛弃的职业。除了一直以来的活多钱少,现在还少了曾经的自由,以及职业的尊严。
“我突然很恐惧。”18岁的吴呈杰,于是回到了他曾经一如既往的“正确”道路上,去了北大光华学院。他想,也许做金融挺好。至少大家都说很好。
然而事实证明,你心中那些梦想,放不下,是会回来找你的。不依不饶。
新生舞会上,吴呈杰遇到一个女生抱着厚厚的一摞纸在阅读。她刚加入了校媒《此间》,她读的是主编布置给她的阅读作业,一堆特稿。
吴呈杰开始淡忘的新闻理想,又被点燃了。他找到《此间》的主编,成了其中的记者。
一篇关于北京高校LGBT群体的稿子,让他尝到了做记者的成就感。文章在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广受好评。因为这篇稿子,北大成立了第一个民间的LGBT社团。
“原来,写作是能改变一些事情的。”他对我说。
我突然有点感动。想起了当年我写《偷渡客在美杀人事件》时的那种骄傲和成就感。那是会上瘾的。
大二,吴呈杰决定修双学位——光华的市场营销和北大中文系,同时开始在《人物》杂志实习。
“选题的范围,从我们关注的校园生活,变成了整个社会关注的话题。半径扩大了很多。”
他说,在光华学的东西是,越来越深、越来越窄,而做记者,让他的世界,越来越宽。
但,随着毕业越来越近,朋友们都在谈论出路,吴呈杰又开始迷茫。
真的应该去做记者吗?十年后,如果身边朋友的社会地位和收入都远高于我,我能接受么?

2
今年7月,吴呈杰有了答案。那时他在《人物》发表了第一篇特稿。报道的是少女偶像团体BEJ48的培训体制和弱肉强食。
他出差到横店,看少女们拍戏。天蒙蒙亮,他就搬着小板凳来到剧组,开始一整天的观察。
那篇文章出色,他也从一个做外围采访和整理资料的实习生,升级为一个可以独立做特稿的记者。
BEJ48里的一个少女团员读了吴呈杰的这篇稿子,她的反馈辗转传到了吴呈杰那里。她说,这个记者写了我这21年没考虑过的很多问题,我该想想我的生活了。
“我居然能帮一个姑娘重新审视人生。”吴呈杰也很惊讶和激动。
那个夏天,原本纠结要不要进入金融行业的他,做了一个决定:去做几个月全职记者,试试自己到底喜不喜欢,适不适合。
听吴呈杰讲他的故事,我其实一直在回忆自己的纠结。虽然没他那么厉害,但我也从小就是,年级前三,全家的骄傲,走在正确的康庄大道。
习惯于走在“正确道路”上的人,有一个毛病,就是,既厌倦世俗意义上的优秀,又没有勇气跳脱出来。
这种从小到大的惯性,可以让一个人,在每一个十字路口,踌躇很久很久,最后总是很怂地选择直行。
高中时选修课,我很想选画画。老师说,这门课成绩不容易高。我问我妈怎么办,她说让我自己决定,只要不太影响GPA就行。我纠结了很久,最终选择了化学课。
我常常想起这件事,讨厌自己。
吴呈杰的说法是,他迟到的青春期逆反心,推了他一把。
“过去,大家都说,你要取得多大的社会影响力,说你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我都听。但是上了大学以后,大家越想让我成为怎样的人,我就越不想成为怎样的人。”
![]()
3
吴呈杰用一个夏天又做了两篇特稿,一篇《动物孤独》讲述地球上剩下的最后三只孤独的斑鳖,和想拯救它们却一直在失败的动物学家。另一篇《追凶》讲述了一场22年的追凶之旅。为了采访和拿到素材,他就像上访似的,在公安局一坐就是一天。
他发现,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
在过去21年,吴呈杰都在被焦虑持续笼罩。现在他依旧焦虑,但都变成了具体的焦虑:焦虑采访,焦虑选题。
至于人生选择,他不再焦虑。他过去心有不甘的梦想找到他了。
三天前,他以《动物孤独》这篇报道,在刺猬公社主办的Epoch非虚构故事大赛里,从5000名选手里脱颖而出拿到了第一名。奖品是10万元,和一份40万元年薪的工作。

他还不知道那40万年薪的工作是什么,如果是做特稿记者的话,那他很开心,因为这薪水这可比他原本想象的多得多了。
那10万块,他打算请帮他一起准备比赛的同学去海南度假——当时他在光华学院的朋友知道他要参加这个比赛都很支持,为了最后的演讲,有人帮他改PPT,有人翘课陪他模拟演讲。
我跟吴呈杰吐槽,他们应该是觉得,他们十年后的年薪会是你的几十倍,所以提前关怀关怀你吧。
我问他,传统媒体的老师们一个个转行,特稿记者越来越少,你不怕走错了路么?
他说,也许记者做不长久,也许他也会跟很多前辈那样,在十年后遇到中年危机,但是现在的他,还早。
“我其实有个伟大的理想,想做作家。虽然说作家也失去了尊严吧。”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这么说还挺悲伤的。”
采访的最后,吴呈杰跟我提了唯一的一个要求:“标题里,可不可以不要出现‘高考状元’四个字?”
这种感觉我懂。是不想再被任何世俗标签绑架,不想被自己的过去绑架。他不是高考状元了,他是个记者。
4
小时候,我最想当的是护士,我的邻居黛黛,想当公共汽车售票员。
我妈给我买了一套护士的玩具,我给我们家每个人做身体检查,再去黛黛家给他们一家三口消毒、扎皮筋、打针。黛黛她妈给她做了一个木板儿,上面绑着一大摞纸,当作车票。黛黛就在两个家跑来跑去,拿着一支小铅笔,给每个人检票,提醒我们从前门上车。
那时候的我们,好幸福啊。我们的梦想没有高低,我们追求地毫无顾虑。
然而长大以后,那些比打针、检票、按电梯还要酷的理想,居然都不被看好。
有的人的理想被时代抛弃了,有的人的理想是背离世俗,有的人被说天马行空、痴心妄想,有的梦风险太大,有的又太普通。
可能你想去支教,做乡村老师;可能你想做个画家,画却很难卖出去;可能你想倾其所有去创业;可能你就想做一个日复一日的匠人。
如果你问我,我要去不去?我一定说,去!
因为那些你放不下的梦想,是会回来找你的。不依不饶。
我有一个因为看了《广告狂人》而决定进广告业做文案的朋友,每月拿着微薄的薪水,没日没夜地工作。
她知道了公司里没有DonDrapper,曾经的麦迪逊大街,现在只是富太太逛街地方。但她,只有亲眼看到,才不愧对这个梦。
有一个被时代抛弃的梦想,本是一件悲伤的事,但你若不去试一回,你除了悲伤,还多了懦弱。
我们也许被时代抛弃,也许被时代裹挟,但我们至少可以,靠勇气来和时代和自己,达成和解。
#尤里卡时刻#
请回答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你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你最疯狂的梦想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