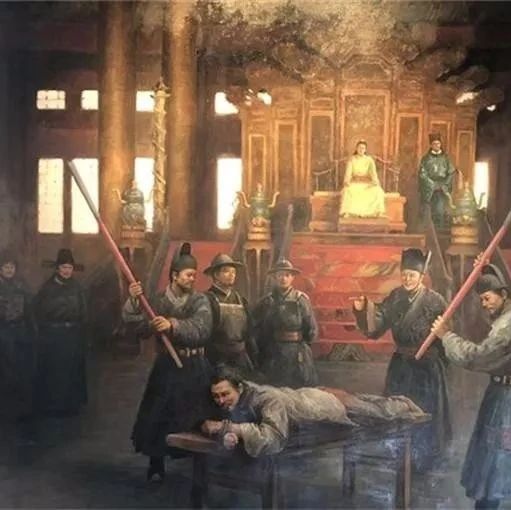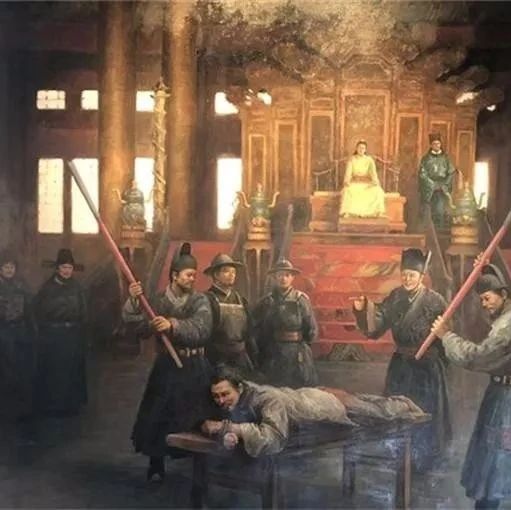作者
尚文华,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SHANGWenhua, Institution of Philosophy, 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inan
)。
大地上的自由
——
叶秀山先生的哲学遗产
尚文华
(
SHANG Wenhua
)
摘要
:
一个人离开世界总是让人悲伤的,而对其生命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也总是纪念他的最好的方式。叶秀山先生尤其如此。在这里,我主要沿着叶先生工作的重心——自由概念,对叶先生的哲学遗产展开论说和梳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性自由是叶先生一生致力所在;在看到其短板之后,叶先生又深入展开对现象学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对大地上的自由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大地的根基不止是过去和现在,甚至更重要的乃在于未来,这是叶先生对自由论述的最深入的地方,同时,也是在这里,叶先生开启了与宗教的对话。但无论如何,我们也正是在此看到叶先生一生对自由进行论述的未竟之业。拓展性的研究应该是对叶先生最好的纪念。
关键词:
叶秀山;自由;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中国文化;宗教
Freedom on the Land
——The Philosophical Heritage of YEXiushan
Abstract:
Mourning is always sad. But to inheritand develop his life goal of the deceased may be the best way to honor him.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Mr. YE Xiushan (1935-2016). Here, I mainly rely onthe focus of Mr. Ye’s work, the issue of freedom, to illuminate his philosophicalheritage. Mr. Ye has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study of speculative freedom of Germanclassical philosophy. After recognizing its shortcoiming, Mr. Ye has also setupon the study of the phenomenology and Chinese culture in depth, and made an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freedom on the land. According to Mr. Ye’s mostin-depth view on freedom, it is the future, rather than the past and present, thatis the most important for the root of the land. This is also where Mr. Ye startsa dialogue with religion here. But it is also where we can see his work leftunfinished. Thus to develop his study is the best way to honor Mr. Ye.
Keywords:
YE Xiushan; freedom; German classicalphilosophy; phenomenology; Chinese culture; religion
如何面对另一种本源性的文明是中国人近两百年来的历史命运。对自身有着本源性的民族来说,这确实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事情;但确定无疑的是,一旦完成这个进程,我们会在生存和思想上更加厚重。在这百年之久的历史进程中,无数学者置身其中,试图在生存见证和思想深处汇通中西,并将之作为自身生存和思想的一部分,从而更深刻地确立自己,确立属于中国人的身份。
无疑,很早我们就注意到,自由和信仰是掌控西方文明最重要的两套话语体系,是西方人确立自身的关键所在。如何理解甚至进入自由和信仰所引导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就是汉语学者尤其是思想界的最重要的任务。哪怕译介性的著作以及附会比较的著作出版再多,离开思想和生存方面的对话甚或有生命的生存性的交融,都不能说我们理解了西方文明的本源性所在。叶秀山先生深刻地看到这一点,并以之作为一生的志业所在。可以说,叶先生的所有著作都内在地围绕着自由展开,并通过自由思考基督教的信仰问题。下面我们就从三个角度分析叶先生所阐释的自由思想,并探讨其彰显出来的宗教维度。以此纪念叶先生。
思辨的自由
90
年代中后期,尤其进入
2000
年之后,叶先生重拾德国古典哲学。从早期学习古典哲学,经由研究古希腊,至
80
年代研究现象学
-
存在论传统,再重新回到德国古典时代,可见叶先生何等深刻地感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意义所在。众所周知,自由及其体系是古典哲学最重要的主题,甚至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学理探讨在根基上确立了现代社会之为现代社会的根据。
作为康德哲学专家,叶先生看到了康德哲学之于现代社会的奠基作用。按照康德的界定,自由意味着不受外在对象和感性的限制,意味着自我的主动性的活动空间——行为的自主性是道德行为的存在根据。这个空间是绝对不允许他人进入的,因而人与人的平等才是可能的,作为“限制
-
禁令”的法权才是可能的。因此,自由者与他人的共在就可以展示为一个普遍的共同的权力
-
权利空间。这就是现代政治
-
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1]
但无疑,在政治
-
法律体系之外,人更多地生活在伦理性的共同体里。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关系乃是由内在的德性规定,同时,在行为遵守内在的道德律之外,人还要求幸福。康德把德性和幸福,亦即道德的善和幸福的一致称为“至善”。对于人的生活来说,伦理共同体中的至善才是真正的目的。叶先生看到这一点,并视其为人的存在论目的,论述至善及其与宗教的关系也就成为叶先生的致力之处;
[2]
并且叶先生深刻地意识到,由至善的可能性而证成的“‘神’就不是‘人’的‘自我’的绝对升华,而是对‘人’来说是‘异己’的‘他者’的升华,即列维纳斯说的那个‘绝对的’‘他者’。正是这个‘他者’,使我们人类‘看到自己不得不那样远远地与理性世界沟通起来’……”
[3]
无疑,叶先生通过列维纳斯的眼睛看到,康德体系之外的绝对的他者之于人的存在的深刻意义。
[4]
由于这种觉识,叶先生阐释了黑格尔哲学对康德哲学的真正突破之处。叶先生认为,对他者的论述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康德的自由个体是形式性的,他无法在内容上与他者进行区分,这就意味着康德体系中的他者是模糊的和空洞的。由于看到这一点,黑格尔把仅用于知识的逻辑扩大到自由体之间,即自由(者)不是封闭在自身之中的,相反,他乃是在发现、意识、改变他者中确立自己。“‘自由
-
自我’要‘有能力’在‘自然
-
他者’中同样不丧失自己,在‘他者’中‘保持’住‘自己
-
自我’,在‘自然’中能‘保持’住‘自由’,在黑格尔看来,只有‘精神
-derGeist
’才能‘做’到。”
[5]
精神是在对立中保持自身的能力,就此而言,康德哲学并非真正的精神哲学。“精神现象学”的要义乃是精神在自身的“自由”和化为自身的“自然”之间的“现实”的展开。与康德式的“理想
-
理念”不同,黑格尔哲学的精神乃是“真实
-
现实”。现实乃是在“时间
-
实践”中的展开,因而黑格尔哲学内在地是历史哲学。此时,如果说还有绝对他者的话,这位他者乃是展示在历史中的绝对精神自身,这也是黑格尔用“上帝”一词的含义。
[6]
因此,在黑格尔式的“精神
-
现实”哲学中,“绝对
-
无限”在“相对
-
有限”中,“相对
-
有限”也在“绝对
-
无限”之中,“自由”与“必然”也就是一体的。
[7]
这样看来,逻辑学、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和神学在黑格尔思想体系中是一个整体,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展示“精神
-
现象”或“自由
-
现实”。就希腊以来的哲学的基本精神来看,黑格尔体系不单是作为体系的哲学的完成,同时也是理性所达到的绝对深度的体现。也就是说,理性并非空洞的思辨的彼岸之物,相反,它注定要进入“心灵”和“历史”,实实在在地将自身彰显在大地之上;自由及其体系(包括至善)也不是“理想
-
理念”,相反,自由乃是承担生死存亡、承担命运的自由,是站立在大地之上的自由。一直以来,中国的学者们总是在命运和自由的夹缝中做着选择,但无疑,一旦在思想和生存中领会了黑格尔哲学——也是哲学自身的精神所在,我们会看到,自由胜过了命运。
[8]
我想,叶先生所以重视黑格尔乃是深刻地体察到这一点,这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意义重大。
但是,同样不争的是,无论康德体系,还是黑格尔体系,都是思辨的产物。而在思辨的理论态度之外,“人”更多地“生存”在“时间”“之中”,“生存”在喜、怒、哀、乐、希望等情绪中。甚至,是这些情绪,而非思辨的理性,更多地,更实在地推动人的生存选择。也就是说,即使理想的道德行为能证明人的自由,即使人的自由有能力在他者中保持自己,但无疑,自由都要落实在“当下”的“处境”中,要“时刻”跟其他推动“选择”的情绪或闪现的念头做着争辩。
一旦把人的具体生存处境带入自由的思想视野,我们会看到,黑格尔意义上的大地上的自由就转换了意义:它不再是宏大的“思维
-
现实”,而是具体而微的、实实在在的让人安息的土地。这里是生老病死,是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之间真正交流和交融的场所。在这里,自由乃是有根基地发生的。我们看到,叶先生正是在这个视野中开启他的“现象学”和“中
-
西
-
见证
-
比较”的思想和生存之旅。
大地上的自由
把时间性引入自由不仅是生存的实际问题,在学理上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康德那里,理念不是知识的对象,从而不在时间和空间中;黑格尔把知识逻辑引入自由,理念在成为绝对理念的同时也要进入时空,但却是“完成”了的时空,因而,时间尽管没有被抛弃,但却是“理念的时间”,而非自由的时间。但是,“自由自然地有一个向时间靠拢的趋势。自由既然是原始性、开创性的,自由者作为‘始作俑者’,就有‘始
-
终’之时间性意思在内……自由就是时间;时间就是自由。”
[9]
因此,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海德格尔把自由、存在和时间拧在一起思考有其内在的依据:自由不是空洞的形式,相反它有着原始的实践性和开创性。就其开创性来看,思考“无”和“有”的关系也就是必然的。在学理上,叶先生就看到,现代存在论的关键乃是“非存在进入存在论”,即:人带来无,澄清死亡的非存在和存在意义是现代存在论的核心问题。
[10]
这就引入对人的生存问题的深入思考。
我们也确实看到,对生
-
死、有
-
无、有限
-
无限(生存论上的)、“时间
-
空间”等对子的深入沉思主导了叶先生从《思·史·诗》到解读中国古典书籍,再到《科学·宗教·哲学》等一系列核心主题的思考。在《思·史·诗》中,叶先生提出,早先欧洲思想由自由而出的“权力”“意志”要控制自然,凌驾生活,但这恰恰以“遗忘存在”为代价。相反,人的自由不是自然的奴隶,也不是自然的主人,“而是‘自然’的‘意义’的揭示者。‘人’使‘大地’显示其‘意义’,亦即‘大地’通过‘人’显示其真正的意义。‘大地’是‘自在的’,成为‘自为的’(萨特)。所以,海德格尔才说,‘人’是‘存在’(意义)的‘守护者’,‘人’的存在,‘大地’才不失去其‘意义’,‘人’使‘大地’‘存在’,并不是‘人’向上帝那样‘创造’了‘大地’,‘人’使‘大地’成为‘大地’,显示出自身的‘意义’。‘人’‘守护着’(保持着)‘大地’的‘意义’,不使其‘丢失’”
[11]
。
那使大地显示其意义,并守护着大地的意义的人被海德格尔称为“
Dasein
”,即:那在“这里”或“那里”,“此时”或“彼刻”的“
Sein
”显示着涌现在大地上的意义,并且“它首先意识到、发觉到自己的‘有限性’、‘时限性’,这就是‘人’,就是‘
Dasein
’”。
[12]
就这种觉识意义看,此在(
Dasein
)与其被称为“人”,不如说时间性
-
空间性更深刻地刻画了他,而此原始的存在意义上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构成其“生活”的“世界”,这正是大地的意义。另外,觉识其时间性和有限性意味着他在“生”的时候“进入”了“死”、“终结”,即:死是不可摆脱的“不远”,甚至是“更近”之事。就“生”之事实来看,“死”是一切可能性的终结、是自由(自主性的)的终结、是一片“虚无”;海德格尔把这种面对虚无的心境或情绪称为“忧”(
Angst
,还可译为“畏”、“着急”等)。
[13]
因此,面对死的忧揭示出无;而无则开显出大地的“本真”的意义。诚然,人更多地在“有”中看到筹划的可能性,也正是因此,肯定(有)和否定(无)常被联系在一起刻画有限事物的属性,本源性的“无”则被遮蔽了。但是,在时间的终结即死亡面前,一切有限意义上的肯定和否定都丧失了意义,就此而言,“无”比“有”更切己、更本真。这种对切己的本真的死亡的忧的逃避“让”我们遮蔽死的意义;但同时,对死亡的忧也“让”我们看到大地或世界的意义之源。一方面,切己本真的无能“让”一切意义都丧失,从而让我们看到,一切意义都联系在时间这一极点上;另一方面,在“让”意义丧失的“无”中,我们能更“本真”地领会“有”或“存在”的意义。这是时间性的
Dasein
的超越性所在;同时也是大地或世界的本源意义所在。对此,叶先生说:
“无”的意识的觉醒,又使人回到“人”与“世界”的本然性(本源性)状态。远古的“黄金时代”,卢梭幻想的“自然状态”,……都在这种“本然性状态”中得到了依据和净化。……西方的传统思想方式使“人”忘记了“本”,忘记“存在”(有)的意义,也忘记“不存在”(无)的意义……由于海德格尔,西方人终于从根本上正视了“无”的问题,在经过一段冲击性的危机感后,又逐渐找到了这存在论上的“无”与自己文化,哲学传统的沟通之处。[14]
在叶先生看来,“无”不仅沟通西方传统的古
-
今,同时也是汇通中
-
西文化的关键。在《思·史·诗》这样的现象学著作中,叶先生专门通过“有
-
无”之辩比较了海德格尔的“存在”和老子的“道”。之后,通过把“有
-
无”之辩与“生
-
死”的参悟相结合,叶先生有了一系列解读《老子》、《大学》、《中庸》、《庄子》等的文章。
[15]
甚至在其离世的前一刻,都在思考《老子》中的“生
-
死”“有
-
无”问题。
[16]
坦白地讲,叶先生并未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进入克尔凯郭尔,也就是说,叶先生对海德格尔的解读可能更多地停留在“无”本身及其之于“有”的存在论意义层面,而未曾深入揭示其生存论意义,这导致他并未更深地进入生存论层面的源始时间性。
[17]
但叶先生对《老子》的解释则显示,他从另一个层面“超越”了他所理解的海德格尔。
在早期,叶先生认为老子要守着那个“
Sein
”,反对“
Da
”,反对“
Da
”的限制和束缚,保住“
Sein
”也就是守住可能性或自由,这是“虚”、“静”、“朴”、“根”。而孔子的“‘仁’的概念原本是‘活’的,不是‘死’的。孔子的‘仁’像老子的‘道’一样,滋生着一切人伦规范,‘仁’就是那个‘
Dasein
’的‘
Da
’的本源性、基础性的意义”
[18]
。无疑,在看到“
Sein
”的“无”的意义的同时,叶先生也深刻地看到“
Da
”的本源性意义。也就是说,在死亡的意义上体察到自由的同时,人同样要把这片大地或这个世界担负起来,于人而言,这同样源始。这里已经体现出叶先生开始把“向死而生”改变为“向生而死”,即:人乃是源始地生存在大地上,而非孤独地被抛在这里。
[19]
在临终前发表的《读
老子
>
书札记》中,叶先生明确地表达出这一点。他把“隐身”理解为“我”为“天下”所有,把“身”投入天下之中,“积极地投身到天下(万事)之中”;把“死而不亡者寿”理解为“留守”,即留在大地家园之上,而非“散失为物”。
[20]
叶先生提示李猛说,“(这)大概跟儒家说的‘仁者寿’一个意思”,
[21]
由此可见,叶先生试图打通道
-
儒的努力方向。这种努力提示我们,对“无”的体察有多深,“有”(大地)就同样深刻且源始地规定了人的生存。与其说“向死而生”,莫若说“出生入死”,生死指示了生存的跨度和深度,但终究,人是在“生”中担负“死”、担负在大地上生存的“命运”。这是“自由”的“命运”,也是“命运”的“自由”。
在密切关注“有
-
无”、“生
-
死”问题的同时,叶先生在“时间
-
空间”框架下学理性地阐述了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关系,对三者做出清晰的逻辑界定。“如果说‘科学’侧重在‘现时’,而‘宗教’侧重‘过去
-
未来’皆为‘现时’,那么,‘哲学’就将重心颠倒过来,一切‘现时’皆为‘过去’和‘未来’。”
[22]
在科学观念中,时间和空间本就是两个最重要的要素,其侧重“现时”本就是重视空间,它为哲学开辟了空间方面的研究;宗教把“过去”和“未来”吸纳到“神”的观念中,因而是“超时间”的,在叶先生看来,这刺激了哲学的时间观念,为了吸纳宗教的观念,它把时间的维度放置在“未来”之中。
[23]
受制于空间的科学追求“必然性”,而“执着”消化过去和未来的宗教则追求“自由”。于是,哲学就是一门追求“必然性
-
自由”的学问,其“必然性”是“自由”的“必然性”、其“自由”则是“必然性”的“自由”。
这样我们看到,通过引入时间
-
空间及其所呈现出来的对象,叶先生简洁却又要害地对科学、宗教和哲学分别做出界定,并对其相互关系做出澄清。由于空间及其对象乃是现实或“现时”的,科学与哲学的认识论关系相对好处理——这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分析论”部分的问题。对于叶先生来说,重要而且艰难的是厘清哲学的未来观念,这是其能否消化宗教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是《科学·哲学·宗教——西方哲学中科学与宗教两种思维方式研究》所致力于分析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简单地讲,宗教问题考验的是哲学的未来向度;缺失这个向度,哲学就无法理解甚至无法面对宗教问题。而根据叶先生,哲学的未来向度同样是自由的未来向度,是人这样的自由存在者在大地之上有力、有意义地生存下去的关键所在。
[24]
自由的未来向度
最晚至
2004
年岁尾,叶先生已经意识到“未来”“观念”之于哲学和自由问题的重要性。在与《科学·哲学·宗教》(
2009
年出版)同年出版的《学与思的轮回——叶秀山
2003-2007
年最新论文集》中,叶先生“有意”把“哲学的‘未来’观念”(
2004
年岁尾作)放在此阶段思考的末尾——同时也是新阶段思考的起始。
[25]
之后,无论在解释康德等哲学家的作品中,还是在原创性的作品中,“未来”、“希望”、“可能性”、“预言”等成为关键词。
显而易见,思考“未来”、“希望”问题的实质乃是,叶先生在“生命现象学”的基础上对思辨性自由(黑格尔体系)的突破。绝对理念或神是超越的,其无所谓未来或希望。但人却不同。作为有限的存在者,人需要在时间中生存,其生存的本性就是时间性和有限性;但同时,其生存又指向无限性,因而未来和希望又是其不得不承担起来的生存维度。
因此,“因自由而有未来”不是指根据过去积累起来的“现实”而在“现时”推论的“未来”的行事能力;恰好相反,因为有死,人才有未来。当然,对于自我来说,“‘死’不拥有‘未来’,而意味着‘在世
-
有限存在’之‘终结’,‘死’为‘去世’;然则,‘人’却有能力‘提前进入死亡状态’,亦即不必等到‘死’的‘时刻
-
点’,就能‘觉悟
-
警觉’到这种‘状态’,于是,‘人’不但‘必然’‘去世’,而且‘有能力’‘在世’时就‘出世’,‘人’有自身之‘超越
-
超然’之能力。”
[26]
提前进入“死”,乃是提前“超越”时间,从而进入“无时间”的“超越之境”,这里是“他者”和“神”所在的“空间”。在这样的“超越之境”中,人“直接”与“他者”、与“神”“相遇”,从而有能力以“超越”的方式再次与时间建立关系。此时,时间的依据已不再是“过去”或“现在”,相反,人乃是在“未来”重新建立自己:未来居于人之存在的首位。
于是,我们看到,自由的未来向度必定与“他者”和“神”(绝对的他者)相联系,这是宗教之根,也是人作为有限、“有死”者的“必然”“宿命”。
[27]
叶先生的一系列写作显示,“他者”进入了这些作品,而“神”(绝对者)则是或隐或显的。
[28]
叶先生把自我与他者的“相遇”把握为“不在场的共在”,即:死亡并非我的历史的终结,并非我作为存在者的完成,相反,他者乃带领“我”进入未来,进入“我”“不在场”的共同世界。同时,另一方面,“他者”也通过“我”的死,使“自己
-
自我”延续着“自己”的历史,即:“我”的生存意义同样进入他者的生命,“历史”乃是“我”与“他者”共同塑造的。
[29]
因是之故,叶先生以共同担待生命解释了基督教下的“救赎”观念和“神”的观念:救赎指的是他者“让”“我”进入未来、进入历史;“神”指的是共在的大写的“他者”。
在
2011
年完成的“人有‘希望’的权利”和“试析康德‘自然目的论’之意义”两文中,叶先生又以共在的“他者”——包含目的论意义上的自然——解释康德出于“希望”而预设的“神”。“希望”是对理性的“完满之善”,即德性与幸福必然结合的“权利”,是对理念之客观现实性抱有信心的“权利”。
[30]
鉴于自由存在者的共在,“我”与“他者”在无尽的未来中,完满之善的实现是可以指望的;同时,“经过康德‘自然目的论’的‘批判’将‘(自然)目的论’‘拉回’到‘自然’自身,‘从天上拉回(回归)到人间’”,
[31]
即自然的合目的性不在于外在的神,相反,它自身乃是合乎目的的,因而自然的幸福是可以在未来指望的。因此,按照这两篇文章的分析,叶先生认为,只需要洞见到“他者”的维度,人类生存的未来和希望问题就是可能的,而无需预设宗教意义上的“绝对者”。同样地,正是源于这种对哲学或理性的信心,叶先生认为,在这种“他者”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做出纯然理性的“预言”。
[32]
在《科学·哲学·宗教——西方哲学中科学与宗教两种思维方式研究》中,叶先生沿着这条思路细致而微地分析了基督徒的“信仰”“审判”“末日”“救赎”等观念。或许叶先生的这些解释无法说服有基督信仰的读者,但这却是汉语学界一次重要的尝试。无论如何,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是需要汉语思想界理解的,其被理解的方式也必定是多元的。作为一位哲学家,叶先生的阐释必然是从其自身的生命经验出发的,诚如先生在试图解释克尔凯郭尔时所说,“一直想努力去‘理解’克尔凯郭尔,但一直都‘知难而退’,不得不使我承认,我的‘思想世界’属于‘古典哲学’……借助它们,很冒昧地写下一些学习心得……”
[33]
这种谦逊和自知本身证明叶先生的真诚,也证明其写作的虔诚。我相信,每个人都能从真诚之人和虔诚的作品中感受到独特的思维力度。
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叶先生的“思想世界”属于“古典哲学”,他感受到了未来和希望之于人之自由生存的意义所在,也注意到正是自由的未来向度为思想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阐释海德格尔的时候,叶先生强调了“可能性”的维度;同时,在未来和希望的维度里,叶先生也“看到”“他者”之于“我”以及思想本身的意义所在,并试图从这个角度与宗教展开对话。但是,我们知道,“他者”确实是宗教的重要的对象,但“绝对者”的维度却是宗教的根基所在——甚言之,没有绝对维度的打开,就没有宗教。尽管可以沿着“他者”的维度揭示宗教之于“我”的意义,但“绝对者”本身的意义却未曾在这种解释中彰显。
因此,就哲学对自由的论述来看,叶先生的阐释和体察已经足够深刻,这是需要我们后辈学人学习的地方;就大地之于自由的意义,或反过来说,自由之于我们生存的大地的意义来看,叶先生也做出了足够深刻的工作;同样,就未来或希望之于人在大地上、在历史中的生存而言,叶先生也都为我们提供了思维的基底。但是,宗教中的绝对者之于生存在时间中的人的意义却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开拓的事业。
自由的未竟之业
叶先生对宗教的反思是哲学式的,对宗教观念的诸多解释和体察也是哲学式的;宗教及其观念也确实应该经历哲学或理性的深入考察,否则,我们无以区分宗教性的信仰和迷信——这一点对于当前中国信仰状况尤其重要。但无论如何,信仰对个人的“占据”却不是哲学式的或理性式的,即外在的对信仰的反思和信仰者对自己信仰的理性反思是两个问题。我想,叶先生真诚地对克尔凯郭尔说的那番话基本就是这层含义的表达。
信仰者是否自由呢?其自由与叶先生阐释的自由有何不同呢?换言之,信仰者能否为自由提供新的思维路径?《圣经》上说,信仰让人自由。古往今来的神学家们也不断地在为这句话做着注释。在现代语境下,我们该如何理解信仰中的自由呢?——在我看来,这是克尔凯郭尔所致力的思考方向,海德格尔也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接受了这种分析。毫无疑问,信仰者的自由以信仰为前提,否则就无所谓信仰。而所谓信仰,是在生存选择的尽头处对神的信靠,于是,神是人的生存的起点。其起点的意义不在于神直接告诉信仰者如何行——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更不在于根据某部经书“现成”地行——那只是自己对经书的解释而已;而是在于把自己所根据的“什么”(经验、观念等)放弃,全然地信靠神而行。
全然信靠不是不做判断,而是不以自己作为判断的依据;我们把这种状态的判断称为来自于神。因此,信仰中的判断或自由就意味着,放弃一切“现实性”,仅仅在信仰中面对来自于神的可能性,这是一种面对全然的或无限的可能性的生存状态。这正是克尔凯郭尔在《哲学片断》“插入章”中通过概念界定所分析的“生成”状态。
[34]
因此,信仰中的自由乃是面对无限可能性的生存状态,是从神出发做选择判断的自由状态——当然,一旦选择一种可能性,人也就离开自由而进入现实中。
在这样的自由中,人面对的是“绝对者”,同时也从“绝对者”出发面对其他“他者”。因而我们看到,这样的生存状态正好与叶先生所分析的生存状态相反。叶先生注意到海德格尔重视“可能性”,却没有看到海德格尔对自由之“可能性”的处理是来源于基督教信仰的。我想,把这两个维度都重视起来能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东西。毕竟,人既是自主的道德存在者,同时,有限性又是其不得不承担起来的宿命,而这正是信仰的根基之一。
无论如何,作为艰难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者,叶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出色、最深刻的哲学家,他对汉语思想界的贡献在我们这个时代,甚至倒退
200
年,都是首屈一指的。作为后学,在继承叶先生工作的同时,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我想,这也是叶先生最希望看到的!谨以此文纪念先生!
参考文献
克尔凯郭尔,
2013
:《哲学片断》,王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猛,
2016
:“‘出生入死’的智慧:读叶秀山先生有关《老子》的临终札记”,载于《中国哲学史》,
2016
年第
4
期,第
10-16
页、
128
页。
尚文华,
2016
:“从自主性到接受性——论施莱尔马赫的新宗教观”,载于《基督教思想评论》第
21
辑。
施莱尔马赫,
2011
:《论宗教》,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叶秀山,
1988
:《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02
:《中西智慧的贯通——叶秀山中国哲学文化论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03
:《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09
:《科学•哲学•宗教——西方哲学中科学与宗教两种思维方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9
:《学与思的轮回——叶秀山
2003-2007
年最新论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13
:《“知己”的学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13
:“从‘理智
-
理性’到‘信仰’——克尔凯郭尔思路历程”,载于《世界哲学》,
2013
年第
6
期。
——,
2015
:《哲学要义》,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6
:“读《老子》书札记”,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6
年第
1
期,第
15-22
页。
[1]
叶秀山:“康德的法权哲学基础”,载于《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34-36
页。
[2]
叶秀山:“‘哲学’如何‘解构’‘宗教’——论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载于《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第
151-15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