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图
盯着那个说要断我父亲几根肋骨的大汉,我捡起一根螺纹钢,冲过去对准他的脊背,用尽全身气力抡过去。大汉一声惨叫,众人的目光瞬间全部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父亲是个挺木讷的人,这几乎是所有家族成员的共识。
有一年,我和父亲一起看电影《那人·那山·那狗》,当电视上响起,“当儿子能背起父亲时,意味着他长大了”这句台词时,一向寡言少语的父亲突然嘿嘿憨笑起来,并自言自语道:“我儿也长大了啊!”
那是2008年的秋天。电视机前,父亲的表情如同平地里捡了一块金元宝,无限得意又满含欣喜。
这种反常的举止在父亲身上很是少见,当然也并非无迹可寻,一切还得从2007年的夏天讲起。
2007年的夏天,父亲还是一个农民工,与此前身份不同的是,他头上安全帽的颜色从蓝色变成了红色。这种颜色的改变,不仅意味着每个月的工资会多出200元,更重要的是他在工地上拥有了一点“领导权”。
照父亲的说法,他跟从工地老板多年,一直实心办事,老板是看上了他的老实憨厚,才让他当了个小领导。
父亲所在的工地工种很多,木工、钢筋工、架子工……工人们口音各异,木工多为宝鸡人,钢筋工多为陕南人,偶尔掺杂有陕北人,而架子工是清一色的四川人。
父亲是钢筋工,在行业历练多年,且比其他工人多长几岁,自然成了钢筋工种的“领头羊”。以往在工地上,父亲憨厚老成的性格,深得各个工种的工友尊敬,平日里有纠纷矛盾,大家也常请父亲出面斡旋协商。
然而,当“包工”这种劳作形式在工地上流行开来,父亲往日的“长者地位”瞬时便不复存在。那时候,建筑工地一改过去的按天算钱”,开始把工程任务分片承包给工人,工资则按照他们各自每天工作的完成量来计算。
为了挣得更多,所有工人都开始拼命干活,以工地里的川籍民工最为典型。一到“浇筑混泥土”的日子,他们将锅碗瓢盆、铺盖被褥直接搬到二十多层的楼顶,吃饭就在劳作地点,通宵达旦地赶工,像一个个攻城拔寨的悍将勇士。
然而,即便每个人都想多干,但塔吊只有一个。因此,当高楼修建到十多层时,每个工种干活所用的材料都要依靠塔吊从一楼运上来,建筑材料不到位,就算鲁班下凡也只能干瞪眼。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塔吊成了决定大家每天能干多少活、能拿多少工钱的关键。
围绕“塔吊”发生的纠纷不断增多,每个人都希望唯一的塔吊能优先运输他们工种所需的材料。工人们纷纷通过各种手段交结塔吊司机,那些比较强势的工种在塔吊使用权上常常获得先机,这让其他工种很是不满,殴打塔吊司机的事故也时有发生。
2007年夏天的某一夜,父亲突然从宝鸡返回家。他跌跌撞撞地闯进门,脸色苍白,双手紧捂腹部,豆大的汗珠从额角倾泻而下,让原本苍白的面庞越发吓人。母亲带父亲连夜赶到医院,检查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两根左侧肋骨有程度不同的损伤。
父亲说这是当天在工地的一场事故中伤到的,在他看来,那完全是一场有针对性的报复。
原来,工地上的塔吊司机是一个四川小伙,和“四川帮”交情甚笃,因此塔吊的运输总是“架子工”优先,这让其他工种甚为不满。尤其是父亲所在的“钢筋工”,每天有大量的材料需要及时运送进场,可等四川帮的架子工的活都干完了,临近中午,钢筋材料才得以运上高楼,工人们每日真正干活的时间,也只剩下了半天。怨怒的情绪在工友间蔓延,大家一致推举父亲去开发商处反映情况。
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原来的塔吊司机遂被解雇,整个“四川帮”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处罚。而父亲也自然成为“四川帮”的报复对象。
事发后第四天,父亲照例像往常一样上楼干活,当他攀爬钢筋架子通往楼层另一边时,冷不丁感觉脚下的钢筋迅速旋转了几圈,自己也迅速地从钢筋架子中间重重跌了下去,两根肋骨就是在下落过程中被钢筋磕到的。
事件发生后,父亲延续了他的木讷,并没有在工地过多纠缠,只是在回家养伤期间,对母亲多次谈到那个暗地里对他“下黑手”的工人情况。
那年,我刚满14岁,守候在父亲病床前,对父亲口中的那个人怀恨在心。出于恼怒、或者就是复仇的情绪,我暗自发誓,有一天,我一定要让这个人“血债血偿”。
父亲在家仅休息了不到两个月,自觉身体已无大恙,便又再次搭上长途汽车返回工地。
父亲受伤后,并没有因负伤之事纠缠,这样的行事方式,使得工地老板对父亲甚是赏识。待父亲重返工地时,立马就被指定为工地领班,职位不高,却能代表老板指挥工地上的所有工种,更多的是负责工种间的协调工作。
对于这样的安排,父亲欣然接受,他自己还常感慨,这是“因祸得福”。受伤后原本也干不了重活,能从一个出牛力的民工,成为了工地上的基层管理者,让他长舒了一口气。
2008年中考结束,我赋闲在家,便搭上一辆长途汽车去找父亲。
那时候,父亲已经在工地当了快一年领班。我想借此机会去瞧瞧父亲如今的新身份,父亲也有意让我到工地“锻炼锻炼”,提前尝一尝卖力气挣钱的艰辛。
而我心里很清楚,自己一年前在父亲病床前暗许下的“血债血还”的誓言,迎来了兑现的机会。
●
●
●
多年来,在父亲耳濡目染之下,有关建筑工地的事我并不陌生,但当我真正以一个“建筑小工”的身份进入工地后,才感觉到,所谓的“纠纷”原来是这样的。
白天黑夜的分际在工地上似乎不复存在,整个工地像一个按下开关的永动机,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其中挥汗如雨。从卡车把材料拉进料厂开始,所有的工种负责人屁股上挂着的那只讲机,就像被磁铁吸住了一般,伴随嘹亮的、口音不一的号子声轰隆隆往塔吊跟前聚拢。
父亲的身影立刻出现,他两手各拿一个对讲机,腋下夹一卷图纸,站在一堆钢筋或者钢管的顶部,一边通过对讲机和塔吊司机协商,一边则挥动另一只对讲机招呼簇拥上来的人群。
第一次遥望这样的场景时,我只感觉《狼牙山五壮士》里五位战士站立在悬崖峭壁上,鬼子从四面包抄上来的画面,正在上演。父亲在建筑材料堆成的“悬崖峭壁”上,孤身一人,嘶哑着嗓子,协调各种“急不可耐”的身影。当父亲的决断脱口而出,各种不堪入耳的谩骂与抱怨,像一颗颗射向狼牙山五壮士的子弹,以我父亲为靶心,统统发射过去。父亲身上,除了额头亮晶晶的汗珠,就只剩下因为高喊过度而嘶哑的嗓音。
事实上,自从他当了领班,嗓音常常是嘶哑的,被人群包围、接受肆意的谩骂,成了他每日必须完成的工作。我除了心疼,剩下的全是陡然而生的愤怒。
半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临近下班,工地上新来了一批材料。
原本打算下班的工人们看到材料,如同打了鸡血一般,纷纷要求连夜加班。这批材料中既有钢筋工的材料,也有架子工的。然而,当一车材料最终被放置到料厂时,钢筋工的材料恰好埋住了架子工的材料。大家一如既往地聚拢在材料周围,父亲一如既往地站在材料顶部。一片骚乱中,父亲决定,塔吊先吊钢筋工的材料,再吊架子工的材料。
这本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决定。然而,“四川帮”的架子工立即聚拢在一起,强烈抗议起来。钢筋工和架子工两军对垒,各不相让,一时半刻也不敢有大的动作。
谩骂不出所料地汇聚到我父亲身上。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半裸上身的中年大汉冲上前去,身上的肌肉突兀而健硕,和我父亲瘦削的身躯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对父亲吼道:“凭啥先吊钢筋料?凭啥?”
“钢筋料压在钢管上面,只能这样吊。”父亲的语气依旧是不温不燥。
“放屁!老子今天就要先吊钢管!”
父亲一时无语,不再理会他,转身招呼钢筋工往钢筋料上套锁,准备运料。
这个四川籍民工一步跨上前,猛推了父亲一把,父亲向后踉跄了几步,“你今天敢先吊钢筋料,就让你龟儿子再断几根骨头!”
那时,我就站在人群中间,川籍民工这句话如同钢针扎进了我的耳朵,我心中积攒许久的怒火瞬时点燃。
川籍民工对父亲的攻击持续升级,连那位民工的媳妇都一同加入了进来,她指着父亲的鼻子口吐污言秽语,父亲极力争辩却始终无果。在一大群川籍民工的引导下,一场关于“运料次序”的纠纷矛盾,升级为“四川帮”针对父亲的指责。
夕阳从楼宇之间穿透过来,将父亲单薄摇晃的身影割碎,我愤怒的情绪此时也升级至于顶点。
盯着那个说要断我父亲几根肋骨的大汉,我捡起一根螺纹钢,冲过去对准他的脊背,用尽全身气力抡过去。大汉一声惨叫,众人的目光瞬间全部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殷红的鲜血从他脊背扑簌簌流下来,将他红色的内裤边缘染成了黑红色。
我余怒未消,想到父亲一年前苍白的脸,想再上前给他一棍,但即刻就被其他工友死死拦住了。“四川帮”对父亲山呼海啸般的谩骂骤然间停止,尤其是被我袭击的壮汉坐在地上尽可能往后缩退,那个对父亲口吐污言秽语的女人,搀扶起他的男人,一边抬眼看我,一边赶紧往人群后面钻,眼神中有恐惧,也有诧异,还有惊骇。
事实上,不仅仅是他们,事后回想,连我自己都惊觉诧异,那时的自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然而,深感最为诧异的,还要数我父亲。
川籍民工的伤势并无大碍,钢筋未能伤及他的脊椎。但他们并不甘心,打算借此事件狠狠报复一下父亲。原本三天便可出院,那大汉在医院一躺就是二十多天,父亲每天拿着各种缴费单子在医院跑进跑出,上下照顾着。
那天,当我把钢筋抡向那个大汉后,父亲第一反应,如今想起,仍让我揪心不已。他并没有愣在原地,也没有翻过身给我一巴掌,而是直接站在我和壮汉之间,把我紧紧地护在他身后。
一个多月后,川籍民工才满足地出院了,留给父亲的只有厚厚地一沓医药缴费单。由于是我闯的祸,医院的花销工地并不负责,全部由父亲承担。当我看着父亲在其他工友面前躬身借钱时,我才知道,自己这是闯了大祸了。不仅如此,在此期间,“四川帮”还向工地举报了我父亲。
让我利用暑假到工地锻炼是母亲的意思,父亲本不同意,但拗不过母亲和我,勉强默许了。然而当时我只有15岁,尚未成年,算是童工。四川帮便以此为借口,举报父亲私用童工,给工地造成安全隐患。
这样的理由父亲无可辩驳,被罚了半个月工钱后,我也随之被工地扫地出门,提前结束了锻炼计划。离开那天,父亲帮我整理好书包,送我到车站。
农历七月,滚滚热浪灌满城市的大街小巷。父亲和我蹲在车站对面的道牙子上,他抽着烟,手里捏着的冰峰瓶子一直滴着水。用后槽牙咬开瓶盖,递给我,父子二人似乎与城市骄阳下的匆匆行人格格不入。我背着书包,一脸土气,父亲卷起裤边,一身穷酸。
“爸,我这次给你闯祸了。”
“是祸躲不过,不要紧。”父亲说。
“以后那些人又报复你该咋办?”我忧心忡忡。父亲没有说话,仰起脖子喝了口冰峰。
“怕啥咧?咱们不惹事,但事来了也不怕事。兔子逼急了也咬人,咱们也不是怂货!”父亲笑了笑。
我知道父亲话中的意思,他这是在变相赞许。
两个月后,我升入高中,父亲也从他所在的工地辞职。
我不知道父亲突然辞职的缘由,或许和我有关,或许无关,我只知道父亲从事的工作很累。
周末放假回家,父亲提议我陪他一起看他新买的电影光盘。他熟练地操作DVD,迅速点开其中的一部《那人·那山·那狗》。
我陪父亲随电影情节推进,对电影片段评头论足,大多时候,我的发言内容都是对电影年代、画质的抱怨,嘲讽父亲花10块钱买回来的盗版,而父亲依旧“木讷”如故。
电影中的父子踏上送信的山路,一条碧溪横亘路前,老邮差的儿子背起邮差,望着儿子的脊背,老邮差泪花闪闪,小邮差说:“你背了我那么多次,现在我长大了,该我背你了!”
那时,我父亲突然而至的笑声泄漏了他脸上飘来的欣喜神情,他自言自语道:“我儿也长大了!”
那时,父亲眼中是否也满含泪花,我真的没有看清楚。
编辑:沈燕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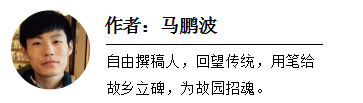

本文系网易人间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email protected],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千字500元-1000元的稿酬。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人间,只为真的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