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灵魂巫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楚辞《招魂》,民间的灵魂信仰一直绵延不绝。但在乾隆三十三年,中国突然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叫魂”妖术恐慌。这场恐慌如何爆发?何以在此时此地?时人如何看待?孔飞力(
Philip A. Kuhn
)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 :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细致刻画,揭露了1768年大清帝国的社会状况与政治运作逻辑。
撰稿丨曾天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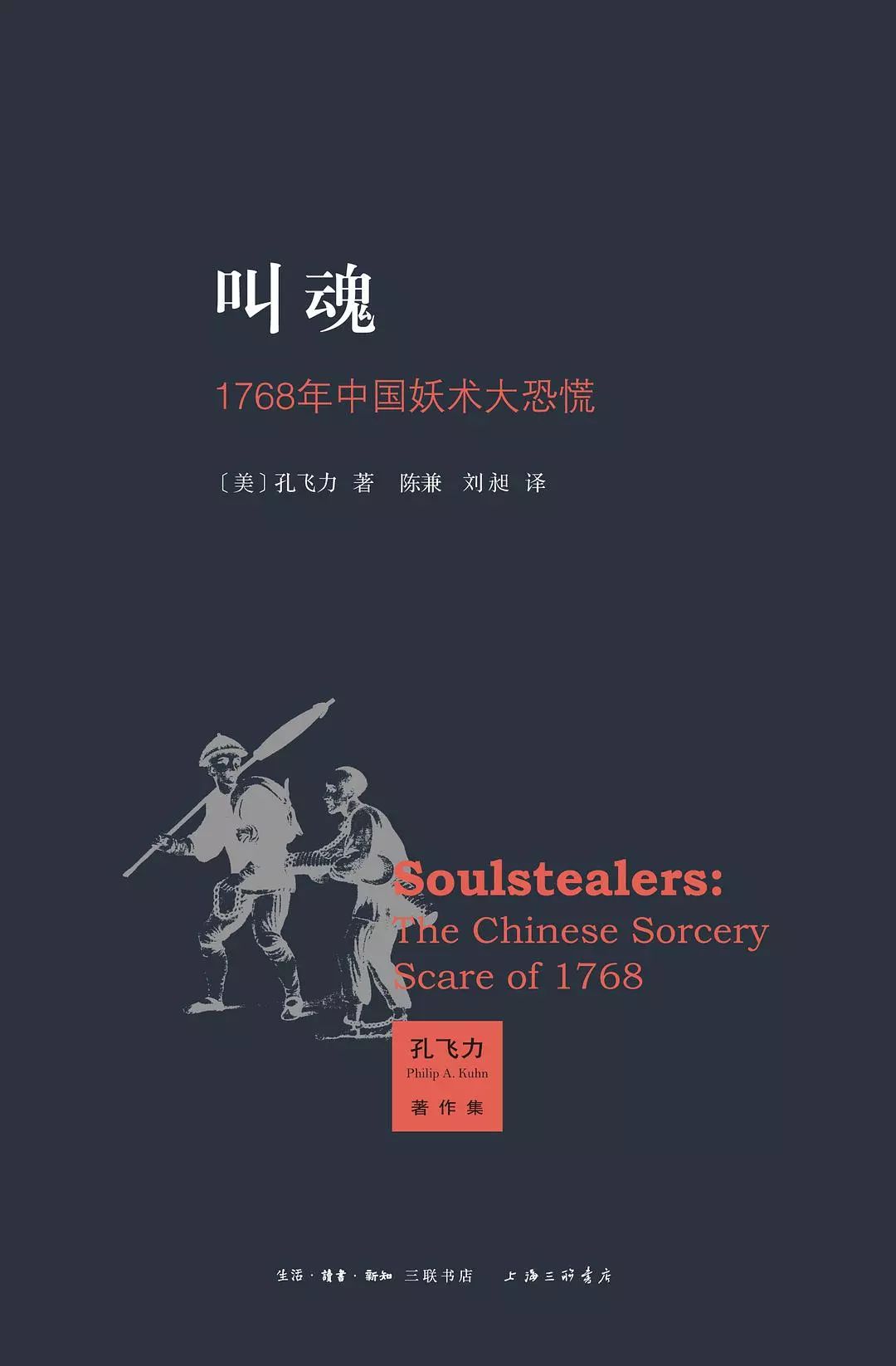
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从初春到仲秋,一场关于叫魂的妖术恐慌席卷华夏大地,弥漫于社会各阶层。先是在浙江,传言石匠会将活人名字写在纸片上,贴在石桩顶部,为锤打增加力量,而名字的主人将被窃取精气,非病即亡,这就是“叫魂”。一个叫沈士良的农夫找到负责德清水门工程的吴石匠,想借此对付两个暴虐的侄子。石匠不会叫魂,而将此事报告给当地保正,沈士良吃了板子。
当时,类似的“叫魂”案在浙江各地层出不穷,一些人被指施展“用药迷人”、剪人发辫等妖术,但这些案子最后都被判为诬告,王朝统治阶层波澜不惊。直到六月中旬,山东巡抚上报了几起剪辫叫魂案,皇帝这才知道“叫魂”妖术的存在,而且已经从江浙蔓延到北部、西部各省乃至京畿。
天子震怒,指责官员欺上瞒下,要求彻查幕后主使,一场全国范围的妖术清剿运动浩荡展开。施妖术者后来甚至被定性为“谋反”,形势不断升温。在乾隆的严厉催促下,各级官僚忙于搜捕、审问了近五个月,最后却发现大部分案件是屈打成招或另有隐情的冤案,清剿运动尴尬收场。
以上只是对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粗线条描述,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勘察,指出君主、百姓、官僚基于对同一经验有不同的表述(representation)。
生活背景和认知结构差异导致个体对于妖术的关注点各不相同,一方面恐惧着妖术可能带来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利用社会的妖术恐慌达成各自的目的。
在考察不同版本的叙述时,我们还可以发现对妖术的恐惧是如何在复杂而庞大的社会中跨阶级传播,以及更多微妙的事实。
民众的担忧:生命的重要性与证据的模糊性
奥尔波特曾在《谣言心理学》中提出过一个谣言强度公式:R~i×a,即流行谣言传播的广度会随着这则谣言对相关人员的重要性乘以该主题证据含糊性的变化而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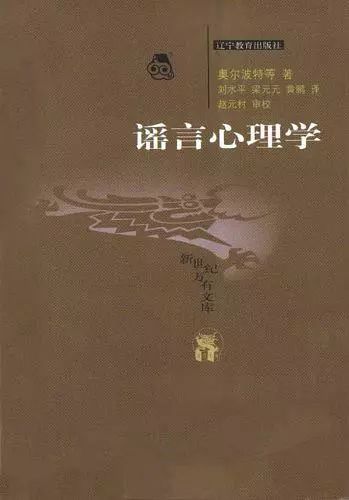
民间对妖术的迷信和恐慌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人们就相信灵肉可分离,如果灵魂离开躯体时间过长,人就会生病、发疯甚至死去。而术士可以偷取灵魂,谋人性命,借助的工具除了纸片,还可能是受害者的名字、生辰八字或者身体的某一部分(如头发)。在德清县石匠的案子中,沈士良就是想用写着侄儿名字的纸片施害。因此,民众对妖术的恐慌,直接源于对自身生命安全的担忧。
而社会各群体中,最有可能谋害人命、因此最受怀疑和排斥的,是以僧道、乞丐等为代表的陌生外地人。乾隆时期,表面上的经济发展、商业繁荣无法掩盖人口增长、物价上涨对普通人生存空间的挤压。
即使是在所谓富庶的江南,仍有很多山区百姓生存艰难。
与此相应的,是人口向外和向底层的流动,社会涌现出大量流浪者,其中一部分沦为下层僧道人员和平民乞丐。在官僚心中,流浪者意味着对公共安全的威胁,他们居无定所,难以追踪,“忠奸莫辨”;在百姓心中,流浪者在社区中缺乏联系纽带,缺少社会制约和对社区的责任感,带有天然的危险色彩。此外,流浪者还因僧道、术士、乞丐等具体身份承受着原因更为复杂的成见。

图:江南小城
不过,带来恐慌的同时,“叫魂”谣言竟也为普罗大众提供了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在人均资源恶化、道德堕落、司法不公问题凸显的社会,
人们无法指望通过个人努力竞争社会资源。而利用人们对叫魂的忌惮,任何人都有机会操纵大众的认知,这是一种权力补偿。
最初的“叫魂”谣言,似乎就是由慈相寺的潦倒和尚散布的。他们谎称石匠在山中作法埋丧,
上山往观音殿进香将遭毒害,借机抢占观音殿的香火;河南“刁徒私将父财妻物花用无存,遂自行剪辫,称被人所割,钱物亦被夺去”,将妖术作为散财借口;“顽生逃学,自行割辫捏称致病”,作为逃学借口……“叫魂”谣言愈演愈烈,与人们对这种微型权力的“充分利用”紧密相关。
“叫魂”谣言酝酿于中国古代数千年的灵魂信仰和渐露颓势的大清社会,下层民众为个人利益编造的谎言在民间信仰的沃土中如野草般芜杂生长
。
起初由于地方官员的压制,谣言似乎并未闹得满城风雨,但由于谣言的源头尚未清晰,妖术又事关个人安危,治标不治本的打压并不能阻止谣言在民间的流传,随着谣言传播范围的扩大,其严重性也逐渐增加,为日后官方大张声势的清剿埋下了伏笔。
君主的焦虑:二级传播语境下的谣言强化
和民众担心生命安全不同,君主焦虑的主要是“叫魂”妖术对政权的威胁。在古代中国,神权与君权统一,术士擅自与神灵世界联系冲击了神权垄断。君主的另一个焦虑点在于:为防止剪辫“叫魂”术,一些人率先自除发辫,而辫子是满族统治者确认臣服的重要依据,于是乾隆开始相信,“叫魂”妖术和剪辫防范的传言都事关谋反。

图:乾隆画像
事实上,与其说是妖术威胁政权,毋宁归罪于妖术引发的骚动。不论是否真实有效,妖术都可能煽惑群众,引发民间动乱,从而更直接地影响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自古如此。
妖术之外,官员的腐败和低效也让皇帝头疼不已。他六月才从山东巡抚的奏章中得知妖术的消息,而案情指向的江浙地区都不曾上报,是为欺瞒;下令清剿以来,各省官员迟迟无法捕捉到“大术师”,是为无能。
大清已走进帝制后期,长久以来皇帝都对官僚体制的“常规化、汉化、江南文化的毒化(放纵、推脱、徇私、浮靡等)”怀有深深的焦虑,叫魂危机为肃清官僚作风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他不厌其烦地严饬属下、重申官场规范、强化超越君臣的个人关系,有意无意地趁清剿运动集中发泄了对官僚体系的不满。
某种程度上,正是对官僚系统的不信任使他对“大术师”的存在深信不疑,这才将对妖术的恐慌自上而下传播开去,使这场闹剧持续到十一月。
妖术恐慌源于民间,通过山东巡抚的上报传递到最高统治层,君主从中解读到的是政权的危险信号——
民间和官僚系统均存在威胁,谣言的杀伤力立刻放大
。大动干戈的清剿活动反过来向民间坐实妖术的恐怖,虽然君主一开始竭力避免将妖术与谋反结合,叮嘱官员在访查中不要惊动民众,但这或许也增加了清剿行动的不透明度。
君主与民众无意识地相互影响,使谣言从酝酿阶段走向了爆发和扩张。
官僚的压力:谣言跨界层传播的主要渠道
“最不精彩”的版本——孔飞力这么评价官僚版本的叫魂故事。作为知识分子,官僚对妖术大多采取不可知的态度,或许可以说,他们位于妖术恐慌的传播链末端。他们既能运用理性判别案情,不随众迷信,又无需像皇帝那样劳心政局。然而另一方面,他们既不得不审查案件,平息百姓对妖术的恐慌,又要承受君主焦虑的指令和斥责。威吓提出妖术指控的人似乎不太奏效,对君主封锁消息也失败了,面对荒唐棘手又势不可挡的“叫魂”案,官僚们采取了各种方式抵制。

江西巡抚在10月初称已经针对妖术布下严密落网,然而似乎直到清剿中止,江西都未查到一起剪辫案,
所谓的天罗地网或许只是虚张声势;江苏按察使则忙于严打苏州禁教,这些与“叫魂”妖术未必有关的教派,成为官僚转移皇帝视线的牺牲品;湖广总督亲临省府,参与妖术案审判,与省高级官员联合上奏,以求法不责众;南京布政使奏请整顿保甲制度,“将紧急、非常规的要求导入习惯的、日常的轨道”,从而逃脱直接搜索案犯的责任……
这些应对手段有的蒙混过关,有些被斥为空言,官僚版本的故事没有诡谲的恐慌和精彩的真相,而是充满无奈,因为皇帝要他们搜找的妖首并不存在。即使皇帝最后终于意识到这一点,受处罚的依然是误导君主的山东巡抚和沾染江南堕落风气的一众官僚。
从谣言传播的层面分析,官僚是谣言跨阶层传播的主要通道
。有趣的是,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妖术恐慌的绝缘体,也无意助推谣言,但依然发挥着上传下达的功能。而由于立场和认知能力不同,官僚自身对妖术不可知的态度却不被其他双方接受。
事实上,如果官僚们能够找到谣言的源头,梳理出谣言传播的脉络,或许能有力地证明谣言的虚妄,更早地阻止其传播
,但囿于整个官僚体系并不高明的运作方式和专制制度中官僚话语权之微,离真相最远的皇帝没有给他们机会。
总结
孔飞力分析了皇帝、官僚、百姓三个版本的叫魂故事,可以看到,百姓的恐慌是皇帝焦虑的来源之一,而皇帝的兴师动众无疑使官僚压制谣言、息事宁人的努力功亏一篑,百姓和皇帝的不安相互滋养,反而是官僚群体认识到了真相,并最终由位高而忠直的士大夫劝止了这场闹剧。书中没有独立叙述僧道乞丐版本的故事,大概是因为他们比官僚版本的故事更为无趣吧,作为妖术清剿运动直指的对象,在集体污名化的背景下,受到百姓和皇帝合谋的攻伐,只有对妖术持不可知态度的官僚能为他们提供微不足道的保护,但谁知道官僚何时也会把他们当作转移压力的靶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