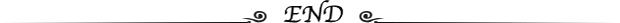【欢迎朋友们转发至个人朋友圈,分享思想之美!】
作者:王建香(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英美文学与翻译硕士生导师)
批判极权主义是20世纪中上期反乌托邦小说的重要主题
如果说,反乌托邦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得以形成,是基于19 世纪末人们过于夸大科技与社会进步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物质便利,而往往忽视它们同时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很多作家通过虚构比现实更令人恐惧的敌托邦社会以警醒读者的话,那么,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种社会动荡、战争威胁、经济垄断、极权政治使得人性受到严重摧残甚至完全丧失这一可怕事实,造成全世界范围前所未有的焦虑和恐慌,则使得反乌托邦小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对科技垄断和权力监控等社会弊端的批判是20世纪上半叶反乌托邦小说的共享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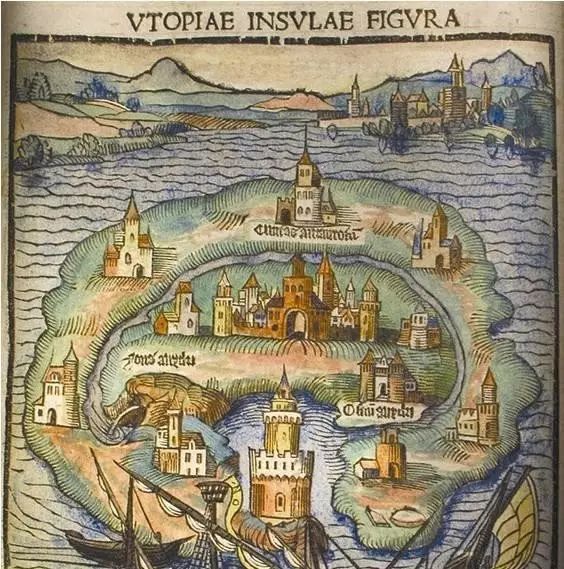
“Utopia”一词出自托马斯·莫尔的拉丁文长篇小说 《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简称《乌托邦》,1516年),是莫尔根据古希腊语虚构的,用来命名其虚构的岛国。图为《乌托邦》书中插图。
莫尔的《乌托邦》中的理想社会不是因为那里的人“具有比其他人更好的材质或天性”,而是因为“他们的法律法规、培养机制、生活条例使人向善的自然能力得到更有效的发挥,而其向恶的天性得到抑制。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健全合理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是乌托邦民众具有公民道德的原因,而非相反;他们的制度是他们良好品质的创造者而非创造品”。
但是由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的心理留下了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痕,莫尔小说中的这种个人绝对服从集体、公共利益为最大利益的思想受到质疑。人们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其中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由此引申的极权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成为20世纪中上期反乌托邦小说的重要主题。在莫尔、威尔斯等作家笔下的乌托邦世界离不开一个有序、强权的政治体制,而在反乌托邦小说中,强权政治,即少数人的至高权力,恰恰是以剥夺大多数人的个性、为社会制造痛苦和悲剧为代价。
反乌托邦小说的兴盛很大程度上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结果
早在20世纪初,英国小说家罗伯特·本森就在其反乌托邦小说《世界之王》(1908)中讽刺了威尔斯《一个现代乌托邦》中的所谓“世界国”,揭露了它技术至上、信仰缺失、人心麻痹的社会现实,并且表达了对世界会由此终结的担忧,尤其对其中以和平之名攫取政权、以真理之名毁灭信仰的独裁政治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批判。《我们》中的玻璃房、《美丽新世界》中的基因处理技术、《一九八四》中的“电幕”似乎也都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所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利用都是为了极权政府打压、消灭个性甚至人性。在被弗洛姆称为“最早的一部现代敌托邦”、为奥威尔《一九八四》中以“老大哥”为首的极权政府埋好伏笔的杰克·伦敦的《铁蹄》中,一个在政治上独裁、经济上垄断的敌托邦“铁蹄政府”,为了维持其权力永久化,一方面通过使中小型企业破产、使农民沦为农奴而自己成为最大的“垄断托拉斯”,另一方面利用残忍的镇压手段排除一切异己力量来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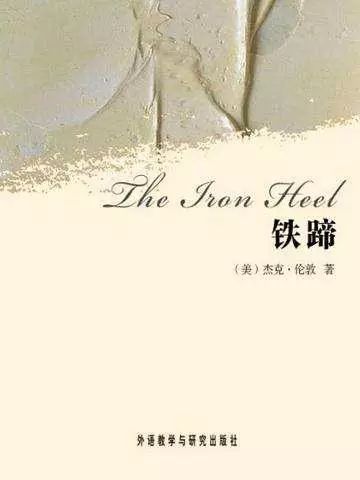
杰克·伦敦的政治幻想小说《铁蹄》是一部有关革命题材的作品,描述了美国垄断组织到高潮之后向寡头统治发展的过程以及工人们的反抗。
由于反乌托邦小说在20 世纪上半叶的兴盛很大程度上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结果,因此反法西斯极权成为反乌托邦小说的一大主题。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的《不可能发生在这里》(1935)写在“二战”纳粹法西斯践踏人性之前,其中描绘了一个压制人性、强制顺从的伪民主的法西斯主义敌托邦,表达了保护自由和批判精神比保护任何社会制度更为重要的写作目的。而反法西斯主义主题更是成为20世纪30 年代英国反乌托邦小说的“主旋律”。玛格丽特·杰姆森的《来年》(1936)、凯瑟琳·博尔德金的《卐之夜》(1937)以及鲁斯文·托德的《在山上》(1939)等,都将小说背景设定为一个高压统治下的法西斯主义国家。
而以扎米亚京的《我们》为代表,数量更多的反托邦小说则将矛头对准苏联的极权。它们批判的不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注定是邪恶的、愚蠢的政治形态,而是在警告,当一种政治体制,虽然其初衷甚至终极目标并无恶意,但一旦它被扭曲、被滥用,甚至打着达到终极目标的旗号采取残酷的压制手段后所带来的灾难性结果便是:“魔鬼的力量控制了这个世界,原本熟悉的行为准则和道德原则,都以‘正义’的名义被重新评估,善意即残酷,残酷即善意。”虽然大多数反乌托邦小说并没有给敌托邦世界指出一条明确的出路,但是都隐含着一个教训:只有理性地集中权力并尊重个体差异,保持个体创造性,人类社会才有可能避免类似灾难性的悲剧,才有可能真正向前发展。

扎米亚京(1884-1937),俄国白银时代小说家、剧作家和讽刺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我们》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1984》并称“反乌托邦三部曲”。
虽然前有威尔斯的《时间机器》、杰克·伦敦的《铁蹄》、福斯特的《大机器停止》等许多杰出反乌托邦先锋,但被《大英百科全书》称为“一个全新的现代文学类型——反乌托邦小说的开创者”的扎米亚京,其代表作《我们》通常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反乌托邦小说”。在这部小说所描绘的世界中,大一统王国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由百万个细胞构成的有机体”。它在“大恩主”领导下,由机器、国家护卫局监控,由卫生局、手术台根除幻想病,由立方体刑台、气钟罩对任何异己进行惩罚、行刑,以确保大一统王国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
小说中,似乎大一统王国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一切“破坏幸福的敌人”都被严惩:I-330 和她的试图谋划推翻大一统王国的地下反抗组织被镇压,一时受“蛊惑”的D-503 也被强制改造恢复了正常生活,并向大恩主“坦白”了罪行,交出了自己的日记,实现了自己“理性”的重新回归。但是,该小说在其悲观基调之下,仍藏有“可能性空间”,甚至“第三空间”。虽然D-503 最终被改造,但他还是有着一般人没有的“灵魂”和较为独立的自我世界。因此,记载他从异化到反叛意识的萌芽、挣扎及形成的日记,藏有美学历史典籍、唯一不透明、能处于监管盲区的古老房子,虽被折磨但至死不屈的I-330 所代表的追求自由的精神,尚未被他们“大一统”宇宙飞船征服的“外太空”等都表明:在看似严丝合缝的极权政治权力的反面,仍有着一股颠覆的力量存在。
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描写的权力中央化可以说是极权主义的缩影:“党所描绘的理想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可怕的和光彩夺目的世界。……人们迈着绝对一致的步伐前进,全都有同样的想法,呼喊着同样的口号。……三亿人有着同样的面孔。”它展现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权力控制机制。科学似乎并未给“大洋国”的人民创造丰富的物质生活,其世界也远没有《美丽新世界》那么“幸福”:“这世界充满着恐惧、背叛和痛苦,这世界充斥着践踏和被践踏”。尤其荒谬的是,大洋国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主要是促进人民团结、忠于国家的宣传手段,与对真理、历史和人的思想的控制一道,都是为了达到权力垄断这一终极目的。大洋国中只有一个政党,即所谓的“英社”;政府机构分为四个颇具反讽意义的部门:负责战争的和平部,负责维护秩序、掌控酷刑室的友爱部,负责宣传文化和教育的真理部,负责定量配给的富裕部。在大洋国里,所有人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政治考虑”,无论是篡改历史还是创造“新语”,抑或是强制人们运用“双重思想”控制现实、战胜记忆。而小说中不断重复的“党”的三句口号:“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是其“双重思想”的实践。《一九八四》中,追逐和获取权力不再需要打什么幌子,小说展示了统治者对权力的赤裸裸的崇拜。如果说《美丽新世界》中是通过使人无知换来顺从的话,那么《一九八四》是以洗脑的方式,通过篡改历史来“重构”真实并最终控制人的思想。

根据乔治·奥威尔同名反乌托邦小说改编的电影《一九八四》剧照
同时,个体的一切除了服务于集中的权力外,不仅毫不重要而且被认为非常有害。任何人不能有任何隐私,连思想都不行。所有人都无时无处不在被监视中,你的家人、朋友随时可以向思想警察揭发你反常言行使你“人间蒸发”。如果《我们》和《美丽新世界》像奥威尔所说,“都描写了朴素的人类精神对一个理性化、机械化和无痛化的世界所进行的反抗”的话,那么《一九八四》就使这一主题走向了极致。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则呈现了极权主义的另外一面:一个以福特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特征的“真正高效、幸福的国家”。在“美丽新世界”里,虽然没有了暴力、犯罪、饥饿,有的只是稳定的国家、丰盈的物质和幸福的感觉,但同时人们也被剥夺了个人情感,失去了爱情,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经历危险的感觉,最可怕的是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和创造的动力,一切完全受控于顺从机制。在这里,肆虐的科学不再具有任何伦理约束,它成为国家机器最大的帮凶,全面压制自由,控制人们思想。也难怪有的文学评论家指责《美丽新世界》格调太黑暗,缺少在危机时代给人以道德启迪的力量。连赫胥黎自己也承认,如果让他重写该小说,他会更乐观些。也许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在《美丽新世界》发表20年后,要以“生态乌托邦”《海岛》作为“补偿”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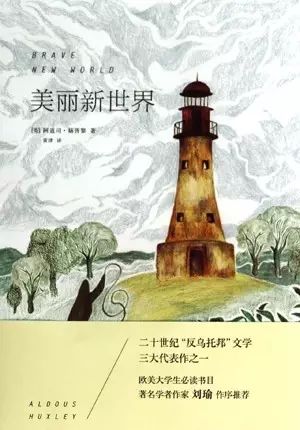
《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为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于1932年发表的反乌托邦小说。
《美丽新世界》中,聪明能干、不满于每天为“世界国”写些规定内容的赫姆霍尔兹最终宁可选择被放逐到一个气候极端恶劣、整天狂风暴雨的孤岛,也认为会写得比现在好,过得比现在更有意义,虽然他暂时也不确定这些更好的东西是什么,也尚未找到合适的描述方法。来自保留区的“野蛮人”即使被最高领导人穆斯塔法威胁说,放弃文明等于是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要求衰老、丑陋和阳痿的权利,要求害梅毒和癌症的权利,要求食物匮乏的权利、讨人厌烦的权利,要求总是战战兢兢害怕明天会出事的权利,要求害伤寒的权利,要求受到种种难以描述的痛苦折磨的权利”时,也不愿牺牲自己对文学、艺术、道德、个性、信仰的追求。“野蛮人”的这种反理性、反对所谓完美的科学乌托邦的行为正是对人性的最后保留。而由于对曾经憧憬的现代文明彻底绝望,他选择逃离,独居于小山顶上的一座旧灯塔,最后宁可自杀也不愿意苟同。“野蛮人”的自杀本身就是对所谓“美丽新世界”最有力的质疑,让读者看到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在批判极权主义奴役人性的同时传递出一种微弱的反叛的力量和希望。
代表20 世纪上半叶反乌托邦小说的最高成就,被库玛盛赞为“没有哪一种极权主义理论,也没有哪些对科学傲慢或技术威胁提出的真心警告,可以比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或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更能表达对20世纪社会的想象了”,虽然《我们》《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在小说生产背景、内容主题、故事发生时间地点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它们对极权主义的表征却有着惊人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特征。
在极权统治的方式上,反乌托邦小说中的霸权社会通常通过政府的高压政治和人民的自觉遵守双重策略得以维持和巩固,即其权力的控制手段为政府强制与民众共识相结合。极权统治一方面通过暴力手段得以维持,个体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而且任何人都没有选择的权利,如《我们》和《一九八四》中利用酷刑来镇压叛乱、改造异己思想,另一方面同时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文化霸权是极权统治得以稳固的另一手段。《美丽新世界》中的反智主义,《一九八四》中的改写历史等,都是通过文化宰制来达成霸权统治。同样,三部小说中的个性受压制方式的外在表现也惊人地相似:身着整齐划一的制服,似乎所有人都是高度一致的物类,而非各具特征的个体。小说中国家机器对人的控制无所不在。无论是在《我们》中的“大一统”王国,《美丽新世界》中的“世界国”,还是《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国”,无论是极权主义对人性的控制,还是对科技的垄断,无论是对个人情感的压制,还是对语言的控制,抑或是对思想意识的控制,总之在敌托邦世界中的极权主义统治下,个性追求与社会价值势不两立;因此,个人反抗就好比蚍蜉撼树,其失败结局早已注定。
极权统治还通过有效控制人的身体、剥夺个人身体的基本需求为手段得以实施,任何成年人的行为和思想都被视为冒天下之大不韪。它不仅强制一切必须服从于极权,对追求爱情、婚姻的个体行为等大肆扼杀,而且还对男女两性的生理需求加以控制。《我们》中,两性之间只有拥有政府分配的配给券才能行使性权利,而且只能在透明的玻璃房中进行;《美丽新世界》中却截然相反,统治者深知“未经抑止的水流”反而能“平静地流入指定的通道,进入平静的幸福中”,因而鼓励彻底自由的性放纵来达到使人民臣服并安于现状的目的;而《一九八四》中,虽然像《我们》中一样采用的是压抑的手段,但使用的是另外一种逻辑,认为人们如果“缺乏性爱就会引发歇斯底里,而这是党所希望的,因为这股力量可以转化成对战争的狂热及领袖的崇拜”。总之,不管它们采用何种荒唐的手段,都是对人的正常感情的压制,并以此达到维护极权统治的目的。
虽然小说中各种反抗大多以失败告终,或至少举步维艰,似乎人物的反抗只不过是一段无伤大雅的小插曲,但是这并不代表反乌托邦小说作者们对人类文明已经绝望。正如福柯所说,任何权力都具有形影不离的两面,虽然敌托邦社会采用各种压制手段,但是小说中仍然或明或暗地标示了反权力的存在。希利加斯在谈到扎米亚京、赫胥黎和奥威尔的三部反乌托邦小说的震撼性,以及受它们影响所形成的反乌托邦“洪流”时甚至说:它们是“最能揭示我们时代焦虑的指数之一”。它们仍能使读者感受到,虽然目前人类对社会进步的曲解已经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他们依然相信,人最终一定能渡过难关,成为战胜“过度发展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的“英雄”。因此,小说中的荒凉景象并不代表绝望,“而是代表他们对不自由之恨有多深,对自由能够永恒、自由的价值能够高扬的渴望有多大”。
“二战”之后,虽然大多反乌托邦小说不再是单纯地反法西斯主义或反苏联,但反极权主义依然是其一大主题。大卫·卡普的《大一统》(1953),其主人公坚信自己是“仁慈国家”制度坚定的支持者,却被当局怀疑是“异教徒”。故事讲述了当局通过对其采取监视、抓捕、再教育、洗脑等方式,最终使其根除异己思想的漫长过程。柯林斯《饥饿游戏》中的“国会区”是一个象征着权力和财富集中地,统治者通过对其辖下十二区采取高压统治的方式来稳固自己的极权统治。

根据柯林斯小说《饥饿游戏》改编的同名电影中的“国会区”
与手段残忍、违背民意,因此无能低效为特征的独裁暴君统治不同,反乌托邦小说中的极权主义大多是以提倡平等、普世幸福、文明、世界大同等崇高、“完美的”理念为幌子,而逐渐达到驯化人民、攫取和维持权力的终极目标。无论是法西斯极权抑或是苏联的极权,他们都声称自己掌握了这个世界的绝对真理。
因此,极权主义是在善的名义下,以善良为借口作恶,即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所说的“根本恶”(radical evil),“采纳恶的准则,把出自道德法则的动机置于其他非道德的动机之后”,这是一种“心灵的颠倒”,也是善恶准则和伦理秩序的颠倒。在极权主义反乌托邦小说中所表现的是,少数的精英统治阶层对整个社会的监控和系统化控制、对占大多数的民众的压迫,以及对人性的压制和践踏。整个社会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打着“有机社会”幌子的独裁者、极权政府和社会机制对法律、规约等的有效执行甚至强制执行,它成为给人类带来痛苦、导致人性扭曲的罪魁祸首。
与乌托邦小说通常强调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区别以彰显前者的优越性不一样,反乌托邦小说却好似残酷现实的自然走向,使读者时时观照现实,通过小说警示现实,反思现实,尽快采取对策,不然小说中虚构的恐怖世界就将成为现实。以扎米亚京、赫胥黎、奥威尔和阿特伍德的小说为代表对极权主义噩梦的表征,给读者带来的不只是乌托邦式的“陌生化体验”,而好似当头棒喝,又好似噩梦初醒,唤醒读者对滥用权力的警惕。
(本文选自《反乌托邦》,王建香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编辑:陈菲。腾讯思享会获出版社授权刊发,文章标题、小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王建香,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英美文学与翻译硕士生导师。湘潭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本科毕业,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毕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毕业。获国家留学基金项目,2014-2015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英文系访学。一直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教学,长期从事当代西方文论、文化研究与英美文学研究。近年主攻现代小说兴起与繁荣之时的18世纪英国小说,以及19世纪末以来的英美乌托邦/反乌托邦小说。研究特点为:将语言学的语用学、尤其是言语行为理论运用于文学批评和研究,关注作者通过虚构手法的现实关切,关注虚构作品的述行之力,关注文学与现实的互文特性。出版专著2部(《反乌托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当代西方文论中的文学述行理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在《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国外社会科学》等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十多篇,其他刊物上发表论文、译文近20篇。
图书简介

《反乌托邦》,王建香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16年10月版
反乌托邦(anti-utopia),作为一种讽刺和批判手法,一直与乌托邦如影随形,而作为一个19世纪末从乌托邦中衍生出来的西方现当代文化思潮,反乌托邦通过勾画一幅幅地狱般的惩罚性图景,一方面从思想上揭示乌托邦在某些方面的不现实性和荒诞性,另一方面帮助读者反观、批评、警醒乃至改善现实社会。它既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生存危机感和社会焦虑意识的产物,同时也是一种“反抗或批判的能量或精神”,一种“社会行动的话语”。反乌托邦体现了对现代社会出现的环境问题、身份歧视问题、科学技术与伦理之间失衡、权力集中与民主之间失衡问题、消费社会中人与文化的扁平化问题等这些“难以忽视的真相”无比的焦虑和关切。
出版方介绍

高等教育出版社建社60余年,以出版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及社会教育等教育类、专业类、学术类出版物为主,产品形态囊括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及期刊,在出版物质量,出版规模,市场占有率,产品数字化、国际化以及综合实力等方面都处于中国出版行业领先地位,在中国单体出版社竞争力排名中位列前茅,是国内唯一入围全球出版50强的单体出版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