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四期《十三邀》中,许知远赴香港拜访叶问的长子叶准,匆匆掀开了香港一角:鳞次栉比的高楼,每个人的空间似乎都非常小,然而却呈现出一种让人惊叹的秩序。

那一集,相对于这座城市,真是不过瘾!谁想到在本期《十三邀》中,许知远再赴香港,由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澜做“向导”,行走于外地人不甚了解的城市纹理之间,吃吃喝喝,或逍遥游,或谈天说地,或隐隐回避现世,纳世界于方寸饭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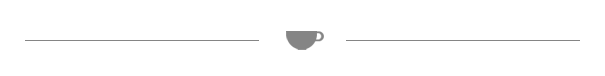
第一顿饭:九龙城吃火锅
“我来了香港 50 年了,我选来选去,还是这个地方比较好。”
因为蔡澜这句话,许知远与这位拄着拐棍,但依然风度翩翩的老者,悠悠闲逛于九龙城。

蔡澜(背黄色布袋者)与许知远
这里有好多商铺,卖的无非是肉啊、菜啊、生活小用品、寿衣、棺材店......从出生到死亡,都包了。每一家商铺摆放的货物都聆郎满目,诉说着这座城市的生机。

“这里有生活、像人。”蔡澜这样总结这个地方,显然他常常出入这里,好多店主人都认识他。

二人一起买海鲜
“菜市场变成我的办公室了,大家都随和一点嘛。”蔡澜边走边说,他本人语速不快,一字一字的吐,语气非常随和。

二人进入一间门脸并不起眼的,位于菜市场上面的馆子,放眼望去,好多张桌子并排摆着,食客们随意享受火锅,就如内地在街面上的大排档一样吃饭。

许知远与蔡澜吃起了火锅,喝起了酒。饭桌上,蔡澜很照顾人,“看看摄影师怎样坐?”、“你今天不急吧......”言语上照顾到,席间布汤倒酒,非常周到。
“吃点鱼春,”蔡澜邀请到。

“吃这个能壮阳吗?”许知远戏谑,在中国,流行着很多可以壮阳的食物。
“不能。”蔡澜斩钉截铁的说,“胡说八道了,哪里有壮阳的东西,壮阳这回事根本不是吃的嘛,是两个耳朵中间的事情,是你的脑子想出来的嘛。”蔡澜边说边用双手指着耳朵。
“其实最性感的是头脑了,”许知远补充,“食物背后都是社会心理,政治结构都有关系,那比如香港,香港的食物跟它背后的社会心理,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我做的这么辛苦,我吃一顿好的可不可以?......发展快,不安性,要回报嘛,要回报嘛,要不我干什么,这种心理。”蔡澜加重了语气。
“所以我最想做拉丁民族,我认为最快乐的是拉丁民族,我以前很忧郁的,不开朗的人,后来旅行了,我就知道,原来人家可以这么活着。”
蔡澜热爱旅行是深受父亲影响。他父亲是一位诗人、书法家,笔名柳北岸,是位五四青年,因党争去了新加坡,后来成为邵氏影业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的经理。所以蔡澜出生在新加坡,1957 年到了日本,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1963 年才来到香港,长期任职邵氏、嘉禾等东南亚最大制片厂的电影监制。
说起旅行,回顾整个人生,蔡澜有诸多游历:
“十二三岁的时候,已经看到那些马来少女,开着水龙头,围着一条纱笼,就在那边洗头发,微微看到胸部,哦,那可性感啦。”
“你有多少个女朋友?”许知远顺势问下去。
“我几十个有吧。”他i想蒙混过去这个问题。

许知远怎么肯依,要求蔡澜如实交代。
“哎......一年一个总有吧......”蔡先生笑的眼睛咪成一条缝。
“帮他解决一个问题,我的制片人,(怎样交到女朋友)”许知远继续。

此时神秘制片人入镜
“交女朋友不是说马上就交到的,”蔡澜传授道,“怎么练习呢?丑的照杀,杀久了以后你就成了专家。那漂亮的就跟着来了。”
三个人顿时都笑做一团。
笑后,照旧闲聊。
“很多时候享乐其实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也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同时发生的,在明末清初做李渔这样的人,是一种选择,但是在这个时代做一个享乐主义者,意味着什么?”许知远问。
“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蔡澜挥挥手,“想通了什么都可以,问题是想通想不通嘛。还有最大的问题是你敢想不敢想嘛,很多人都不敢想的嘛,在笼子里面关太久了。”
“那如果你选一个朝代,你想生活在什么时候?”
“还是现在好。”蔡澜不假思索的回答,“因为你现在最容易得到资讯,新的技术太多给你学了,我一直学互联网。”
但是许知远却一直对手机有种矛盾,他拿出自己的手机:“这样一个手机,它看起来有很多自由,但其实变成一个牢笼,新的牢笼。”
“你不当它是就不是,不要管人家怎么想,你要明白这一点。”蔡澜又挥挥手,期望许知远不要在意其他人对手机的看法。

柳北岸
除了旅行,父亲还教他准时、守诺言......这些都是有着老派文人印记的东西。
“有一个一直很困惑我的东西,我很佩服您父亲那代人身上都有的,中国文人身上认为的天下还是很重要的,包括顾炎武说的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我困惑的是‘读圣贤书所谓何事’他们怎么平衡啊?”
“后来你发现,吃吃喝喝才可以平衡。”蔡澜大笑,“来来来,喝酒”。他没有再给予这个问题更多的解释,哪怕许知远一再追问。

第二顿饭:餐后泰餐馆喝椰青
餐后,二人说说笑笑,到了火锅店附近一家名为“金宝泰国餐馆”的餐厅。

店面布置比火锅店内更显雅致,整体色调昏黄,竹椅木桌,别有东南亚风情。


墙面上有菜牌
蔡澜说,他年轻的时候,看《约翰·克里斯多夫》、《战争与和平》......经过那个时代后,就看的更加广泛了。
“那约翰·克里斯多夫是非常英雄主义的,您现在再回头看,觉得背叛了自己的青春吗?”许知远问。
......
蔡澜仍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避重就轻的问:“你们这几天还想要干什么?”
许知远说,想去看看香港邵氏的一些地方,并且问蔡澜是否有兴趣。
“没有。”他回答的干脆利落,然后低下头去,细细喝椰青。

蔡澜经历了香港电影整个的黄金时代。从 1985 年 到1999 年无论是明星阵容还是影片的数量、质量,都是空前的。在这一时期,比如成龙、周润发......都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不灭的偶像。
蔡澜在香港邵氏担任要职,见证过成龙主演的一系列商业娱乐片被大众接受,见证了成龙偶像地位的确立。可是蔡澜却认为,那是一段不开心的时光。
他觉得邵逸夫本人一生不停的学习、不停的动脑,但是他一面倒。他只知道商业片可以赚钱,却不知道文艺片也可以赚钱。那时候一年拍 40 部戏,都赚钱,蔡澜说,邵先生我们拍一部不赚钱的怎么样?邵逸夫回答说,希望第 41 部也赚钱。
“他的思想还没有到那个层次。”蔡澜说,“因为他不懂,他不能接受。”
“这个大局我改变不了。”蔡澜又笑了,“不讲了。”
“但您应该讲的,我觉得这个对下一代来说非常重要,对您自己也重要。”许知远希望蔡澜用笔述说心曲。而蔡澜,此时仅仅是饭桌上的游侠。
“我是一个把快乐带给别人的人,所以我有什么感伤,尽量都把它们锁在保险箱里。”
“但人是平衡的嘛,你有快乐的一面,享乐主义的一面,就必然有感伤的一面,要不人就完蛋了,就失衡了。”
蔡澜又笑了:“我现在已经学的不失衡了。保险箱里面有个锁链,还踢进了海里。”
“所以你还是知道有这个保险箱的。”许知远说。
“我知道所以我可以踢嘛。”蔡澜继续喝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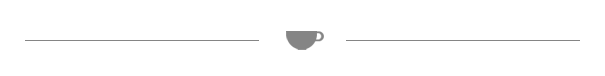
第三顿饭:中环喝早茶
喝完椰青,二人道别,蔡澜说,要请许知远一行转天喝早茶。
许知远希望在早茶上,探讨喝椰青时没有探讨完的问题——一个享乐主义者,必然是敏感的,才能发掘生活中的美食美景,也必然对这个社会敏感,对不公敏感,与道德敏感,那么他是如何面对他的敏感神经所探查到的这些?
许知远想在早茶时分,打开蔡澜的保险箱。

这是一家名为“陆羽早茶”的店面,刚开席,蔡澜便演示给大家看,如何喝冷泡茶。
许知远吃了一块儿猪肝,继续发问:“我记得加缪说过一句话,说一个人如果是个感官主义者,那一定是一位道德主义者,这个东西对您来说怎样理解?”
蔡澜笑,他内心一定第一时间识破了许知远所问的是什么,“食物是本能嘛,人们常常忘记本能。”
直接问行不通,就拐个弯去问,“你最有野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蔡澜说,最有野心的时候正是在邵氏的时候,一心想拍个好片子(文艺片),后来想通了,做艺术要有良心,对老板有良心、对人有良心......“王家卫作品,有多少个人死在脚下,有多少老板亏本....多少人支持你才成为王家卫电影,我开始明白,要太有个人主义的话,就不要拍电影,因为电影不可能是一个人,它是一个全体创作......所以开始写作,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没有人控制我,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不好我撕掉好了。”
“那么香港文化的那种创造力,是不是来源于香港的流亡精神?比如金庸写的其实是流亡文学,他被迫离开那么大的世界,而想象塞北、想象大漠,香港那么小,那么窄......香港没有沧海一声笑。”许知远用这个侧面聊蔡澜的“保险箱”。

金庸的武侠小说与改变的电视剧,让无数人着迷
“你不要想得太多啊,老兄,你整天想的太多。”蔡澜拍拍许知远的肩膀,“吃一点,吃一点,大家多吃一点。”话题最终还是回到了吃饭上。
二人吃完饭,行走在香港唯一剩下的石板街上面,那是过去老香港的感觉。

走在这条阳光洒满的石板街上,两个人还怎会将苦闷与人生联系在一起?
三顿茶饭,时间虽不长,蔡澜或侃侃而谈,或回避绕弯,但是他也用“吃吃喝喝”回答了许知远的疑问,他经历了大时代的到来与退去,他本身对逝去的文人精神也好,对商业浪潮也好,都是体验者,而不是旁观者。
但他选择不回应,选择继续自己的享乐人生。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人世间的苦闷与失败,真的那么值得去欣赏吗?
蔡澜选择买最好的衣服,开最好的汽车,去生活,去经营生意。

相谈甚欢,也有道别一刻。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谈笑间,也收获了光阴,读圣贤书,不是为了背负。
“我认为我要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话,我就去洒热血断头颅,我认为我没有这个力量改变,所以我就开始逃避喽,吃吃喝喝也是一种逃避。”蔡澜在饭桌上曾这样说。
他笑许知远的理念,许知远认为知识分子可以解决一些事情,但是蔡澜认为,解决不了。
“你要再过一阵子会同意我的话。”蔡澜对许知远说。
就这样,蔡澜用自己的逃避,过上了自由快活的生活,他成为了一个风流快活的体面人。
这样的人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许知远在节目结束时说:“体面的人有原则,这是对中国最大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