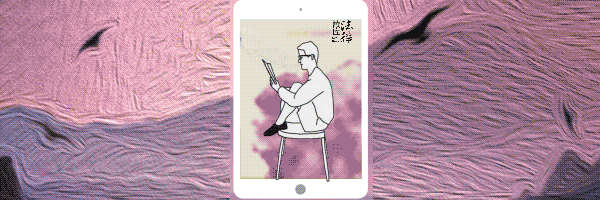
这已经是他连续三年第三次无证驾驶了。前两次因为无证驾驶,只是受到了相应的行政罚款和行政拘留。
而这一次,终于酿成了大祸:由于无证驾驶无牌无保险的三轮车,超载拉运砂石,结果在转弯时,刹车失灵,追尾前方车辆,导致前车驾驶员被侧翻的车子当场压死,发生了亡人严重后果。而他,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可以说,这次他终于咎由自取,触碰到了刑罚制裁的红线。

不过,抛开上述这些背景,其个人似乎也并非如此“面目可憎”:衣着陈旧,不修边幅,左脚上胡乱踩着一双布鞋。尤为显眼的是,本次事故也造成他自己骨折:被纱布裹的严严实实的右脚,耷拉在半空中,需要借助拐杖一步一步的往前挪。一条套在脖子上的绷带,将他的左胳膊悬在胸前。
种种迹象,无声的诉说着他背后困顿的家庭生活。即使这种境遇,案发后,他的家人通过努力筹钱,给被害人家属赔偿了26万元,取得了对方谅解。侦查机关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移送审查起诉。
案子基本事实再清楚不过了,定性也没有任何分歧。按照以往的惯例,这种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的普通交通肇事案件,似乎是可以建议适用缓刑的。
不过,问题就出在讯问的过程中。接受讯问时,虽然他口口声声认罪认罚,但是一些细微的举动令我对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产生了摇摆:虽然对于基本事实,他并不否认。但在追问事发当时的车况、拉载砂石的细节时,他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反问道:就这么简单的事,以前给公安机关都说过了。
在给他解释量刑建议的理由时,他甚至半是自言自语,半是说给我听似的:我都已经赔偿了26万了,还需要坐牢吗。我反问;你觉得赔偿26万就够了吗?他微微一愣,继而又强调道:别人都说了,只要取得被害人谅解了,就不需要坐牢了。他始终在强调自己能否坐牢的问题,却从没有提过那个被害人的情况,即使他们之前是老相识。
尽管认罪认罚具结书签署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尸检照片当中,被害人的惨状始终萦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这个量刑建议恰当吗?我不断的在内心深处反问自己。
案子很快到了审判阶段。法庭上,法官问被告人对案件的看法,对方一律回答没有。脸上,始终是那样一幅满不在乎的表情。例行完法庭调查、举证质证,发表公诉意见时,有那么一刻,一种莫名的对被害人的悲哀感升腾起来。我抛开提前拟制好的公诉意见书,向法庭陈述自己对案件的感受:
被告人从内心深处缺乏对逝去生命的敬畏感和忏悔感。虽然他确实愿意认罪认罚,并赔偿了对方家属26万元,取得了谅解。
但是26万元就能与一条鲜活的生命划上等号吗?他认罪认罚的动机究竟是内心深处真正来自对被害人的歉疚,亦或只是为了保证自己不用进监牢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通过被告人今天在法庭上的表现,公诉人认为需要深入考察。因为赔偿了26万元,在被告人看来,事情已经了结了,那条逝去的生命已经与他没有关系了。现在的庭审不过就是走走程序而已。
在这种心态下,我们很难保证他不会有第四次、第五次乃至更多次的无证驾驶行为的发生。是否应当处以缓刑,应该从严掌握,以彰显法律的威严,告慰被害人无辜枉死的生命……
空气中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站在被告席上的他,显然对这种情况很意外。直到此时,那无所谓的表情才似乎有了些许慌乱,忙不迭地解释道:我认识到自己做错了,不该无证驾驶,我对被害人很愧疚……
可是,此刻的这番解释,与其说是反省,不如说更像是为了推脱罪责而做出的辩白,显得苍白又无力。缺乏来自内心深处的忏悔,缺乏真情实感流露的认罪认罚,只是包裹在冷漠心肠外边的华丽外衣而已。
后来,当法院依法做适用缓刑的社会调查评估时,评估结果并不理想。法院建议我调整量刑建议。我果断的调整了可处缓刑的量刑建议。
一审宣判后,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并没有上诉。直到现在,一直好奇他是出于何种动机放弃上诉的。是被庭审上的话语打动了吗,还是他真的觉得对不起被害人。只是希望,他能够在失去人生自由的囹圄当中,真正能够想明白:为什么付出了26万元,依然没有换来自己最初想要的刑罚。
认罪认罚从宽固然是我们应该积极推动适用的制度。但是,认罪认罚绝不只是一句“我自愿认罪认罚”就能体现得了的。这句简简单单的话语背后,需要我们抽丝剥茧、层层拨开案件的迷雾来考量这句话的真实性,进而做出恰如其分的量刑建议,这既是制度本身所蕴含的题中之意,也是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所需。
不过,深究起来,促使我调整本案认罪认罚量刑建议的动机,与其说是追求正义,不如说是对被害人的同理心使然。
是的,只有司法办案中具备了同理心,我们才能不仅仅将案件当做案件本身,而是透过纸质的卷宗,看到背后那鲜活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