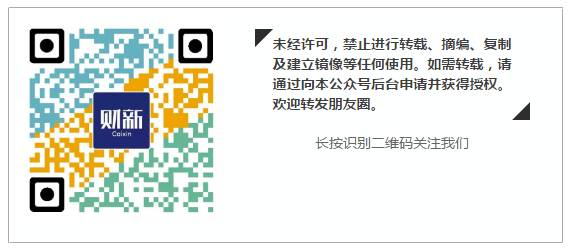公办学校“减负”,民办学校“抢跑”,沪上家长热衷将孩子送到课外培训机构“拼娃”。中小学生学习负担,已成上海重大民生问题
在上海,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已成为重大民生问题,从市委书记到普通百姓都投以关切。
一个说法可对此作形象说明——有家长花大价钱买了学区房后,发现学区对口的公立小学“变差了”;但要把孩子送进优质的民办小学就读,竞争异常激烈,必须先把孩子送进课外培训班,加班加点“拼一拼”。

在上海,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已成为重大民生问题,从市委书记到普通百姓都投以关切。视觉中国
上海家长为何焦虑?教育主管部门多年力倡“减负”而剥离的应试训练,是否会从公办学校转移到民办学校和机构?眼下,公办学校还需要再减负吗?日前,在同济大学举行的“基础教育减负政策研讨会”上,多位上海学者、中小学校长和家长代表就此展开讨论。
2017年开春,“减负”成为沪上公共政策焦点。“孩子们现在是最辛苦的。比家长还辛苦。孩子们的上课时间、做功课时间,远远高于大人上班时间。”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2017年2月举行的上海两会上,公开表达对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忧切。
上海教委随后成立“减负”小组,并颁出“民办学校不得提前到幼儿园、小学遴选学生”、叫停民间举办的“小机灵”杯数学竞赛等杯赛、会同有关部门“净化整顿教育培训市场”、恢复“晚托班”等政策。
在上海的教育决策视野中,“减负”其实不是新问题。
聚焦科技与教育政策的同济大学里瑟琦智库,在上述会议上发布了一项名为《上海市基础教育“减负”15年反思》的报告(下称《报告》),其中介绍,上海自2005年以来一直对“应试教育”进行规范和调整,每年都有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相关政策面世。
但教育主管部门的“减负”新政能否落地?有学者在上述会议上提出担忧,认为在上海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现状下,“减负”恐将成为“走过场的形象工程”。
一位上海的公办小学校长指出,上海家长的教育焦虑,源于义务教育阶段后的升学压力。这位校长说,有家长曾向其表达过孩子“进不了民办中学,就进不了示范性高中,那就考不了985”的担忧。
“公立和私立学校教育出现区别化。”上述《报告》提出,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强制性免试就近入学,而私立学校则进行“入学竞赛”,这是家长自主给孩子增负的直接原因。
面对此一形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陆建非反问,“在权衡利弊后,家长有可能选择合作(减负)吗?”
减负令难敌择校热
“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和考大学”环环相扣,择校形成竞争,“就必然导致学校和家长对学生学业要求的高标准”,上述《报告》指出。
上海孩子要上好大学,摆在眼前的是上海高中里“四大名校、八大金刚、逍遥二仙”(指上海中学、复旦附中等知名高中)升学率领跑的现实。
而想进入上述的重点高中,从录取率来看,上海优质民办初中的表现比公办初中更优异。上述《报告》也指出,“在竞争民办初中入学名额的过程中,公立小学和狠抓应试教育的民办小学相比,已经较为明显处于下风。”
上海“小升初”的家长圈甚至还流行一些择校“暗语”——“植物园赏赏花”“烈士陵园拜一拜”“闵行体育公园散步”,这些“暗语”分别对应几所上海的热门民办初中:西南模范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和华育中学。
在升学压力层层向下传导的形势下,“优先选民办、保底到公办”,已成为很多上海家长为孩子选择小学的基本思路。
民办小学“抢跑掐尖”
“上海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主要是民办初中。”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上述会议上表示。
《报告》指出,“招收最优质的生源”和“对学生进行艰苦的学业训练”,是上海优质民办小学冲击重点初中高升学率的两大法宝。
上述公办小学校长坦言,“民办学校‘掐苗’严重,我们学校的生源,是被一流的民办、二流的民办一轮轮掐过的。”此前,上海民办小学的招生考试在公办小学招生前举行,凭借“起跑线领先”等优势,“对公办教育冲击很大”。
此外,也有上海民办小学凭借“不听从行政指令的优势”,对学生进行“刷题”等学业训练。上述《报告》引述一位上海公办小学校长的看法称,“公办学校都会严格按照主管部门要求的基准来操作”,民办学校却存在“拔苗助长”的问题。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分析,“民办学校自身缺乏减负动力,相比公办学校,它们所受的约束和限制也较少。政府的‘减负令’难以(在民办学校)发挥和公办学校同等的限制作用。”
公办小学已“无负可减”?
“公办学校已经无负可减了!”有公办小学校长在上述会议上表示。
上述《报告》对上海50余位基础教育领域教师的调研也显示,这些教师普遍认为“公办学校教学大纲的要求已经非常低了”,如果仅从满足大纲要求的角度来看, 上海的“00后”学生与“90后”学生、“80后”学生相比,他们的学习负担和压力“在代际之间逐渐下降”。
自1988年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始,为中小学生推出“减负”的政策,长年出现在中国各级教育部门的决策视野中。据陆建非介绍,从1949年到2013年,中国官方对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共推出56个减负令。
而在上海,“减负”的政策力度尤甚。近年来,上海在公办小学全面推行“零起点”教学和“等第制”评价制度,使用“ A、B、C、D”或“优秀、良好、合格、需努力”的等级制,取代百分制评价,以淡化小学阶段的分数选拔功能。
“但是公办学校通过‘减负’剥离的应试训练,是否已转移到民办学校和课外培训机构?”张端鸿在上述会议上提出疑问。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近日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日本基础教育阶段实行了30年“宽松教育”后,出现系列副作用,日本政府因此进行反思。日本的“宽松教育”政策从1976年开始实行,以缓解学生学业压力为诉求,包括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缩减课本)、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等措施。
但在实行了30年“宽松教育”后,日本却出现公立学校“瘦弱”,私营办学机构“肥满”的现象。整个社会的教育供给也被改变,日本中产家庭“若在子女教育上要求上进”,必须对抗“经济负担、选择焦虑和全家被裹挟参与孩子应试”等“三座大山”。
家长“拼娃”冲动何来
2017年1月,360手表发布的基于400多万“儿童成长状况大数据”显示,上海小学生的周末时间,约有42%被各类培训班所占据,而去广场、公园和游乐场的时间仅剩下13%。
上海孩子为何疲于参加课外培训?上述公办学校校长引述一些家长的想法以作说明。家长们称,若孩子要上“八大金刚”等优质“牛校”,“就要让孩子成为牛蛙(娃),成不了的话,至少要成为青蛙(普通的娃),不然我的孩子就只能成为小蝌蚪”“如果我的孩子成为小蝌蚪,我这一辈子没有指望了,我的孩子也没有指望了”。
中产阶层,或许是让孩子参加课外培训意愿最强的群体。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智力开发研究所副研究员胡伶在上述会议上,分享了她关于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与父母职业关系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研究结果显示,在样本中小学生群体中,“行政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或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花最多时间在父母或校外文化补习班布置的作业上。
陆建非说,“在上升通道狭窄的社会里,当家长不能给孩子提供超过社会群居水平的教育资源时,就只能依靠孩子自身的竞争争取资源。”
当政府的“减负”政令和家长的“增负”冲动相遇,“(公办学校)减得越多,事实上留给私立学校和培训市场的空间越大。”上述《报告》提出,过去十多年的“减负”政策,或已使公办学校的学生学习负担不断下降,但衍生副产品的却是“一个繁荣而功利的教育培训市场”和“孩子日益增加的课余负担”。
系统性教育不公隐忧已显
公私立学校除了减负力道不一,上述《报告》还对一个问题提出担忧,指上海逐渐壮大的优质民办中小学市场,将走向按照“家庭背景、父母成就、孩子口头表达”等显性标准进行招生的倾向,“民办学校喜欢招收‘收入高’‘家境好’‘孩子机灵’‘家长陪伴时间足’的学生早已广为人知”。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告诉财新记者,在江浙等地区,各界已形成共识,家庭文化背景对于学生的培养至关重要,“家长都希望孩子与好孩子在一起,民办学校只要一次考得好,就会受到追捧”。
“而公办学校一次表现得不怎么样,就会被抛弃。”吴华指出,民办学校发展的契机,既来源于外部政策环境,又源于内在管理机制,“民办学校教师对学生付出的努力远超过公办学校”。
此外,公办学校被严禁择校、控制生源规模,也给了民办学校“难得发展契机”,吴华称,“如果一个民办学校表现出优势,在市场引导下,生源规模将越来越大,规模大了就会产生经济效益。”
而上海的一些优质民办学校自身基础也较厚实。杨东平透露,上海顶尖的民办初中,有的是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中的“改制学校”,“与公办母校和公办高中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杨东平称,“这些民办初中游离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之外,在考试选拔等方面大展身手,所获取的高升学率使公办学校处于下风。”
而已在上海、杭州等一些发达城市出现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升学表现倒挂、优势家庭子女更愿进入私校,以及各阶段教育资源长期配置失衡产生的影响,或更加深远。
此前,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在一项政策建议报告中提出担忧,中国或在面临一种“系统性教育不公平格局”的挑战。这种格局表现为:社会中的优势群体子女,在私立中小学接受优质教育,继而可获得优质低价的高等教育服务;但弱势群体子女,却接受着较低质量的基础教育服务,最后难以在竞逐精英型高等教育机会的比赛中取胜。
杨东平建议,上海需要提出“重建以公办学校为主的义务教育体系”的命题,或“重建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即在民办教育实行分类管理的框架中,规范非营利民办学校的行为,彰显义务教育的公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