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做个每日精选一篇书摘的小栏目
从译文社的书中,摘一些有趣或无趣的内容
今天是第四十四篇
也欢迎看到您发来的个人建议
告诉我想读哪位作家的作品
|
-
44
-

11月20日,爱尔兰短篇小说大师
威廉·特雷弗
(William Trevor)在英国病逝,享年88岁。
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篇特雷弗的小说选段,谨以此表示纪念。
“我对人很有兴趣;我很好奇。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又怎样生活。如果看到那边的一个女人,我就想知道她为什么要那样离开;她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还很多疑。……我听到什么然后就开始思索,……人们总说我有一双很警觉的眼睛。”
选自公众号“
壹光年贺彬
”文章|
《
坐对威廉·特雷弗》
在外一晚
文
|
威廉·特雷弗
译
|
杨凌峰
摘自
|
《出轨
》
- 声明:刊发已获授权,
转载先请
私
信联系
-
剧院的小酒吧里,人们还在说着话;虽然已经有通知播放提醒过,两分钟之后演出就要开始,但人们还是不紧不慢地享用着饮料酒水。酒吧今晚的客人太多了一点,超出了恰当的接待容量,因此就谈不上舒适宽松;不少人只好挤在吧台前和房间角落里凑合着喝上一点东西;有些人则已疏散到酒吧外面通往观众席的几处通道口,准备入场。
“离演出开始还有一分钟。”扩音器里又传出不容置疑的最后提醒;随后,突然之间,仿佛潮水急退,酒吧里立刻便几乎空无一人。
酒保体貌特征鲜明,算得上是个人物。他面容沮丧愁闷,瘦得皮包骨,戴着眼镜;他干瘦细长——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像一截老旧的绳线。女招待则显得年轻不少,体态丰满,总是乐呵呵的。
“喂,你看,”她说,“那个女的。”
一位女士没有与其他客人一起离开,而且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要离开的迹象。她坐在房间一角的桌子前,那是酒吧仅有的几张桌子之一。在她四周,沿墙壁固定好的一溜架板上,还有所有的椅子上,都放着客人们留下的空玻璃杯。她自己喝的是一杯兑了汤力水的金酒,还剩有四分之三的高度。
“是聋子吧,你觉得呢?”酒保感到疑惑。女招待回应说,听力困难的人可从不到剧院这种地方来,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是,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个人的助听器被暂时关掉了,然后又忘了再打开。
他们谈论的这个女人穿戴得漂亮考究,两种色调深浅略有差异的绿色协调搭配。长外套放在一旁,垂挂在她落座的那张桌子所搭配的另一张椅子靠背上;这件外套一面是粗花呢,另一面是防雨布料子。往昔美貌的遗痕照亮了她的五官,依旧惊艳,而且看似比她生命中早先年代的漂亮容颜更少了一些偶然草率,多出了一份沉静雅致。秀丽的金发间也冒出了少少的灰白丝缕,这与时光流逝所雕琢而成的其他变化一起,让她的容貌更增添了一种出众的独特气质。
“夫人,打搅一下,”酒保开口道,“提醒您一句,演出已经开始了。”
伦敦,这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啊!杰弗里心中感慨道。他仰望亨利·哈弗洛克男爵铜像那昏暗的面孔;雕像头顶上落有少许的鸽子粪,因此这位功勋士兵的脑袋显得比脸部要亮一点。四月最后的熹微暮光正在悄然退去,此时的伦敦城便处于最美妙的状态,正如这个城市在清晨、当黎明幻化为白昼之际所呈现出的样子——在杰弗里眼中这两个时刻最美。特拉法加广场上,交通出现了拥堵,笨拙庞大的红色公交车与耐心的出租车都在慢慢爬行,时不时地有一两个单车骑行者从车流中蜿蜒穿过。人们聚集在过街路口的信号灯前,顺从地等待着,信号转换之后便可继续前行;每当一波行人过街之后,随后一波等信号灯的人群阵势就略微缩小一些,看上去就好似有些人从原先那同一群人中消失不见了。鸽子们在空中盘旋,仿佛在宣示翅膀下方的领土归它们所有;它们不时飞扑降落到地面,摇摆着去啄取地上的零碎吃食,或者还因为食物而相互争抢斗嘴,然后又一起呼啦啦拍动羽翼飞上天空,争吵的聒噪声在空中余音不绝。
杰弗里转头离开了这一切,把亨利·哈弗洛克男爵与鸽子还有那四只大狮子[雕塑]丢在身后;广场上的泛光灯刚刚才打开,照亮了国立美术馆的外墙立面。“让她在那等太久是不行的。”他低声自语,引得一旁经过的两个小姑娘对他切切暗笑。他让她等得略久了一点——到达约定地点时,他反而拐进了圣马丁巷的索尔兹伯里酒吧,点了一杯金铃威士忌,随即又招呼服务生说最好是双倍份量的。
他需要这个。说实话,他甚至还需要再来一份威士忌,但他摇头否决了这个念头,在心里自责道:如果喝得醉眼蒙眬、迷迷瞪瞪了,他肯定无法计划下一步的接触,而她也不会希望跟一个酒徒之间有什么进展。回到街上,他在防雨布料的外套口袋里摸索那只小塑料瓶——里面装的硬颗粒口香糖一走动就发出咔嗒声响。结果他在夹克口袋中找到了瓶子,然后便放了两粒糖在嘴里嚼着。
伊芙琳稍稍向后靠了靠,躲开酒保那看似脏兮兮的衰老面孔,也躲开了酒保的满嘴假牙与干瘦凹陷的双颊。他又说了一遍演出已经开始。
“谢谢好意,”她说,“实际上,我在等人。”
“你可以先入场,等你朋友来了我们会把他送进去的。如果你身上带着票的话。在戏还没有正式开场时,即使有人进出打扰了一下,其他观众往往也不会太在乎的。”
“不用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这里碰头而已。我们不打算看演出的。”
她看到在镜框厚厚的眼镜后面,酒保的眼中满是困惑。她随后读出了酒保困惑表情中闪过的内心念头:这事有点异常。酒保大概也满足于这样的判断——他毕竟得出了一个结论。
“我再问一下你不介意吧?如果你的朋友们都来迟了,身上还带着票,需要进场的话,我可以跟我的同事讲一下。”
“你真是太周到了。”
“不客气,夫人。”
就在她坐着的位置附近,酒保清理起架板上的玻璃杯,用一块半湿的灰色布顺势擦抹架板,同时收起更多的杯子,摞在一起,熟练地保持了平衡。“这位女士在等朋友,”他对在吧台后面一个水槽边清洗忙碌的女招待说,“今晚的演出,他们不看。”伊芙琳能够感觉到从吧台那边投来的瞥视目光。稍后还会有猜测议论的,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要消磨时间。而暂时她只不过一个落单的女人,独自坐着。
“我还可以再喝一杯吗?”她对吧台喊道;她突然决定再来一杯,“你们等下有空就拿过来?”
然后她自己开始猜测起来,想象着一个什么样的人注定要走进来。过去的经历常常是这样:当一个令人失望的家伙应约而来,她在内心里便不由叹息一声,噢,老天!——而她的想象也就随即戛然而止。“哦,怎么这样。”她甚至对自己嘀咕了一声,然后徒劳地看向一边,装出并非在指望什么人来的样子。以前见过的人倒是有一些,这些人前赴后继——劳埃德的银行经理,醉心于合唱的音乐狂热爱好者,自称海军退役军官但实际是邮轮服务员的家伙,露出马脚后跟她道歉再离开的“鳏居”大学教授,还有个编写棋类游戏的男人。甚至在还未开口讲话之时,他们蝇营狗苟、纠缠不休的德行便与微笑一同展现出来,但满肚子的小小罪恶却是欲盖弥彰。
有生以来的岁月中,不管是什么约会,她都会自我强迫似地提早到场先等着。今天她也是等着,同时做出了一个决定:如果这次还是不行,以后就不会再重复这样的经历。她将对人生中的这件事听之任之;当然,那会是一个遗憾,但同时也会是一种解脱。她的饮料送到了。酒保这回没有逗留。他说马上就把要找的零钱拿过来,她摇头表示不必。
“谢谢了,女士,请慢用。”
她以微笑作答。当一个男人出现在敞开的酒吧门口时,她的微笑还继续着。那男人有点犹豫不决,站在那里左右张望了一下,仿佛酒吧里人头济济,有好几个不同的女人要他从中选择一样。他的紧张几乎一览无余。他走近了一点,先朝她点头示意,然后才开口。
“我,杰弗里,”他说,“伊薇,是你?”
“对,不过我的名字叫伊芙琳。”
“噢,我真不应该,非常抱歉。”
他那件防雨布外套有几处陈旧磨损得厉害,但好在不脏不破。他的颧骨挺高,脸上这一部位的皮肤好像被拉紧了一般。他看上去完全不是那种营养良好、红光满面的类型。他的深色头发倒是连一丝灰白都没有,但软塌塌的;她不禁怀疑他是否患了流感,现在还处于康复期。
“你的饮料要不要加满?”他以一种挺绅士的风度提议道,“来点小食吧,坚果还是薯片?”
“不用,这样就好,谢谢。”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吃的东西有点挑剔讲究。他那副略显生硬紧张的外表下,是否有着一种特别的脆弱?她一直希望对方要善于表达、谈吐得体,在这一点上他好像还没问题。如果他刚从哪怕是一场普通感冒中恢复,看上去自然也会有点憔悴;谁都免不了,这也不是能装出来的。他脱掉防雨外套,解下蓝色围巾,里面穿的是一件粗呢夹克,倒是与腿上那条浅棕色的灯芯绒裤子差不多搭配。
“我选这个地点碰头,让你惊讶了吧?”他说。
“可能有一点吧。”
现在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她已经见到他,从他那里可以看出一点点迹象,表明他是怎么来考虑这种安排的:演出开始后,剧院酒吧间会空下来,那样他和她都可以避免因为找错人而带来的小小尴尬。他没说出这一点,但她已经清楚。直到这会儿他才迟迟向她道歉,说让她久等了。
“等一下完全不要紧的。”
“你确定不要再喝点什么?”
“真的不用了,谢谢。”
“那好吧,我自己去看看酒水。”
杰弗里在吧台询问:“你们有白的吗?干白?”
“先生,当然有的。”酒保转身从后面一个装了冰块的桶中拿出一瓶。“格瑞诺,”他说,“是干白,我们一直保持低温存放。”
“格瑞诺?”
“先生,这是这款酒的名字,产自‘格瑞诺河谷酒庄’。瓶子上的标签差不多被冰块磨掉了,但这酒就是叫这个名字。格瑞诺在我们这里很受欢迎。”
杰弗里不喜欢这位酒保,对于从事服务业的人,他经常都不太信任。他猜那个女招待大概就像个人到中年的女儿那样照顾着酒保,听他因年老辛酸和身体的小病痛而发出的唠叨悲叹,偶尔会邀请老头子参加一两次圣诞的庆祝聚会。她白天的正式工作或许是售卖窗帘材料,杰弗里想道,而老头子则很久以前便从女人所在的那同一家百货商店退休了。事情有可能就差不多是这样,而剧院酒吧才是这两人的真实世界。
“好吧,这个给我来一杯。”他说。
他们聊了一会儿天气,然后又说起眼前的这间酒吧,评论它乔治王朝时期的石膏天花板的损坏情况——原初的天花连一个角也没剩下。时不时地,欢呼声或笑声从剧场演出厅那边传来。他们的交谈谨慎地转向了更隐私一些的话题。
介绍所的人说他四十七岁;个人详情表格中“职业”一栏填的是“摄影师”。她想到的是电视上常看到的摄影记者,这些人成群地聚集等候在某个名流巨星的门外,或者在犯罪现场你推我搡地抢着拍照。但在电话里,那个介绍所的女孩向她确认:这里的摄影师不是指那种新闻摄影记者。“不,根本不像那种,”女孩说,“也不是婚庆摄影师。”他在他那个领域很出色的,女孩向她透露,跟一般说的摄影师有区别。
她试着在记忆中去搜寻一些伟大摄影家的名字,但想得起来的只有卡蒂埃—布列松a,而且脑海中也没有浮现出任何具体的影像。她本来想问问他最喜欢用哪种相机的,但话到嘴边却改口了,问他拍的是哪种类型的照片。
“城镇景观,”他回道,“真的就只是城市街景。”
她点头,很肯定的样子,好像已经完全了解他所说的意思,好似她也能够领略给城镇街道拍照所蕴含的乐趣。
“我拍伊斯灵顿的一些地方,”他说,“还有东伦敦霍克斯顿一带那些小小的背街深巷。人们很少看到这些偏僻街区的景象。”
他一生的计划就是拍出伦敦各处的特色景观与独有风貌。他提到了很多地方:亨格福德桥、德拉蒙德街、礼拜街、砖头巷、维尔克罗斯广场(老井广场)。他描绘起路上的沙井盖,接收卫星电视的锅状天线投在地面的影子,还有雨水落在石板瓦屋顶上的样子。
“真是非常有趣的工作。”她说。
她想寻找的是生活伴侣。有时候,在去唐斯丘陵草地或者海边休闲游玩时,她便体会到孤独感带来的重压。在电影院或剧场里,她常常不由得希望身边有一个人,可以让她转脸相向,说说对这个或那个演出什么的有怎样的看法。她并没有特别的愿望要去赴一场所谓浪漫的烛光晚餐约会,而介绍所——布莱恩斯顿广场联谊中介所——在一开始则想当然地把这个当作是优先考虑的重点;如果对方有这样的特意安排,她也不会拒绝,只要那人还算顺眼,能让她觉得称心。她接受约会,不过并未直接考虑到结婚,当然也没有将结婚的可能完全排除在外。
她认识的人都不知道她是布莱恩斯顿广场联谊中介所的一位顾客,但之所以隐瞒,倒也不是她觉得这有什么可羞耻的。如果熟人朋友们知道了这事,或许会引发一点点惊讶猜疑,但她可以轻松地就应付过去。更难应对和敷衍将就的——而且一直如此——是那种很不舒服的感受:不管是从介绍所内部的办事方式还是从它所安排的那些约会来看,真相或者说事实都看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至少她清楚自己当时是怎样诚实地填完那张个人详情表的,在每一个选项的小方框中划勾之前,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她都很仔细地查看斟酌了一番;当然她也如实写下了自己的年龄——今年五十一岁。在约会的时候,她也尽心尽力,不允许有任何的错误印象或误解;一旦发生,便随即去澄清。但即便如此,那种同样的不安焦虑总是存在;在她所开始的这种约会活动中,谎言和不实信息似乎是自然而然的——意识到这一点,不免令人忐忑又懊恼。
(完)
本文
选
自
特雷弗
短篇小说集
《出轨》
刊发已获授权,在此向出版方
99读书人 / 上海文艺出版社
表示感谢

出轨
[爱尔兰] 威廉·特雷弗
|著
杨凌峰
|译
威廉·特雷弗2004年出版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他以收放自如、犀利敏锐的笔触,讲述了十二个直抵人心的动人故事,呈现了一个失落的世界。故事里大多是时代的落伍者、小人物、失意者与边缘人,游离于现代社会进程的主流之外,他们既有悲戚、痛苦、无助、孤独的一面,也有着荒诞、贪欲、狡黠、罪恶的一面。而对于这些人性或非人性的举止,特雷弗都抱以理解和宽容,充满了轸恤与悲悯。
戳以下
标题
可跳转至
近五期每日读
完整每日读目录请戳文末
阅读原文
每日读
第39期
《
春分之后
》
作者:夏目漱石
每日读
第40期
《
谁掌握了日本女性主义风向标?
》
作者:新井一二三
每日读
第41期
《
在她身边,周围这个枯燥、乏味的世界又算得了什么
》
作者:菲利普·迪昂
每日读
第42期
《
关于我自己,没有更多可说的了
》
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每日读
第43期
《
立体几何
》
作者:伊恩·麦克尤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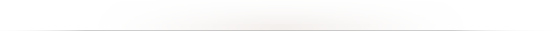
上
海译文
文学|社科|学术
名家|名作|名译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
或搜索ID“
stphbooks
”添加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