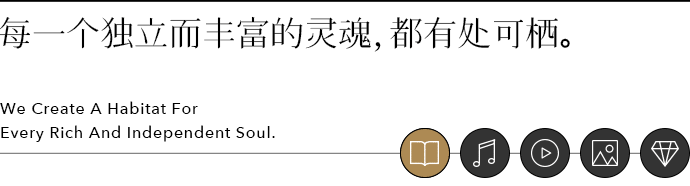
【每周一书】是由单向空间编辑部推出,代表着单向空间选书标准的栏目。每周,单读公号、单读 App、单向街书店公号 三个平台的编辑共同商讨决定书目,每一本书,都是我们的郑重之荐。
我们希望通过【每周一书】,带你在新书之海拾贝;更希望通过【每周一书】,我们能共同跃出书海,奔向这个时而躁动不安,时而寂静无语的世界。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后期的美国,人们不再想把命运交托给别人了。可狂热的英雄主义、战后的精神溃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萧条,共产主义思潮等种种接连不断的冲击,将人从精神的根基上打翻,让理想和野心都成为草芥。有人希望以宗教式的避世放逐来完成自我救赎,也有人渴望激进地闯进自由之地,挣脱时代牢笼。可似乎不管如何挣扎,都无法改变被囚禁的命运......如何才能抵抗时代的洪流?在《囚鸟》中,库尔特·冯内古特洞见了人类最无奈的窘境:必须要先承认“我们都是受困的‘囚鸟’,既渴望逃离,又踟蹰不前”......

我们都是受困的囚鸟
朱玥
“科幻小说”是被严肃文学划分开来的流派,尽管它常常只是以倒置了的时空视角,反观人类的现状和困境。库尔特·冯内古特对这过于笼统的划分不满,可充满讽刺的是,多数读者“结识”冯内古特也源于这个他自嘲的标签——“科幻作家”。
他数次调侃自己这个身份,甚至说:“我八成是在哪里冒犯了某个人,因此得不到他们的信任,害我成不了严肃作家。我断定这是因为我写了有关科技的东西,而就算是第一流的美国作家,对于科技也是一无所知。”也许因此,科幻小说家才频繁地变成他作品里反击荒谬人世的角色,像《冠军的早餐》,那个叫基尔戈的老男人因言辞激烈的作品一朝成名,倍受尊敬,生活优越,但其实他有一种不符年龄的顽劣,每个毛孔都往外张着抵抗现实腐蚀的劲儿。
可无论怎样定义冯内古特都无法完全贴切。比起“科幻作家”、“黑色幽默作家”,他更像是顽童、疯子与睿智的洞察者。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起大落的政治格局和德裔身份带来的文化夹击都让冯内古特置身“边缘”,他清楚个体处在时局洪流中的感受:战争、政局、亟待重建的社会和生活都是重力,人再怎么挣扎,都只能是无奈又无处可避地触地。

库尔特·冯内古特
这样的经历促成了《囚鸟》。相比起冯内古特的其他作品,它的风格独树一帜,谈不上明显的科技元素与足够狂放的幽默,连往日书中放肆的涂鸦也消失不见。他把所有的思虑都压缩成不易察觉的文字囚笼,用压抑无奈的气氛将你引入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尼克松下台后的美国,把放大镜对准那些惶惑的自由知识分子:
故事中的主角斯代布毕业于哈佛大学,任职政府官员。但那有什么用处呢?他没有像传统的理想定律那样顺风顺水,野心勃勃。在爱情中他迷糊被动,需要爱人们救济与养活。而工作上,虽曾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参与工人运动,却无法忍受和“工人阶级”的群众为伍,最后成为出卖伙伴的罪人。担任过尼克松的青年事务特别顾问,但他的工作只是个被架空的名号,唯一引起人注意的——是烟抽的太多......如此不值一提,却还成为政治事件的无名丑角,一生中三度遭遇牢狱之灾。
活得如同儿戏的,不仅斯代布,还有疯癫的富婆,坚定“让上帝失望”的官员、被战乱钳住咽喉的天才女孩,隐藏的科幻作家......如何生又如何死,他们连自己都摸不清头脑,放弃了挣扎的主动权,偶有一两位清醒者,也难逃那只操弄命运的手。
那只手是被少数人操弄着的历史,和作者所写“把年代用大写字母写,好像它们是人名”一样,时代被拟人化成巨人,与普罗大众争夺主宰权,让人的自我认知逐渐失血死亡。从萨柯与凡才蒂事件起,到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希斯和钱伯斯事件,朝鲜战争,最后到水门事件......那一代人从出生起就浸泡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焦虑中,尖锐的社会差距危机四伏。狂热英雄主义、战后的精神支柱溃败,经济萧条,共产主义的传播......这些巨浪接连不断,将人从精神根基上打翻。像主角那样曾经理想、激进的自由知识分子更因这伤害而日渐趋于封闭、保守。大众文化与社会精神危机不断撞击精英文化,理想抱负沦为草芥,它给予人机会,又再将人推至更深的渊崖。人已不再是个体,也是一整代游魂的群像,难以逃避被抉择的命运,也无法避免随之而来的灾难。
可以说这是一本伟大而正经的小说,无论你生于何时,哪怕从未读过他的作品,也迷惑于叙述线索中解构式的亦真亦假,虚虚实实,这本书仍能让你倍感亲近。它甚至跨越时代地指清人的处境,为迷惑之心作答:我们都是受困的囚鸟,既渴望逃离,又踟蹰不前,最后坠入无声息的死亡......读罢,或许还会心生出现代版的《局外人》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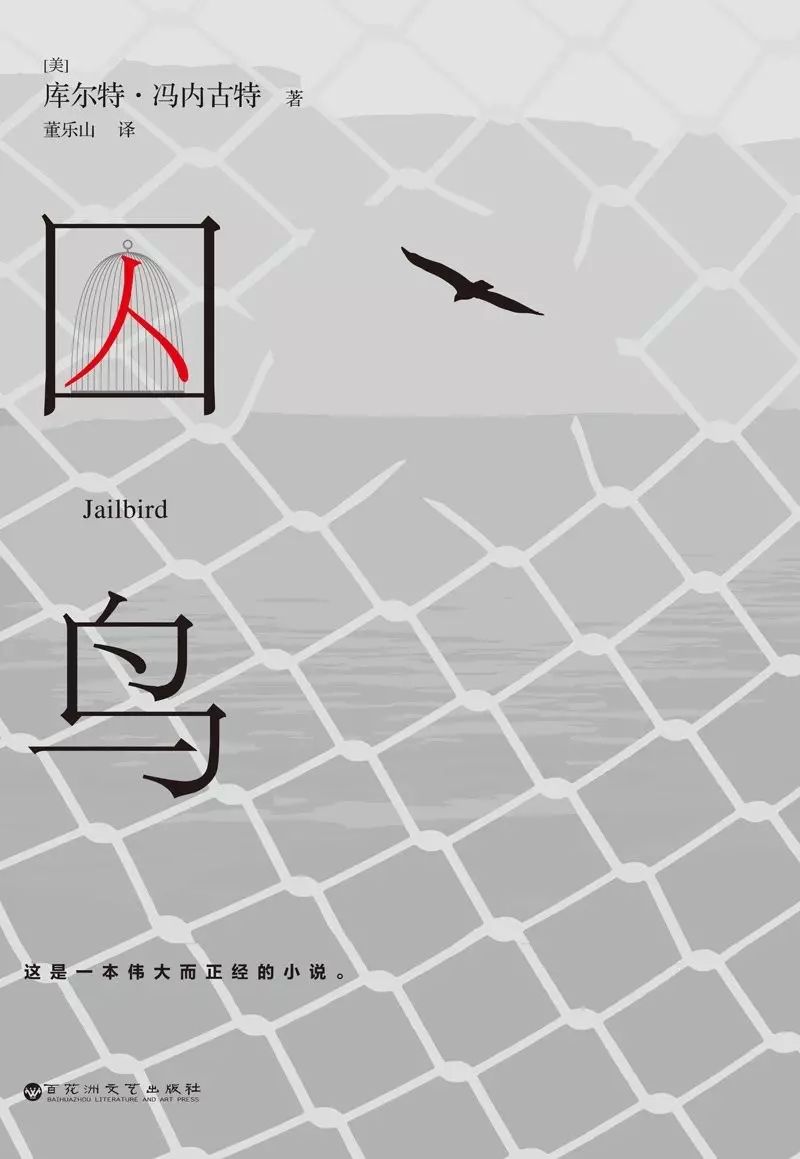
作者: 【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译者:
董乐山
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7 - 6

囚鸟(节选)
库尔特
·冯内古特
这两个孩子的祖母,我已过世的妻子露斯,生于维也纳。她们家在那里拥有一家珍本书店—那是在纳粹分子把铺子强占去以前。她比我小六岁。她的父母和两个兄妹在集中营遭到杀害。她自己被一家基督教徒藏了起来,后来在一千九百四十二年被查获,同那一家的家长被一起逮走。因此,她本人在战争的最后两年是关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集中营里,最后被美军解放的。后来,一千九百七十四年,她在熟睡中死去—病因是心力衰竭,那是我被逮捕前的两个星期。不论我到哪儿去,不论如何狼狈,我的好露斯总是跟着一起去的。如果我对她的付出稍有钦佩的表示,她就会说:“我还能到哪儿去?我还能干什么?”
她可以当个出色的翻译家。她对外语能应付自如,而我在这方面就不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在德国待了四年,但从来没有学会德语。而欧洲各国的语言,露斯无一不会,至少能说一点儿。她在集中营里等死的时候,就请其他被囚的人教她她原先不会的外语,以此作为消磨时间的办法。这样她就精通了吉卜赛人的罗马尼亚语,甚至学会了一些巴斯克语的歌词。她也可以当个肖像画家。那是她在集中营干的另外一件事:用手指蘸上灯上的烟油,把过往人的肖像画在墙上。她也可能成为有名的摄影家。她十六岁那一年,也就是德国吞并奥地利前三年,她在维也纳拍了上百个乞丐的照片,这些乞丐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致残的老兵。这些照片出了集子,我最近还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发现了一本,让我又伤感又惊叹。她也会弹钢琴,而我则五音不辨。我甚至不能跟着调子唱“莎莉在花园里”。

二战纳粹集中营,资料图片
我什么都不如露斯,你可以这么说。
到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我开始不走运了,尽管我在政府中担任过种种高级职务,尽管我认识不少重要人物,但却哪儿也找不到一个体面的差使,这时全靠露斯拯救了我们在契维蔡斯郡受人冷落的小家庭。虽然她开始碰了两次钉子,情绪很消沉,但后来说起这两次失败来却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她第一次碰钉子是到一家鸡尾酒酒吧去弹钢琴。老板不要她,说她弹得太好了,他酒吧里的顾客“……欣赏不了这种高雅的情趣”。她第二次失败的尝试是给人家拍结婚照。照来总是有一种战前的阴暗气氛,怎么修版都涂不掉。好像整个婚礼宴会慢慢地要在战壕中或者毒气室中收场似的。
可是后来她当室内装饰家却成功了,她用水彩画来招徕顾客,为他们装饰房间。我当起了她的笨手笨脚的助手,给她挂窗帘、靠在墙边举起墙纸的样片、给她接顾客的电话、跑腿、取货、送货等等。有一次我把价值一千一百元的蓝色平绒窗帘给烧了。怪不得我的儿子从来不尊重我。
他哪儿有机会尊重我呢?
我的天—他的母亲这么操劳,努力供养这个家庭,省吃俭用,勤俭度日。可是他的那个失业在家的父亲,却总是不争气,碍手碍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最后为了抽支烟,把价值一大笔钱的窗帘付诸一炬!
哈佛大学的教育真是好!做哈佛大学出身的人的儿子真光荣!
这里插一句,露斯身材娇小,皮肤黝黑,颧骨很高,双目深陷,一头乌黑的直头发。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德国纽伦堡,那是在一千九百四十五年八月底,她穿着肥大的军用工作服,我还以为她是个吉卜赛少年。我当时是国防部的文职人员,三十二岁,以前没有结过婚。我在战时一直是文职人员,但掌握的实权比陆海军将领还大。当时我在纽伦堡第一次看到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不禁大吃一惊。我是被派去照看美、英、法、俄四国的战争罪行审判代表团的膳食和住宿问题的。我在此以前曾在各地为美国士兵设立休养中心,因此对酒店的业务稍懂一些。

二战时期的美国妇女,资料图片

二战美国女兵,资料图片
吃喝住方面,我在德国人眼里简直可以说是个独裁者。我的工作用车是一辆白色的默塞德斯轿车
(默
塞德斯 Mercedes:现译作梅赛德斯,即奔驰,全名是梅赛德斯-奔驰 Mercedes-Benz )
,这是一种四扇门的敞篷车,前座有挡风玻璃,后座也有挡风玻璃。它还有个警笛,前挡板两头都有小插座,可插国旗。我当然插上了美国国旗。这汽车一定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它是集中营创始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当初不可一世的时候送给他妻子的结婚纪念日礼物。我不论上哪儿去,都有一个带枪的司机。读者可别忘了,我父亲就当过百万富翁的带枪司机。
八月间的一天下午,我坐车经过纽伦堡的主要大街科尼希街。战争罪行法庭原来在柏林开庭,如今要搬到纽伦堡来,只待我把一切准备妥当。大街上仍到处是瓦砾,正由德军战俘在清除,他们是在美国黑人军事警察炯炯的目光监视下干活的。当时美军仍实行种族隔离。每一支部队不是全黑的就是全白的。不过军官除外,不管什么部队一般都是白人。我当时没觉得这样的安排有什么不对。我对黑人一无所知。克利夫兰市麦康家的宅邸里没有黑人佣仆,我上学的学校里也没有黑人。甚至到我当共产党员的时候也没有同黑人交过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