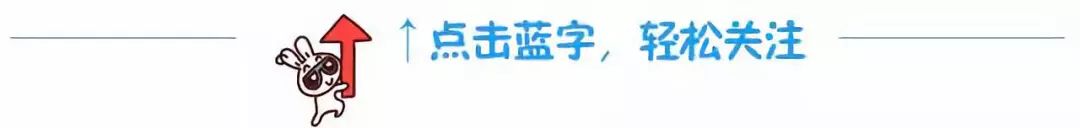

2018
年
6
月
27
日
来源:中国旅游报
作者:易开刚
傅博杰
旅游电商平台推动了旅游产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因平台内经营者的非伦理和非法行为使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从法律视角识别旅游电商舞弊行为的类别与主体责任,进而有效治理旅游电商舞弊,对规范旅游电商经营、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旅游电商平台是指在网络旅游商品交易活动中为交易双方或者多方提供网页空间、虚拟经营场所、交易规则、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供交易双方或者多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的专门化信息网络系统。
本文所指的
电商舞弊是指在消费者使用旅游电商平台过程中,电商系统内发生的不正当、不诚信、导致市场经济秩序遭受破坏的违法行为
,涉及电商平台、平台内商户或经营者、消费者三大参与主体。
近年来,依托现代科技的电子商务迅速占领各大消费市场,电商平台亦渗透进入公众的消费模式当中。电商平台取代了传统的实物交易模式,创造了消费者与经营者的线上交易场所,大大降低了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但也
因其虚拟交易特点增加了平台交易的不确定性与舞弊易介入性,减弱了监管部门对其可防控度。
旅游电商平台在旅游消费日益大众化、个性化的背景下,大大推进了旅游产业的发展,但同时
也因为平台内经营者的非伦理和非法行为给旅游消费者带来了不良效果,损害了消费者权益。
从法律视角识别旅游电商舞弊行为的类别与主体责任,并提出有效治理旅游电商舞弊的建议,对规范旅游电商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律视角下旅游电商舞弊行为的类别与主体责任
(一)法律视角下旅游电商舞弊行为的类别
1.
开展虚假宣传及组织虚假交易行为。
对主观方面存在故意的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新修订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
于第
8
条作出明确规定,并增加组织虚假交易行为之责任认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亦于第
20
条作出否认上述行为正当性的规定。
虚假宣传或虚假交易传递给消费者错误信息,剥夺消费者对商品的知情权,使得消费者“不得不”在交互信息断层情况下做出交易选择,损害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2.
对虚假宣传及虚假交易行为不作为。
《侵权责任法》
于第
36
条作出规定,在旅游电商平台不知情情况下,平台内经营者出于不正当竞争目的实施舞弊行为,被侵权消费者有权向平台提示其平台上的内容构成侵权,若平台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则构成对侵权行为的放任,具有间接故意,视为与平台内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如果平台明知平台内经营者舞弊行为仍不采取必要手段,放任侵权结果发生,同样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反之,则适用“避风港”规则,旅游电商平台免于担责。
网络交易平台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而未采取必要措施,亦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4
条成为平台内经营者与平台承担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
3.
利用格式条款限制消费者正当权利。
格式条款是旅游电商交易中约定消费者权利义务的常见条款形式,其特点为受众广、内容格式化,易使消费者对其内容放松警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6
条规定,格式条款应该公平公正。
舞弊行为背后平台内经营者制定的不退换不退款等规定,平台捆绑服务等公告,都属于不公正不合理的条款,属于主观故意的舞弊行为。
4.
诋毁行业竞争者误导消费者行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12
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实施影响其他经营者提供服务的行为。该条款同样适用于旅游电商舞弊。
在旅游行业竞争中,某一经营者恶意干扰其他竞争者合法经营活动,容易导致旅游市场竞争引导消费选择机制的失灵,消费者信息接收受阻碍,从而引发旅游电商舞弊行为的不良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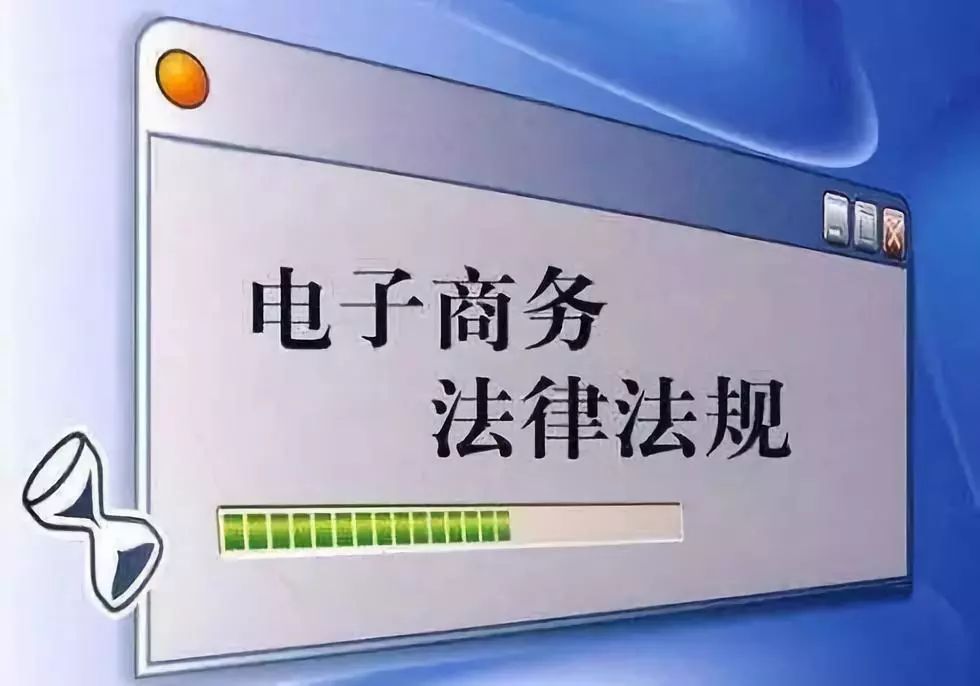
(二)法律视角下旅游电商舞弊行为的主体结构
法律主体分析是研究旅游电商责任认定法律适用的前提和基础,在此笔者认为旅游电商舞弊行为的主体结构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
平台内经营者构成第一责任主体。
平台内经营者是电商平台运行过程中活跃度与参与度最高的主体。《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8
条、第
20
条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0
条对其开展虚假、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组织虚假交易等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
平台内经营者违反禁止性规定且旅游电商平台已尽到注意义务,则平台内经营者单独承担法律责任。
2.
旅游电商平台构成第二责任主体。
旅游电商平台作为提供服务的法人组织,其经营者地位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
条得到明确。旅游电商平台出于直接故意的主观目的组织无过错经营者进行虚假交易,为取得相关市场优势地位而实施舞弊行为,适用该法第
8
条之规定,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经营者提供真实、全面信息,在平台进行真实合规有效交易,因平台违规违法导致不法交易的,旅游电商平台单独承担法律责任。
3.
旅游电商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旅游电商平台归属网络服务提供者,是适用《侵权责任法》中网络侵权者与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承担模式之前提。依据国家工商总局
2014
年公布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及商务部《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交易规则制定程序规定(试行)》,电商平台属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范畴。据该法第
36
条,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侵权者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定情形为违反“通知与取下”规则与违反明知规则。
旅游电商平台明知平台内经营者实施舞弊行为但不采取必要措施,导致消费者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或消费者做出平台内经营者侵权提示时,平台仍未采取必要措施阻断舞弊结果的发生,旅游电商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特殊法优于一般法之法律适用原则,目前已通过二次审议的《电子商务法(草案)》是最具电商针对性的未成形狭义法律。该法在第
25
条赋予电商平台管理平台内经营者及经营活动的权利,可见其确定电商平台注意义务的意图已十分明显。由此,
违反注意义务带来的连带法律责任也在意料之中。
二、旅游电商舞弊行为主体责任确定的困境
旅游法
作为规制旅游业最直接的法律,主要针对旅游者、旅行社、旅游经营者三大旅游主体,该法除在第
48
条增加对发布旅游经营信息的网站的义务外,并未对旅游电商之旅游活动作明确规定,且又因立法目的
忽视了旅游者作为电商舞弊行为主体之情况
。旅游电商舞弊行为的责任确定困境主要有:
(一)现有法律难以直接分辨旅游电商平台责任
1.
平台法律责任构成要件与实际平台的责任认定难以匹配。
作为新修订法律,《反不正当竞争法》重点对互联网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规制,
将旅游电商舞弊行为法律责任归咎主体列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两方
。分析该法第
8
条专门性条款的构成要件,“组织”“帮助”于主观方面都附着一定主动性而将舞弊行为主体偏向平台内经营者。但在实际操作时,旅游电商平台通常表现为未尽到注意义务等不作为行为,
严格说来,参照条款对于主观方面的责任认定要求,实施消极行为的平台难以成为责任主体。
2.
平台注意义务之合理标准难以有效界定。
旅游电商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的注意义务以合同关系为基础产生及发生作用,而非基于具有强制保障力的司法权或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平台注意义务应致效果,进而模糊了平台注意义务之界限。加之
旅游电商平台内交易价格的波动性很强,旅游电商平台的注意义务得到更好的隐蔽,追究旅游电商平台的责任难度较大。
3.
平台积极预防行为对其舞弊责任认定的影响。
事实上,大型旅游电商都在积极做出旅游电商舞弊的治理和应对。比如,阿里飞猪针对旅游供应商舞弊行为做出相关应对措施:加入中国企业反舞弊联盟;开发系统风控模型阻断舞弊行为扩张性蔓延;同步研发黑名单库弥补用户交易模型的命中率偏差等等。在旅游电商平台已经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和治理平台内的舞弊行为时,
如何认定平台经营者、产品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的责任,则应根据平台采取措施的时机、舞弊行为效果减轻等实际情况进行判断。
(二)平台内部人员舞弊责任划分不清晰
平台内部人员出于不正当目的对舞弊行为纵容、包庇等引发侵权的责任,成为旅游电商责任主体认定的一大空缺。该责任于平台内部可由规章制度明确,
但对外部(消费者)产生的侵害是由内部人员负责还是参照雇主责任由平台负责,法律规定并不明晰,对于该类内部人员的直接法律规制亦处于空缺状态。
(三)消费者舞弊行为性质缺少法律界定
旅游电商舞弊行为的认定较为困难,尤其是在消费者参与的情况下,很难判断是不是平台和经营者舞弊。
比如消费者在明知消费者刷单的情况下仍购买该旅游商品,一方面消费者自身利益受到损失,另一方面也会纵容舞弊现象的泛滥。消费者对舞弊行为的消极式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舞弊行为对电商市场的破坏力度。出于相对公平原则,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向来是法律保护的对象,对消费者的责任归咎有待法律更加完善。
三、对旅游电商平台法律治理的建议
(一)完善认定旅游电商平台责任的相关法律规范
我国网络营销方面存在较大的法律空缺,对于旅游电商方面的立法更是有待加强。
立法机关应当对旅游电商运营的重要过程设定法律法规,包括:确立商家进入旅游电商平台的旅游业准入专门标准;对旅游交易合同,尤其是格式条款进行权威性审查;对有损消费者利益的网络旅游诈骗等犯罪活动进行定罪,等等。同时,对旅游商家主体资格进行行政确认,设置相应的处罚性条款。
各大法律对于旅游电商平台作为责任主体的规定存在空缺
,笔者认为,结合旅游法与《电子商务法》制定专门法规以制约旅游电商舞弊行为,可实施性较强。此外,应增加对旅游电商平台舞弊行为预防措施的法律确认,对旅游电商平台责任类型加以概括性规定,对平台内部人员及消费者协助舞弊行为作出违法性认定及责任承担确定。
(二)设置明显的舞弊行为责任认定要件
《侵权责任法》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