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因民族国家而生”
。是
朱与非
兄在
《评欧洲保守主义的“巴黎宣言”》
中的案首语。原本这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一句箴言,既包含了政治理论上的应然性,也包含了政治现实上的实然性,如果
基于政治学来理解是自明的,也可以是自洽的。但是这句话本身也存在语义模糊之处,
“帝国”、
“民族”
、
“自由”
,这些相关联的概念如果不加以限定讨论,仅仅望文生义来理解这几个词,并用历史加以检验,是很难不产生歧义的。这两天在群里围绕这个话题引起了持续激烈的讨论。所以本文的目的是以政治哲学的原理对这个结论做一个演绎,本文也可以看做是前文
《反抗绝望:欧洲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呐喊》
的理论强化版。
帝国
统治形态
帝国统治本身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寻求内部的服从认可,是
一种最普遍最本质的政治关系,
所以决定了帝国的统治对象并不需要界定特殊,只要统治对象愿意服从,都可以纳入到帝国内部,
无所谓寻求一种单一的或者是均质的统治对象,多元是可以在帝国内部得以存在的,也就是说帝国是具有普世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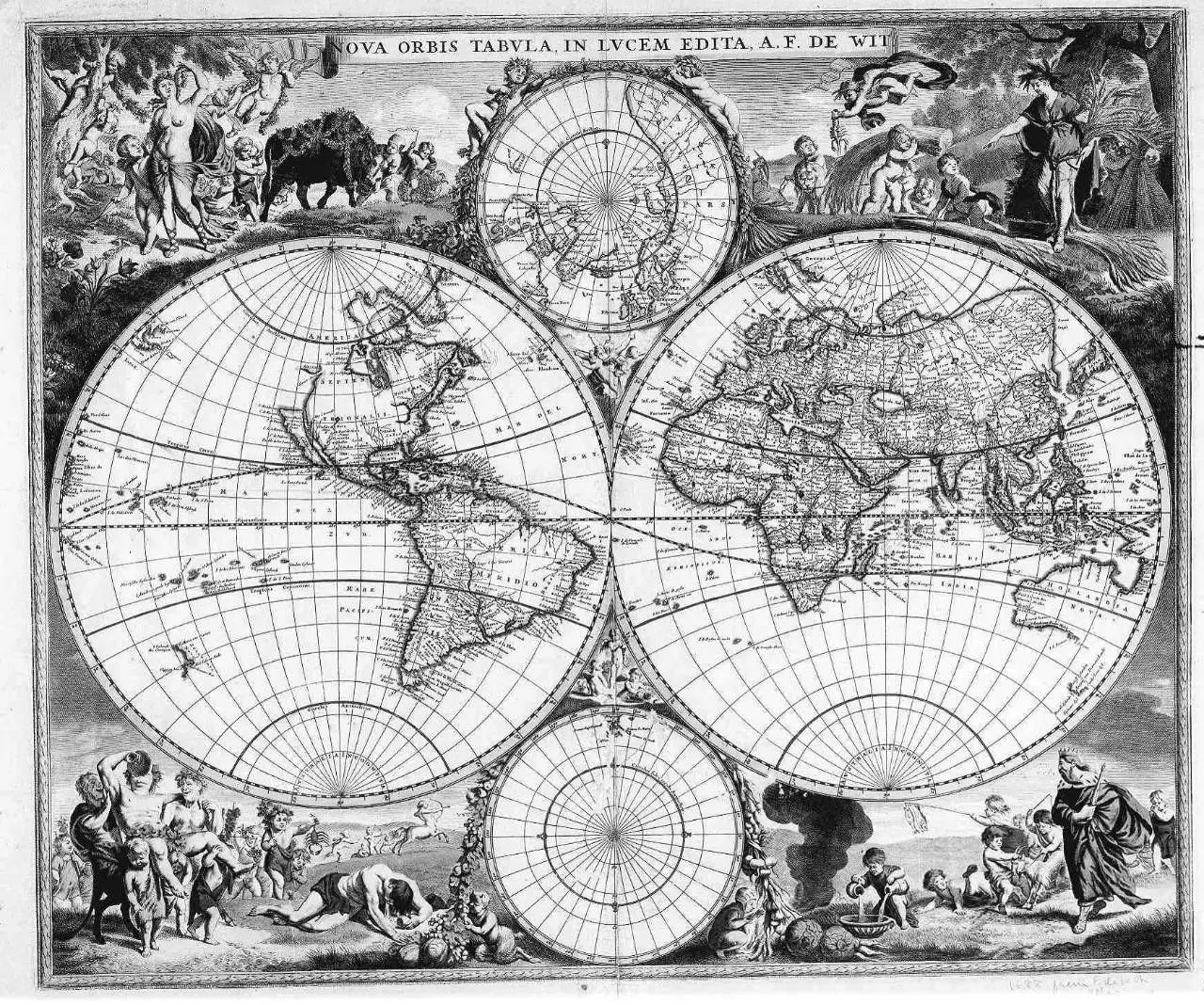
帝国统治权威由暴力的威慑力和德性说服力所决定,这里的暴力威慑力和德性说服力存在一个能力临界点,超越这个临界点,便不属于这个帝国的统治范围之内。
所以,帝国看似普世的统治,又受到
但是帝国权力辐射能力的限制,离中心越远则帝国的控制力越弱,基于这种统治能力的限制,帝国可以通过某种统治意志实现的折中,换取边疆保持某种自治,保证对帝国的效忠。反之,帝国又需要通过统治中心的力量巩固,来保证帝国的统治辐射力的维系。帝国内部的一消一长,则决定了帝国统治需要或者必然存在等级差异。这种
中心和边疆基于等级差决定财富和自由的分配比例不同,在各取所需的目的实现后,帝国达成了权力架构的平衡。
由上可知,帝国统治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由或者不自由,帝国的统治下,人的自由度非常可能是高度的。
注1
人类历史的很长时期内,这种外在统治压力的自由度,成为了人类政治制度的最常见形式。
民族国家
虽然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得民族国家的声望有些臭名昭著,甚至已经和
“自由”
这个概念对立起来。无疑,这是一种被意识形态笼罩的一层迷雾。如果我们拨开迷雾,进入到思想观念史的脉络去重新审视民族国家产生的思想根源,甚至会发现,民族国家是基于一种
“自由”
诉求产生的政治形态。
通常在思想史上,将公元前500年到基督降生这段时期称之为
“轴心时代”
,希腊诸子、先秦诸子、印度宗教以及犹太先知等一波思想上的先哲开始思考一些超越性的概念价值,将人的思想空间从现实拓展到超验、抽象的维度。这样的思想实践,使得人可以反思自身的行为,也就是说,人类的行为从此有了超越性的
“是非对错”
的标准,人类可以根据这种超越概念意识反过来追问自己的内心,检视自我的行为。

到了16世纪的欧洲到20世纪这几百年时间里(也可能没有结束),人类又迎来了第二次思想的突破,虽然是否能称之为
“第二次轴心时代”
存在争议,毕竟我们生处时代与之距离过近,还无法基于历史的纵深做出全面性概括。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这一次的思想革命,相比人类过往的历史存在的特殊现象。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个人开始可以从血缘、地缘、国家这些旧的社会群体中脱离出来。其中标志性的思潮就是自由主义的产生。自由主义说服个人从社会本体论的
“脱嵌”
,个人具有成为自身主权者的理据。当人尝试了这样的想象,接受了这样想象的可能之后,就很难在回归到原镶嵌式的本体想象当中去。
注2
但是,当个人能将自己从集体解放出来,将自己想象成为原子化的个人之后,还需要面对一个现实困境,因为人类至今没有办法走出亚里斯多德的断言
:“人是天生的城邦动物”
,这里我们可以将
“城邦动物”
这个概念理解为
“群居动物”
或者
“共同体生存”
。因此当人成为社会本体意义上原子式的个人,摆脱原有的血缘、地缘、政治缘的生存结构想象之后,就面临一个新的现实困境:
和谁生活在一起?
基于人类对于习惯、历史、安全感、自我肯定、经济成本等因素,选择一个与自己接近同质化的群体组建政治共同体,毫无疑问的属于最佳选择,毕竟同质化的社群,可以将社会摩擦大幅度降低。
注3
而在所有的同质化共同体中,民族主义是最粗暴最有效的情感动员模式。所以,民族主义的狂飙也就催生了民族国家的诞生。
注4

如果说习惯、历史、
安全感、自我肯定、经济成本等可欲诉求是形成民族国家的
客观理性动力的话,那么在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其实还有一种主观产生的动力因。因为民族是一种自我想象的放大延伸,所以民族作为集体,所表达的情感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个人情绪的集合。因此,我们可以借用黑格尔提出,并由科耶夫和福山发扬光大的
“主奴斗争”
概念来理解民族国家形态的演进。在科耶夫对于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创造性的解释中认为:人类基于
“被承认”
的欲望是人行为的根本动力,整个人类历史都是为此展开的。因此,当一个群体完成民族想象之后,绝不会满足于本民族处于帝国等级秩序的次级地位,而是要寻求政治上的被承认,帝国和民族之间的
“主奴斗争”
也就此展开。
注5
虽然,人类并没有进入科耶夫所预言的那样,进入
“普遍同质化国家”
,但是随着自由主义的思潮在国内政治获取主导性地位之后,作为个人主义放大版的民族国家也同样取得了国际关系中的普遍形式的地位,当然这同样也意味着正当。
民族国家的自由观
或许是因为以赛亚柏林爵士关于
“两种自由”
的定义实在过于经典,以至于这种划分遮蔽了自由的复杂面向。用最通俗的话来概括
“消极自由”
,那么就是免于被强制;而
“积极自由”
,就是无所顾忌的去实现自己的意志。通常基于二十世纪的历史教训,人普遍的倾向于肯定
“消极自由”
,而否定
“积极自由”
。对此,共和主义一直批评自由主义的自由观过于简化,需要将
“自由”
纳入一个现实主义的考察中,而不只是抽象的演绎。所以,共和主义认为:
离开政治共同体,绝无天赋人权存在,自由国家是自由个人的前提。个人自由与国家政体存在现实性的逻辑关联。
在理解了共和主义的自由观之后,我们可以将民族国家的诉求看做是共和主义自由观的一种实现方式。只有一个自由的民族共同体,才能保障个人的自由。所以,当民族主义狂飙的时候,不可否认其中所蕴含的自由诉求。即使我那最反感的民族主义的朋友克罗采和春天在
《谎言与幻想:民族主义二百年》
中,也在开篇中提到:
“民族主义是这样一种奇妙的意识形态,当它代表的人群居于少数的时候,它代表着民族平等、不受压迫、文化自主。”
也即是意味着帝国和民族对立的结构中,民族主义的自由面向。
虽然民族主义存在一个自由的面向,但不可否认其中所包含的积极自由的侵犯性。
民族主义在完成建国大业之后,成为主权者,行使主权者的积极自由去侵犯境内更弱势的少数群体。这种行为似乎令人难以接受,但是难以接受是一回事,不可避免又是一回事。
注7
人类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不会受到哲学规范的限制,特别是当主体民族成为国家的实际主权者之后为所欲为,那么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还没有高于国家主权的国际法对此进行制裁监督。根据经验,不用怀疑,人在获得绝对的权力之后,会放纵自己的人性,那么民族国家成为主权者之后一样会,目前没有任何方式可以避免,只能由美国作为
“世界警察”
的存在才能做到有限的威慑。
注8
欧洲的出路
施米特在
《政治的概念》
中指出:
“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如果一个民主制国家始终不渝地承认普遍的人类平等,它就会在公共生活和公法层面上失去其实质。”
今天欧洲国家就是因为丧失了民族国家这个政治概念前提的本位性,忽视了国家的根基来自于主体民族本身,才使得在
“文明的冲突”
面前束手无策。
“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朋友与敌人这对概念必须在其具体的生存意义上来理解。”
欧洲的出路在于迫切的需要重新划分敌我,重新政治化。
注9
目前存在两种方案。第一种,是以欧洲政治采取一种温和的社群主义进路来安排社会秩序。即强调所有的外来者入乡随俗,服从欧洲的现有法律秩序和社会习俗。而不是坚持自由主义所预设的那样,个人在不侵犯他人的前提下,自己享有对自己的自主权。第二种,则是以一种消极防御性的方式采取政治上的排外主义。以一种“
文明共同体”
的身份,重新拾回文明自信,对于外来文明适度的歧视,以一种强硬回应姿态给予相当的威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