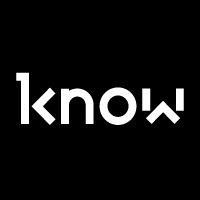“在我成人的过程中,有一个分水岭一样的时刻:我把那个时刻视为我作为一个青少年的终结一刻。它是我认识到这个世界无法自圆其说的复杂性的开始——如果说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充满了愤怒和攻击性的青少女,在那之后我对生活的负面情绪开始转变为无奈和厌倦——但那也是我真正开始走上‘成为自己’的道路的一刻。
那就是我意识到父亲有他自身的创伤和扭曲的那一刻。
”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这个像写作般给我们留言的粉丝一样,为了逃离与父辈之间的不同,决心远走,而在远离故土的地方生活、接受越来越高的教育之后,却发现自己与他们之间的罅隙日渐扩大。
她发现自己一方面感到与他们难以沟通,反感他们的价值观,想要挣脱他们对她的控制,但与此同时,家仿佛又是一个永远不能摆脱的地方——这种无法摆脱不仅体现在,
每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总能轻易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他们轻而易举地让我们狂怒、暴躁、哭泣;也体现在,在离开之后,我们却逐渐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们留下的底色。
这种底色里,既有破碎和缺失,也有力量和坚韧,还有明明反对却不经意间沿袭了的行为思维模式。
最糟糕的是,不论我们是否情愿,我们或多或少地理解他们。
我们看到他们的局限和他们自身未解的问题,因而无法一味简单地对他们感到怨恨和愤怒——这是一种更复杂无解的心情。
在心理学领域,有这样一个概念:
“创伤的代际传递”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它指的是,上一代的创伤会被传递到他们的后代身上,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话题。
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它?创伤的代际传递有可能停止么?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谈一谈。

什么是代际创伤?
代际创伤(Transgenerational Trauma)指的是
通过PTSD(创伤后应激综合障碍)的机制,从创伤事件的第一代幸存者转移到他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创伤,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创伤的代际传递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对代际创伤的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研究者在针对“集中营综合症”进行研究时,发现集中营、大屠杀
幸存者的孩子中也出现了大量寻求精神援助的情况。
随后,研究者发现,代际创伤有可能会影响到第三代,比如,
大屠杀幸存者的第三代(孙辈)在儿童精神诊所求助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3倍
(Fossion, 2003)。目前,对于代际创伤的研究基本集中于三代以内,即通常来说限于能够有直接接触的范围。
* 在讨论创伤的代际传递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创伤”。
创伤性事件通常指的是与(实际或威胁性的)死亡或严重伤害相关的事件,暴露在这样的事件中,会使人感受到害怕、恐怖、无助的情
绪
(APA, 1994)。而在“代际创伤”的定义中,创伤事件可以指的是广义的、对于个体而言可能受到的各种类型的创伤,比如虐待、亲人犯罪、丧失、事故等等;也可以是狭义的,即集体性重大创伤事件,比如战争、屠杀、恐怖袭击、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等等,这样的事件往往会在较大的范围内影响到某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代人。
在我国,由于近百年来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代际间的创伤传递格外突出。社会性的集体创伤在近百年间屡屡发生。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父母,大多都经历过“文革”(1966-1976),而爷爷奶奶那一辈人,则不仅经历过文革,还可能经历十年内战(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他们两代人还都有可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大跃进”、“反右”等一系列发生在上世纪50-70年代之间的政治运动。
几乎可以说,
在我国早于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人,都或多或少是集体性创伤事件的承受者;而与之同时,他们接受的精神健康服务却很少。
这也是为什么,代际创伤在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本文讨论的重点,不是上一代个体经历的创伤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而集中于集体性创伤事件带来的创伤传递,因为这可能是更有普遍性的一个角度。

创伤通过亲子教养向下一代传递
近几十年来,在对代际创伤的研究中,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直接的、具体的创伤传递(即父母在创伤后的精神症状直接导致孩子的精神症状,比如两代人都表现出PTSD的症状),发展到间接的、非具体的创伤传递(即
创伤事件影响了第一代人的认知、情感,影响了他们作为父母/长辈的功能,进而影响到孩子的精神健康
)(Kellermann, 2001)。
精神分析师Plaenkers(2014)认为,集体性事件引发的代际创伤的特点是,那些无法想象、无法承受的创伤从个体记忆中消失了,经历者试图掩盖和忘记它们;它们也从公共话语中消失了,往往在一段时间以后不再被主流所谈论。但它们仍然存在于个体的无意识中,通过教养模式、沟通方式,通过上一代人的“言传身教”来向幸存者的后代传递。Albeck(1994)形容说,代际创伤对幸存者后代的影响,就仿佛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没有伤口的疤痕”。
第一代的幸存者对后代的沟通和教养方式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1. 对创伤的过度沉默或者过度分享
在和后代沟通的过程中,上一代人对于创伤经历有两种典型的处理方式,即过度沉默或过度分享,它们都是不健康的。
a. 过度沉默:
在创伤的第一代承受者中,很多人会努力让自己忘记那些痛苦的经历,将这些记忆隔离起来,并压抑自己与他人沟通的欲望,几乎不向他人提起(Harkness, 1993)。
比如,在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父母会不再提起战争时期的事情,孩子也会不去问自己的父母在纳粹时期经历了什么,他们能感觉到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Tatlow, 2016)。尽管如此,后代仍然会感受到那些被父母压抑着的痛苦、愤怒或者悲伤的情绪。他们不会直接询问,但会去努力猜测上一代人的感受,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种种蛛丝马迹,去拼凑一个故事的原貌。在中国,经历过贫穷和迫害的家庭也会有类似的表现。
b. 过度分享:
与过度沉默相对应的另一种极端的沟通方式,是上一代人会以不恰当的方式去反复分享自己的经历。这一方面可能会令他们的后代感到恐怖和害怕,产生一些歪曲的认知;另一方面,对这些经历的讲述也会造成冲击,因为它们和后代所处的环境、经历的人生是如此不同。比如,经历过饥荒的上一辈人可能会经常和孩子说这样的话:“现在你经历的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根本不能和我们那个时候相比”,或者,“我们小时候只能吃树皮,一家人都在饿肚子,现在你能吃上肉就应该很满足了,不要挑食”。
类似的频繁表述很难被辩驳,它们有可能会
导致过于严苛的教养方式,比如幸存者会以与自己相同或类似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后代,
并不符合现在的生活环境;也可能会
否认
孩子现在所经历的挫折和创伤,认为这些不值一提,使孩子产生怀疑感、被否定感。
同时,也使得他们彼此都固守在自己的价值观和处境中,很难真正地相互理解,从而影响代际间的情感联系。

2. 过度控制
通过对美国老兵和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都发现,
幸存者的教养方式呈现出的显著特点是过度控制。
他们会突出表现为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或溺爱,以及过度苛求,比如制定严格的规范和严酷的惩罚等等,这
都使得
后代很难完全地脱离父母或长辈而独立(Kellermann, 2001)。
Tomas
Plaenkers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中国文革的心理创伤研究,他认为,文革所造成的集体创伤,使得经历过它的人们怀有极度的不安全感,
他们用一种充满担忧的方式生活,怀有巨大的成功压力,执着于努力奋斗,这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成功来保护自己,让自己免于无助,更少地受到统治者或社会环境的影响
(Tatlow, 2016)。
与之相应的是,他们会对自己的孩子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对于成功的要求。这一方面可能导致对孩子的忽视,即由于过于强调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忽视下一代的情感需求;也有可能导致虐待,比如对孩子施以家庭暴力。
3. 有意识地传递社会规范和信念
社会学习论认为,孩子在照料者的照顾中完成社会化过程,从父母的照料行为中习得社会角色,从父母的身上观察、模仿和学习社会规范和信念。与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地传递不同,这种传递是有意识地进行的(Kellermann, 2001)。
大规模的集体创伤事件,会使得第一代人形成一些坚定的扭曲信念,进而传递到后代身上。比如,经历过大屠杀、政治运动的人会倾向于不信任他人,他们会把这种价值观不断地灌输给后代,会从小和孩子说“要时刻保持警惕”,“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让孩子时刻保持危机感。
代际创伤的影响
创伤的代际传递会影响到幸存者后代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影响到家庭结构,也会提高他们的精神疾病风险。
1. 自我(self)与任务的冲突
作为幸存者后代的孩子是肩负任务的。他们往往会对上一代“受害者”的身份过度认同,拥有对上一代过度的弥补心理等,认为自己有一些必须要承担的任务(Kellermann, 2001)。
任务一:“修复”父母
幸存者后代的任务之一,就是
接收、处理和消化上一代人的负面情感,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
从精神动力学的视角来看,这些情感并不是被有意识地传递的,而是“在无意识中被转移的”。在下一代成长的过程中,上一代人不自觉地外化了受创伤的自我,下一代人则无意识地吸收了上一代那些被压抑的、没有被充分处理的经历、情感和情绪。这使得在一个家庭里,孩子可能反过来成为照料者的“抱持性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本意是指像父母对婴儿进行抱持一样,给孩子制造的一个安全、能够消化挫折的环境),他们努力使得父母能够走出那些创伤事件和负面情绪,同时适应变化的新世界。

任务二:完成父母(未完成的)愿望
无法成为独立个体的孩子,需要完成上一代人未竟的愿望,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对于成功的强烈渴望。
比如,很多父母会将自己遭遇的历史环境、创伤事件作为没能达成人生目标的原因,比如和孩子说“我们那时的考试难度是现在的好几十倍,你要珍惜现在的环境,必须要考上xx大学”,或者在孩子成绩下滑时责怪说,“要不是经历了xx事件,我肯定会成功,不会像现在这样;而你的学习条件这么好,还不努力”等等。
任务三:复仇、改变、记录
以色列的心理治疗师DinaWardi(1992)在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的治疗中发现,许多人都充当着历史事件的“纪念蜡烛”的角色,他们会不自觉地想要为上一辈人表达或者做出改变。比如,有人会选择激进的方式,为自己的父母奔走呼吁,帮助某个历史事件平反,或者在网络上发起反纳粹运动;
另一些则采取更为迂回的做法,从事一些帮助和保护他人的职业,比如律师、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公益从业者等。
对于创伤幸存者的后代来说,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是艰难的。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会感到这些任务与自己身份的冲突:几代人生活在完全割裂的世界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上一代的经历、价值观及身份都和自己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幸存者的后代在家庭以外的环境(比如学校、工作、社交场合)不断接受新的知识和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们又被迫卷入上一代的创伤经历中,去接受上一代因为创伤而被极大改变或塑造的价值观,去和这样的父母或长辈紧密相处。
在身份的建立过程里,他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选择和上一代相近的身份,会使他们自身感到巨大的冲突和痛苦;如果和上一代划清界限,建立新的身份,又会使上一代产生强烈的反对情绪。在很多时候,他们都既想维持和父母长辈的情感联系,又挣扎着想要与他们区分开来。
2. 精神疾病的易感性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可能会具有更高的精神疾病易感性,尤其表现在PTSD、抑郁和人格障碍的易感性上,这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症状的传递”。不过也有研究发现,父母PTSD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孩子的PTSD症状程度没有显著相关,但却
和父母经历创伤后的家庭功能下降、负面教养行为的程度有关
(Harkness, 1993)
。
Kellermann(2001)总结出,以下这些因素最容易引发幸存者后代的精神疾病风险:a. 后代在父母的创伤发生后不久出生;b. 后代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先出生的孩子;c. 双亲都是幸存者;d. 后代是“替代性”的孩子,即在此之前家中曾经有孩子丧生;e. 父母忍受了极端的精神折磨或者重大的丧失,并且结果导致他们的生活被极度地扰乱;f. 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依赖共生关系非常明显,家庭关系的特质表现为“纠缠”关系;g. 创伤在家中被地过少或过多地谈论。

3. 对家庭内部机制和人际功能的影响
由于受到创伤事件的影响,
上一代人的情绪反应可能是不稳定、缺乏一致性的,父母有时回避冷漠,有时却敏感易怒,这使得父母和孩子之间很难建立起安全型依恋
(Kellermann, 2001)。对幸存者后代的研究发现,幸存者家庭内部的机制很可能体现为纠缠(Enmeshment):
这样的家庭是一个高度封闭的系统,家庭成员就好像大海里一群靠在一起的小岛,他们只和彼此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其他人隔绝开。这可能也和父母不信任他人和社会,觉得“外面很危险”有关。
父母和孩子的边界是极端混乱的,他们过度地卷入彼此的人生,子女可能反而承担着父母的“父母”或者“配偶”角色(点击查看“当父母把孩子当做了伴侣”),对彼此承担着过度的承诺 (Klein-Parker, 1988; Harkness, 1993; Kellermann,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