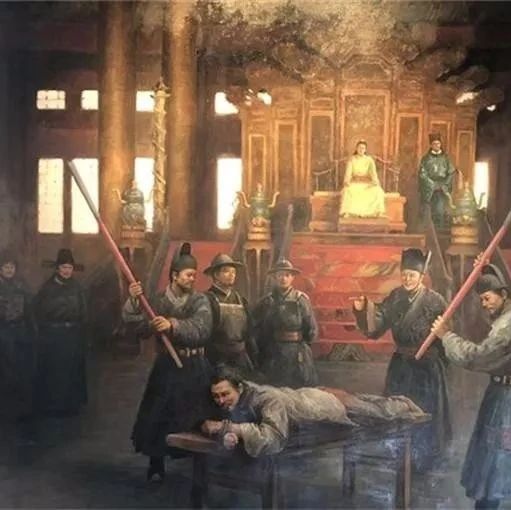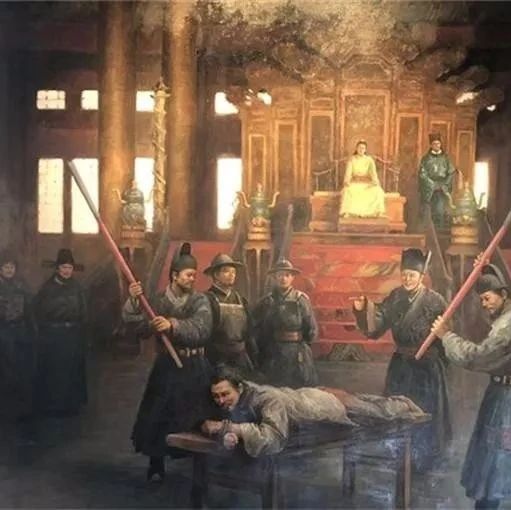本文初稿撰于
2013
年
5
月
14
日至
18
日之间,以“同性婚姻的滑坡”为题,分三部分先后发表于个人博客,作为对
5
月
17
日“国际不再恐同日”的响应。其时该节日的全称为“国际不再恐惧同性恋与跨性别日”(
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and Transphobia
),
2015
年改为“国际不再恐惧同性恋、跨性别与双性恋日”(
InternationalDay Against Homophobia, Transphobia and Biphobia
)。初稿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有幸收获诸多师友及不知名网友的热烈讨论,令我在修改时受益匪浅,在此一并致谢。——作者按
林垚,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LIN Yao, Ph.D. in political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
同性婚姻、性少数权益与“道德滑坡”论
林垚
(
LIN Yao
)
摘要
:
在性少数权益的支持者所遭遇的种种诘难中,最常见是“道德滑坡”(
moral slippery slope
)论。对道德滑坡论的辨析,不仅仅是为了更有效地回应性少数权益反对者的质疑,也有助于澄清“性少数”及“性少数权益”这些概念本身的涵义。本文以同性婚姻合法化为例,从正反两个方面反驳道德滑坡论者。正面的办法是:论证同性婚姻和所有在道德上不可接受的性模式之间存在均关键区别,从而直接拒斥类比、阻断滑坡。反面的办法是:将举证责任转移到反同人士头上,首先要求其给出上述前提中的类比所依赖的原则,而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通过构建相反方向的滑坡,论证这些原则将使反同人士自身陷入道德困境。最后结果表明,反同人士试图在同性亲密关系与某些道德上不可接受的性模式之间建立滑坡,从而在道德上拒绝前者的努力是失败的。
关键词:
道德滑坡论;性少数权益;同性婚姻
Homosexual Marrige, Sexual Minority Rights
and Moral Slippery Slope
Abstract:
The most common challenge amongwhich the supporters of sexual minority rights are faced with is the moralslippery slope theory. The examination of the moral slippery slope theory isnot merely a more effective response to the queries of opponents of minorityrights, but also clarifies the concepts of sexual minority and sexual minorityrights. In this paper, I take homosexual marriage legalization as an example torefute moral slippery slope theory from positive and negative approachesrespectively. The positive approach i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re are keydifferences between homosexual marriage and other morally unacceptable sexualmodes, in order to directly reject any analogy and hold back slippery slope.The negative approach is to transfer the burden of proof to anti-homosexuals, i.e.,to demand them to provide a principle of analogy as a premise for theabove-mentioned argument, then in the same manner to construct inverse slipperyslope so that the anti-homosexuals get into trouble. Finally, it isdemonstrated that it is a failure for anti-homosexuals to construct a slipperyslope between homosexual marriage and some morally unacceptable sexual modesand then to refute homosexual marriage.
Keywords:
Moralslippery slope theory; sexual minority rights; homosexual marriage
一 引言
过去几十年间,人类社会在对性少数权益(
sexual minority rights
)的认识与保护方面,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仅以同性婚姻为例,自荷兰
2000
年首开其端以来,迄今已有
20
多个国家以议会立法、公投修宪、司法审查等各种方式,将同性婚姻合法化;这背后体现的,是相应社会的主流民意对同性亲密关系的态度转向。
当然,欢呼性少数权益在全世界范围的胜利还为时尚早:同性之间的性行为,迄今在
60
多个国家仍属违法,在
10
个国家甚至可被判处死刑;即便在那些已经同性恋除罪化,甚至已经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不论是同性恋者还是其他性少数群体,都仍然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面临教育、就业等诸多方面的歧视。正因如此,为性少数权益辩护,依旧是当下公共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性少数权益的支持者所遭遇的种种诘难中,最常见的大约是各类换汤不换药的“道德滑坡”(
moralslippery slope
)论。比如,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人士,往往会在辩论中祭出如下的质问:“假如把同性婚姻合法化,那就意味着婚姻不再局限于一夫一妻咯,这样的话一夫多妻岂不是也应该合法化?”这背后的逻辑,是将同性婚姻(或其他方面的性少数权益)与某些乍看起来道德上不可接受的性模式(包括性认同、性倾向、性行为、性关系等方面的模式)相捆绑,视同性婚姻合法化(或对其他方面性少数权益的追求)为通向道德堕落的滑坡起点,令支持者望而却步。当然,这并非性少数权益反对者唯一可用的论证策略,但出于篇幅考虑,本文将只围绕这一策略稍作讨论。
这类道德滑坡论的基本推理结构如下:
R
:性少数权益支持者力图辩护的某种“非正统的”性模式(比如同性性行为、同性婚姻、跨性别认同等);
S
:目前绝大部分性少数权益支持者并不力图辩护的某种“非正统的”性模式(比如恋童癖、尸交、人兽交、一夫多妻制、乱伦等)。
[大前提]
如果
R
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那么
S
在道德上也是可以接受的。
[小前提]
S
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
[结论]
R
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
对道德滑坡论,支持性少数权益的学者此前已有若干辨析(
Corvino, 2005
;
Volokh, 2005
),本文与这些既有文献的大方向保持一致,但在整体框架以及具体论证上仍有独到之处。此外,
John Corvino
(2005)
曾将对同性恋及同性亲密关系的道德滑坡式质疑称为“
PIB
论证”,其中“
PIB
”是英文“多偶制、乱伦与人兽交”(
polygamy,incest and bestiality
)的缩写。道德滑坡论的变体虽然并不止于“
PIB
论证”(
R
可能不是同性恋或同性亲密关系,
S
也可能不是多偶制、乱伦或人兽交),但后者仍有一定的代表性;同理,本文对道德滑坡论的辨析虽然主要以同性婚姻为例,却完全可以举一反三地用于辩护其他方面的性少数权益。另一方面,本文的讨论也将说明,性少数权益支持者对童交、童婚、尸交、人兽婚等类比的回应,所依赖的理论资源将有别于对多偶制、乱伦等类比的回应。
对道德滑坡论的辨析,不仅仅是为了更有效地回应性少数权益反对者的质疑,也有助于澄清“性少数”及“性少数权益”这些概念本身的涵义。近年的性少数平权运动通常会采用“
LGBT
”(
lesbians,gays, bisexual, trans- gender
[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
]
)这一缩写来指代相关群体,但也有人建议将其扩展为“
LGBTQ
”(
LGBT + queer
[
酷儿
]
)、“
LGBTQIA
”(
LGBTQ +intersex, asexual
[
间性人、无性恋
]
)等等,以反映对更广泛的性少数群体及其相关诉求的承认。这时自然而然的问题便是:性少数的边界究竟能拓展到什么程度?是否任何对非正统的性模式的偏好与追求,都应当获得同等的承认?倘非如此,谁才是相关诉求应当受到承认的性少数群体?什么是判定承认与否的标准?换句话说,凭什么不能把具有多偶、乱伦、恋兽、恋童、恋尸等性癖好的人也纳入“性少数”的范畴,承认其癖好的正当性,并保护其满足相应癖好的权利?
本文结论部分将回头处理“性少数”的界定问题。在此之前,我们先以同性婚姻合法化为例,考察如何驳斥反同人士对其道德滑坡论式的质疑。具体而言,同性恋权益的支持者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着手。正面的办法是:论证同性婚姻和所有在道德上不可接受的性模式之间存在均关键区别,从而直接拒斥类比、阻断滑坡。反面的办法是:将举证责任转移到反同人士头上,首先要求其给出上述前提中的类比所依赖的原则,而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通过构建相反方向的滑坡,论证这些原则将使反同人士自身陷入道德困境。
二 异性恋规范
先说反面论证。把同性婚姻(甚至同性恋本身)与人兽交、尸交、恋童、多偶制、乱伦等性模式相类比,其合理性并非不证自明——毕竟所有这些用以类比的性模式,都既可以发生在同性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异性之间。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说“如果异性婚姻(或异性恋)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其他一些性模式(比如人兽交、尸交、恋童、多偶制、乱伦等等),在道德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呢?(
Corvino,2005: 510
)
反同人士要想陷同性恋于道德困境,就必须给出一般性的道德原则,来为“男女结合、一夫一妻”的异性恋规范(
heteronormativity
)奠基,将符合这一规范的性模式,与包括同性婚姻在内的其他“非正统的”或在他们眼中“不正常的”性模式区分开来。大体而言,反同人士能够给出的原则无非四种:一是神意(或宗教戒律);二是传统(或主流文化);三是自然(或目的论);四是伤害(或后果论)。
§2.1 神意
将同性恋视为对神祇旨意或律法的违背,这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各大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派别中是常见的论调。但用“男女结合、一夫一妻是神的安排”之类宗教说辞来反同,至少会面临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来这对绝大部分教外人士毫无吸引力,自说自话不利于促成有效的公共讨论,与政治生活中基于“公共理性”(
public reason
)进行争论与说服的道德理念相冲突(
Rawls, 1997
)。第二,倘若无视教外人士的意愿,强行根据特定宗教或特定教派的教义来制定公共政策,将直接动摇现代国家普遍接受的政教分离原则。
就算基于宗教立场的反同人士对公共理性与政教分离原则均弃如敝屣,他们也仍然要面对第三重难题:如何证明自己确实获知了,或者正确理解了上帝(真主或其他相关神祇)关于婚姻问题的旨意呢?要知道,任何宗教的教义(包括对经文的解读与阐释)在历史上都是不断演变和分化的,并且当代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宗教内部的各个派别在同性恋问题上也远远不是铁板一块,凭什么认为反同人士的宗教主张就代表了对神意的正确解读呢?
最后第四点,任何用神意来为特定道德主张或政治主张辩护的企图,都难以逃脱“尤叙弗伦悖论”(
Euthyphrodilemma
)式的诘问:一件事情的好坏对错是出于上帝的规定吗?还是说,上帝对某件事情是好是坏是对是错的规定,乃是出于这件事情本身的好坏对错?事实上,对所有关涉道德或政治的争论(包括前述各个宗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对特定教条存废的争论)加以剖析便可发现,诉诸“神意”并不能为这些争论在规范层面上提供任何有效的信息或额外的理由,不过是迷惑听众的修辞手段而已。
§2.2 传统
反同人士有时会采取理论上的保守主义立场,将是否符合传统或主流文化,作为判断某类性关系在道德上是否可接受的标准。但无论“传统”还是“主流”,都远比保守主义者所想象的更为复杂多变,难以从中提取一以贯之的、且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原则。譬如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多妾制在诸多文明传统中均长期而广泛地存在;基督教历史上长期禁止夫妻之间进行非阴道的性交,或者采取任何避孕手段;美国各州从殖民地时代就立法禁止跨种族婚姻,直到
1967
年才由最高法院裁定违宪;等等。倘若仅以“传统”或者特定时段的“主流”为标准,保守主义者必将陷入极大的道德困境。
更重要的是,同性恋权益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在拷问“传统”与“主流”性观念的道德合理性;而同性婚姻的观念接受与合法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传统”与“主流”的转变过程。换言之,若以这种性模式不符合传统或主流文化,作为判定其在道德上不可接受的依据,其实是犯了循环论证的谬误。
当然,保守主义者可以坚持说,传统是数千年人类文明的沉淀,我们有理由对其保持敬畏,在试图改变传统时三思而后行,等等。但这些充其量只是“缺省态的理由”(
prima facie
reason
),即在双方均未给出充分论证的状态下保持现状不变,却并不构成任何“阶段性的理由”(
pro tanto
reason
),即对某一方的论证提供实质性的支持(
Hurley, 1989:130-135
);只能用以要求主张变革者给出尽可能充分的论证,或在行动时尽可能地慎重,却无法用以判断主张变革者的论证是否足够充分、行动是否足够慎重。要做出这些判断,最终还得回到议题本身涉及的道德原则上来。作为一种道德或政治理论,保守主义有着天然的内在缺陷。
§2.3 自然
“自然”一词存在多种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异性婚姻恰恰是“不自然”的,因为婚姻制度本身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而“文明”常被视作“自然”的反面;相反,同性恋倒是“自然”的,因为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在动物中广泛存在(
Bailey &Zuk, 2009
),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性取向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受先天因素影响甚至决定的,无法通过后天手段“矫正”(
American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9
;
Sanders
et al
., 2015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性取向本身的道德正当性并不一定依赖于其到底是先天决定还是后天养成,而且性取向“生理决定论”本身的伦理性也存在争议(
Schüklenk
et al.
, 1997
),只不过从大众心理学的层面,“性取向不能后天改变”这种说法总体上更有利于主流社会对同性恋的宽容与接纳(
Horn, 2013:245-246
)。
不论如何,对反同人士而言,婚姻的“非自然性”与同性恋的“自然性”意味着,倘要以“符合自然与否”作为判断标准,视异性婚姻为“自然”、同性婚姻(以及人兽交、尸交、乱伦等用以滑坡类比的性模式)为“不自然”,就必须对“自然”给出特别的定义。
一种办法是诉诸“自然观感”。一些反同人士声称,大多数人天然地对异性恋感到愉悦或者情绪稳定,而一想到同性恋、人兽交、尸交、乱伦等就觉得恶心,说明前者是自然的、道德上可接受的,后者是不自然的、道德上不可接受的。显然,这一论证首先需要解释,凭什么大多数人的自然观感可以被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准。即便不考虑这一棘手的道德哲学问题,反同人士的这个论断在事实层面上也站不住脚。近
10
年来美国公众对同性婚姻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中国网民中“基”、“腐”等词汇最初的贬义逐渐得到消解,都说明无论性取向本身在多大程度上由先天决定,多数人对同性恋的观感都并非乍看上去那么“自然”,而是主流文化建构的结果。
因此现今在反同人士中更为流行的办法是,从目的论的角度解释“自然”:性交的“自然目的”或者说“自然理性”就是繁衍后代,所以但凡有利于繁衍后代的性关系都是自然的、道德上可接受的,而不利于繁衍后代的性关系,包括容易导致后代基因缺陷的乱伦,以及“并不能导向生育”的同性恋、人兽交等,则是不自然的、道德上不可接受的;有学者由此宣称,同性恋者无法“按照实践合理性的要求做出选择”,因为就连“他们性交的方式也是违反理性的”(郑玉双,
2013
:
63
)。
类似地,根据这派人士的理论,婚姻的“自然目的”是实现“一种永恒的、排他的、经由共同生儿育女而自然地(内在地)实现的相互承诺”(
Girgis,George & Anderson, 2010: 246
),所以能够“共同生儿育女”的异性婚姻是自然的、道德上可接受的,而做不到这一点的婚姻形式,比如同性婚姻、人兽婚、童婚等,则是不自然的、道德上不可接受的。不但如此,他们还断言,由于同性伴侣无法拥有共同的生理后代,他们缺乏“异性婚姻通过生育所建立的家庭对善的追求”,因此“同性之间的感情要比异性婚姻者的感情脆弱很多”(郑玉双,
2013
:
63
)。
“同性伴侣之间感情更脆弱”的断言,已被相关研究证伪(
Rosenfeld, 2014
)。与此同时,对反同人士而言更加麻烦的是,根据他们提出的这种“自然目的论”,不但同性恋、人兽交、乱伦这些性行为是不自然的、道德上不可接受的,而且手淫、口交、肛交、戴避孕套的性交,由于同样不利于繁衍后代,因此也是不自然的、道德上不可接受的(当然确实有虔诚的宗教信徒这么认为);类似地,不但同性之间、人兽之间以及与未成年人的婚姻是不自然的、道德上不可接受的,就算在异性之间,缺乏生育意愿(比如丁克家庭)或生育能力的婚姻也是不自然的、道德上不可接受的。
在美国最高法院
2013
年同性婚姻案“合众国诉温莎”(
United States v. Windsor
)的庭辩中,卡根大法官就曾向代表反同人士的律师提出过这样的诘问:倘若如你们所言,婚姻的目的是繁衍共同的生理后代,并且我们可以因此立法禁止同性婚姻,那么我们是不是同样可以因此立法禁止
55
岁以上已经绝经的女性结婚?而反同一方则从未对此类诘问给出稍微靠谱的正面回应。
§2.4 伤害
除此之外,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人士还常常声称,与在异性婚姻家庭成长的儿童相比,在同性婚姻家庭成长的儿童会遭到更多的身心伤害。然而他们所援引的“研究”,要么在方法论上存在重大缺陷,要么干脆是基督教保守组织资助的伪科学。事实上,时至今日,科学界早已达成共识,同性婚姻家庭背景对儿童的身心发展没有任何负面影响,真正起作用的因素是社会经济条件与家庭关系的稳定性(
Manning,Fettro & Lamidi, 2014
);而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由于令同性伴侣关系得以见光并受到保护,因此恰恰有益于这些家庭中儿童的身心健康。
另外一种诉诸伤害的方式,是宣称同性婚姻合法化将导致社会总体生育率降低,长远而言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存续与政治经济运作,从而间接伤害社会中的个体。这种论调的质量比前述“婚姻自然目的”论更为糟糕:并非所有异性婚姻都具有高生育率;反之,同性伴侣即便无法拥有共同的生理后代,也完全可以拥有各自的生理后代;再者,禁止同性婚姻并不会增加同性恋的生育意愿。更何况,为了提高生育率而剥夺特定人群的婚姻权,从道德正当性的角度说,本身就是舍本逐末。
§
2.5
小结
综上,一旦将举证责任转移到反同人士头上,要求他们对其滑坡论证的前提给出类比的原则,后者便将陷入重重困难之中,要么诉诸只被圈内人接受(甚至可能连圈内人都有争议)的神学理论,要么依赖对传统、主流文化、自然观感、发展心理学等事实材料的简化与扭曲,要么因为刻舟求剑地以复杂多变的传统或主流文化作为标准,或者因为采取对性交与婚姻目的的狭隘理解,而陷入相反方向的滑坡:倘若拒绝承认同性婚姻(或同性恋)的道德合理性,便不得不同时拒绝接受许多即便在“异性恋规范”的道德框架中也完全合理的性模式。
当然,以上并不构成对反同人士道德滑坡论的决定性反驳。如前所述,反同人士可以援引保守主义有关传统的“缺省态的理由”,要求在同性婚姻支持者尚未给出充分论证的情况下维持一夫一妻的法律“现状”不变,即便反同人士本身同样没有给出充分论证。因此,同性婚姻支持者还需要从正面立论,证成同性婚姻与所有在道德上不可接受的性模式之间均存在关键区别,从而拒斥对方构造的类比与滑坡。
三 同意与道德能动性
那么,同性婚姻的支持者该如何正面驳斥道德滑坡论呢?一个很容易想到的论点是,性关系及婚姻关系在道德上可被接受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其必须以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或者说符合“同意”(
consent
)原则。这一原则在当代已被广泛接受,比如《世界人权宣言》第
16
条便宣称:“只有经当事配偶各方的自由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缔婚”(
Marriageshall be entered into only with the free and full consent of the intendingspouses
)。
(注意此处我依据宣言的官方英文版本重译,与官方中文版本措辞不同。后者此条作“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由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缔婚”,其中“男女”一词预先排斥了同性婚姻,“双方”一词预先排斥了多偶制婚姻。相反,英文版中的“当事配偶各方”措辞更为中立。既然本文讨论的正是同性婚姻、多偶制婚姻等非传统模式的道德性问题,此处自以遵从更中立的表述为上,以便进一步讨论。——但这并不是说《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们本身就支持同性婚姻。相反,如上节所述,起草者是否接受“传统”的或在当时占“主流”的婚恋观,对同性婚姻的道德性本身并不造成任何影响;而且此处引用《世界人权宣言》与否,对本文的论证也并无实质影响。此外,诸如《公民权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3条、《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0条等涉及婚姻定义的条款,均存在类似的版本表述差异问题,恕不赘述。)
§3.1 道德能动者与道德容受者
不过“自由和完全的同意”这一概念究竟何谓,并非一目了然。不少反同人士正是出于对此概念的误解,而抓住这点大做文章。譬如时评人李铁在《同性婚姻,绝非李银河说的那样简单》一文中连续质问:“如果仅仅是当事人自愿便可结婚,那么,父女、兄妹、母子自愿结婚可不可以?三个人结婚可不可以?三男两女呢?人和动物结婚呢?人和板凳结婚呢?”(李铁,
2010
)
李铁所举的这一连串例子,可以分为两类。在血亲婚姻(“父女、兄妹、母子自愿结婚”)与多偶制婚姻(“三个人结婚”与“三男两女”)中,当事配偶各方均为人类,后文将另行讨论。至于“人和动物结婚”、“人和板凳结婚”,情况则截然相反,在此李铁的质问显而易见是荒谬的。
我们只消反问:作为婚姻的“当事配偶”,动物或板凳如何能够对该婚姻表达“自愿”,表达“自由和完全的同意”?需知“同意”概念首先蕴含“道德能动者”(
moral agents
,或曰道德主体)概念,只有那些具备在决策过程中应用道德原则的抽象概念能力,从而能够且应当对其决策后果负责的行为主体,才有所谓“同意”可言。在童话、寓言等虚构世界之外,我们一般不把非人类的动物(以及死人的遗体)视为道德主体,遑论板凳之类非生命体。显然,人兽婚、冥婚、以及人与物品的婚姻,既然要将动物、尸体、物品也视为“当事配偶”之一,便根本无从满足当事配偶各方均能“自由和完全地同意”的原则,自然更不能与同性婚姻相类比。
有人可能会注意到此处婚姻关系与纯粹的性关系的不同。诚然,人不能与物品结婚,但大概不会有多少人认为:人同样不能与物品发生性行为,尽管物品无法“同意”与人发生性关系(当然,和板凳性交,听起来似乎不大有可操作性,不妨换成充气娃娃)。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类似地得出:诚然,人兽婚(或者冥婚)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但人兽交(或者奸尸)在道德上却是可以接受的,尽管非人类的动物(或者死人的遗体)同样无法“同意”与人发生性行为。
与充气娃娃一样,动物和死者并不足以被视为“道德能动者”。但与充气娃娃不同的是,后者仍可被视为“道德容受者”(
moralpatients
,或曰道德受体)(
Regan, 1983: 152
),亦即尽管缺乏道德责任的能力、无法表达同意,却可能遭受(道德意义上的)伤害。比如动物作为“有感知力的存在”(
sentientbeings
),能够体验不同层次的生理或心理痛苦;而死者虽然已经无法再体验到一般意义上的身心痛苦,但仍然可能在社会建构层面享有尊严权或其他权益(也有人认为,死者本身并不享有尊严权或其他权益,但对其尊严的损害会间接伤害到其仍在世的近亲或其他相关人士的权益)(
Smolensky,2009
)。
充气娃娃根本不是道德容受者,自然也不必被视为性行为的当事方,而只是纯粹的性玩具(注意与相应婚姻关系的区别:倘要赋予充气娃娃“配偶”的法律地位,就必须承认其为婚姻关系的当事方)。相反,作为道德容受者,动物与死者仍可被视为人类对其性行为的当事方,成为道德关切与保护的对象。其无法对人类与其发生性行为的意愿表达“自由与完全的同意”这一事实,也因此必须得到严肃对待。
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必须给予动物与人类同等程度的保护。比如可能会有人坚持说:“尽管动物没法表达同意,但只要性交过程不构成对动物的虐待,那么人兽交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就像宰杀牲畜、动物临床试验都是可以接受的一样。”无论这种说法成立与否,它涉及的是人兽交这种行为本身的道德性质,已经不再构成对同性性关系或同性婚姻的道德挑战(如前所述,同性恋权益的支持者一般以符合“同意”原则为必要条件之一,而人兽交并不满足这一条件),故与本文主旨无关。
§3.2 同性恋与恋童
根据“同意”原则,同性婚姻(或同性性关系)与人兽婚(或人兽交)等性模式之间无法建立滑坡类比,那么与童婚(或成人和儿童性交)之间如何?
反同人士经常宣称,“同意”原则无法区分同性之间自愿的性关系与成人儿童之间自愿的性关系。比如李铁就在其文章中绘声绘色地描述道:“早在
1972
年,美国两百多个同性恋组织的共同纲领便是要求废除性行为的所有年龄和人数的限制。其中有一个‘北美男人男孩恋协会’(
NAMBLA
),正在有组织地争取恋童合法化。对他们来说,多元性爱美不胜收,只要自愿,只要注意卫生,不弄伤儿童,小朋友们开心,性行为就和一起玩过家家游戏一样,有何不可呢?”(李铁,
2010
)
在进入理论探讨前,首先需要指出,李铁的上述描述对不了解美国性少数运动史的读者具有相当的误导性,使其以为恋童合法化是美国同性恋群体的主流主张。实则恰恰相反(李铁文中误导读者、污名化同性恋群体处比比皆是,因无关本文主题,恕不一一辨析)。
1972
年
2
月,“全国同性恋组织联盟大会”(
National Coalitionof Gay Organizations Convention
)在芝加哥召开,会上通过了《
1972
年同志权利纲领》(
1972 GayRights Platform
),共提出
17
条主张,其中一条是废除性行为的年龄限制。
这份纲领的意义,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大,因为这次会议是美国同性恋群体第一次未受反同人士骚扰中断,成功完成全部议程的全国性会议(从而得以第一次提出一份共同纲领),值得载入历史。说小,因为这次会议是
1969
年“石墙骚乱”(
Stonewallriots
)后同性恋群体分裂的产物,对当时以及后来的同性恋权益运动均未产生太大的影响。会议组织者向全国
495
个同性恋组织发送了邀请函,但只有
85
个组织约
200
名代表与会(李铁误将与会代表的人数和“两百多个同性恋组织”混为一谈);纲领中有关废除年龄与人数限制的条款,也因得不到未与会人士的支持,而在会后递交给政界人士的过程中被删落(
Humphreys,1972: 162-168
)。
即便是对纲领中废除性行为年龄限制的条款表示支持的与会代表,多数人也并非出于恋童合法化的考虑。当时美国各州,除某些直接立法禁止同性恋外,其余往往通过对同性恋与异性恋设置不同的法定同意年龄,从而实现对同性恋的歧视。比如马萨诸塞州规定,
13
岁即可“同意”与异性发生性关系,但要到
18
岁才能“同意”与同性发生性关系。各州这类歧视性的法律直到
2003
年,才在“劳伦斯诉德克萨斯”(
Lawrence v.Texas
)一案中,被最高法院判决违宪。在六七十年代的激进气氛中,很自然地有人认为,只有完全废除年龄限制,才能防止这类歧视性法律的出现。
另一些人则是出于对某些州过分苛刻的年龄限制的抵触。比如纽约州的法定同意年龄为
17
岁,倘若两名
16
岁的少年相互发生性关系,则两人都将被定罪。这次会议的发起者是纽约州的“同性恋行动人士联盟”(
Gay ActivistsAlliance
),其成员以大学生为主,对法定同意年龄问题自然格外敏感。之后随着“法定同意年龄分级制”(
graduated ageof consent
)概念的提出(见下文),彻底废除年龄限制的激进主张失去了用武之地,“同性恋行动人士联盟”也最终于
1981
年解散。
考虑到美国同性恋权益运动的发展史,很难说
1972
年纲领中废除性行为年龄限制的激进条款能够代表同性恋群体的主流态度。倘若非要说美国同性恋组织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共同纲领”的话,
1993
年华盛顿同志权利大游行的纲领(
Platform ofthe 1993 March on Washington for Lesbian, Gay, and Bi Equal Rights andLiberation
)恐怕比
1972
年纲领有资格得多,毕竟这次游行约有
100
万人参加。在这份纲领中,涉及年龄处共两条,一条支持自愿同意的成年人之间非强制的性行为,另一条呼吁通过并实施法定同意年龄分级制。
至于李铁提到的“北美男人男孩恋协会”,成立于
1978
年,从
80
年代开始一直受到美国其他同性恋组织的集体孤立,
1994
年时更被“国际同志协会”(
InternationalLesbian and Gay Association
)除名。此后该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据警方卧底调查显示,全国范围内成员不到千人,是一个毫无影响力的边缘团体。
§3.3 同意与年龄
澄清事实并不足以打消反同人士的疑虑。相反,不少反同人士坚持认为,目前多数同性恋组织之所以反对恋童,纯粹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步步为营,一旦完成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任务,就要图穷匕见,暴露出争取恋童合法化的真面目来。因此同性婚姻的支持者仍然需要从理论上说明,同性婚姻合法化与恋童合法化在道德性质上存在关键区别。
这里需要澄清一下“恋童合法化”一词可能存在的歧义。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0
年的《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第十版》(
ICD-10
),“恋童”(
paedophilia
或
pedophilia
)被定义为“对儿童的性偏好”。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认为这种性偏好的存在本身应当被定罪(尽管有人可能觉得这种性偏好本身就令人反感)。相反,所谓“恋童合法化”指的是把落实和满足这种性偏好的行为合法化。此外,落实和满足对儿童的性偏好也存在多种方式,从在虚拟世界中消费儿童色情产品,到在现实世界中对特定儿童实施性行为,不同方式在道德上的可接受度并不一致。比如有人就曾主张(
Luck, 1999
),既然虚拟世界中的杀人游戏合法,那么虚拟世界中的儿童色情产品也应当合法化。
但是在反同人士的道德滑坡论中,与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以及婚姻关系构成对比的,是现实世界中成人与儿童之间的性行为(“童交”)以及婚姻关系(“童婚”),而非虚拟世界中对儿童色情产品的消费;因此这里讨论的“恋童合法化”,也是特指对(道德可接受度最低的)童交与童婚的合法化。
前面提到,至少在人与人之间,性行为与婚姻关系在道德上可被接受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当事人“自由和完全的同意”。恋童癖(以及试图以此进行滑坡攻击的反同人士)会辩称,未成年人完全可以“自愿地”、“自由和完全地同意”与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或者缔结婚姻。
然而这是对“同意”原则的误解。如前所述,这一原则中的“同意”(
consent
)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赞成”(
agreement
),而是一个特殊的道德概念,蕴含着对“道德能动者”资格的认定。只有能够被合理地认为心智已臻成熟、具有民事行为与责任能力的个体,才有所谓“同意”可言。在其心智成熟之前,儿童尽管仍然应当被视为道德容受者,却并不足以被视为道德能动者。正如儿童需要有法定监护人、没有投票权、不能签署医院的知情同意书一样,他们同样不能“自愿地”与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或者缔结婚姻。
一些论者反对以上“儿童完全不具备同意能力”的说法,即便他们依旧承认儿童不具备“同意发生性行为的能力”。比如
Ole MartinMoen
在其关于恋童的论文中举例说:“假如我问我十岁的儿子要不要一起去打篮球,他说要,于是我们一起去打篮球——这中间并没有任何错处。同样情况还有一起去滑雪、看儿童电影或者烤蛋糕等。另一方面,有些事情是儿童没办法同意的。如果我建议我儿子和我一起玩枪、醉酒、做爱,不管他同意与否,听从这些建议都不应当被允许”(
Moen, 2015:116-117
)。在
Moen
看来,这种区别的原因在于有些事情会对自己造成伤害(或对自己造成伤害的风险很高),另一些事情是对自己无害的(或低风险的),而“成人拥有(在一定限度内)同意会对自己造成伤害的事情的特权,但儿童并没有相同的特权,或者并没有相同程度的特权”(
Moen, 2015:117
)。
然而只要我们将民事责任及道德责任层面的“同意”,与普通意义上的“赞成”相区分,便可发现
Moen
的前一类例子涉及的只是儿童的“赞成”而非“同意”——事实上,所有这些建议都是由作为监护人的父亲提出的,倘若在这些低风险的活动中发生意外,负责的同样应当是父亲而非儿子。我们并不会认为,由于这些活动是低风险的,所以儿子有能力“同意”(而非“赞成”)参加此类活动,以至于一旦发生意外时,责任人将是儿子而非父亲。
当然,即便按照
Moen
的理论,儿童仍然无法“同意”发生性行为,因为后者对儿童造成伤害的风险很高(
Moen, 2015:113-116
);但“同意”与“赞成”的区分能够更融贯、更自足地解释为何儿童无法“同意”发生性行为。无论如何,根据“同意”原则,同性性行为与同性婚姻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而成人与儿童之间的性行为或婚姻关系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
两点题外话。首先,个体发育存在差异,有人心智成熟得早,有人成熟得晚。但从法治的角度说,法律规则的内容必须“一般、明晰、众所周知”(
Waldron,1989: 84
),不可能也不应当将对少年儿童心智成熟度的判断交给具体案例中的当事人或司法者,而是必须“建构”出一套明确的、一般适用的关于法定同意年龄的规则。
其次,心智成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或者应当对“同意”能力进行相应的差别建构?比如我们可以依据前述的“法定同意年龄分级制”概念制定如下的法律(这里的具体年龄只是举例,在实践中可以进一步论证和调整):任何人均不得与
13
岁及以下的儿童发生性关系;任何
18
岁及以上的成人之间均可以在“自由和完全的同意”基础上发生性关系;任何人若要与比自己年幼且年龄在
14-15
岁之间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必须获得对方“自由和完全的同意”且与对方年龄差不得超过
1
岁;任何人若要与比自己年幼且年龄在
16-17
岁之间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必须获得对方“自由和完全的同意”且与对方年龄差不得超过
2
岁。换言之,一名未成年人也许无法“同意”与成年人发生自愿的、非强制的性关系,但只要达到一定年龄,不再视为“儿童”后,便可以“同意”与另一名年龄相近的未成年人发生自愿的、非强制的性关系。至于这种观点与传统一刀切的法定同意年龄孰优孰劣,就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四 权力结构背景下的平等与自由
如本文一开始所说,反同人士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滑坡式质疑包含两个前提:大前提建立其与同性恋权益支持者并未全力辩护的其他某种“非正统”性模式
S
之间道德性质的等同,小前提则从道德上拒绝
S
;两者结合,得到对同性婚姻的道德否定。当
S
是人兽婚、尸交、恋童等性模式时,只要根据“同意”原则,即可在肯定小前提的同时否定大前提,推翻滑坡类比。
但如果
S
是多偶制或乱伦时,情况就比较复杂。在多偶制或乱伦关系中,当事人均可以是能够担负完全民事责任的道德能动者,从这个角度说确实具有“自由和完全地同意”进入某种自愿的、非胁迫的性或婚姻关系的能力。因此仅从“同意”原则出发,似乎不足以从道德上区分同性之间的性关系,与多偶制或乱伦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同性恋权益的支持者大抵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认为“同意”原则是在道德上衡量性与婚姻关系的唯一必要标准,因此接受滑坡论证的大前提,但同时否定小前提,力证多偶制(
Calhoun, 2005
;
Goldfeder,2017
;
March, 2011
)或乱伦(
Bergelson, 2013
;
March, 2010
)在道德上并非不可接受。这样一来,就算同性婚姻确实会滑坡到多偶制或乱伦,这一事实也无法构成对前者的任何道德攻击。
另一种选择是继续接受小前提,同时否定大前提。这就意味着需要对“同意”原则做出更强版本的解释,或者在“同意”原则之外给出对性与婚姻关系的其他道德约束,这些约束被同性亲密关系满足,但并不被多偶制或乱伦满足。
§4.1 常见论调
在给出最终能够将同性婚姻与多偶制或乱伦相区分的道德原则之前,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某些常见(但并不靠谱)的用以否定多偶制或乱伦的理由。
乱伦合法化为何在道德上不可接受?对此,最常见的论调有(
i1
)“乱伦禁忌深深植根于传统和主流文明之中”,以及(
i2
)“乱伦行为天然地令多数人反感厌憎”。比如著名政治理论家
George Kateb
就曾说过,尽管“一个权利至上的社会完全给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论证”来支持对成人之间自愿乱伦的禁令,但是由于“我们受规训所理解的(无论是民主的还是不民主的)文明要求我们持续谴责并禁止这些行为”,因此出于对“文明价值”(
civilizationvalues
)的保护,我们就必须对其持续地加以谴责和禁止(
Kateb, 1992: 13-14
)。
就道德论证而言,
Kateb
的表态近乎自暴自弃。何况,本文前面关于传统、主流文化、天然观感的讨论,在适用于同性婚姻的同时,也一样适用于乱伦:要么传统、主流、观感等不足以作为拒绝成人自愿乱伦合法化的有效理由,要么就必须以此为据一并拒绝乱伦与同性婚姻二者的合法化。显然,这种区分策略对同性婚姻支持者完全不可行。
还有一些人试图从乱伦对个人与社会可能造成的实际伤害角度对其加以否定,比如:(
i3
)“乱伦产下的后代易存在基因缺陷”;(
i4
)“真实案例中,乱伦往往是强制性的,尤其是男性长辈强制女性晚辈发生非她自愿的性关系”;(
i5
)“乱伦导致辈份错杂,社会关系混乱”;(
i6
)“允许血亲之间通婚将为某些人钻法律空子大开方便之门,比如通过与父母结婚来逃避遗产税”,等等。
在上述理由中,(
i3
)实际上意味着承认,乱伦行为本身并不存在道德问题,关键是要做好避孕措施;就算乱伦双方想要后代,也只需等待科技发达到足以检测甚至修正胎儿可能的基因缺陷即可。而(
i5
)与(
i6
)则更加牵强,
82
岁老翁迎娶没有近亲关系的
28
岁女青年同样会造成(
i5
)所述后果,然而我们并不因此禁止双方年龄差距较大的婚姻;至于(
i6
),只需稍稍修改法律条款即可防范。
其中唯有(
i4
)所言尚可一议,但需要做出较大的修正。仅仅由某些乱伦案例违背了“自由和完全的同意”原则这一点,并不足以推出“乱伦”这种行为本身在道德上不可接受,或将其他所有那些自愿的乱伦关系一并禁止(就像不能仅仅由某个社会中强奸案频发这一点推出该社会应该完全禁止任何性行为一样)。要否定乱伦行为本身的道德性,必须在“同意”原则的基础上,将“家庭”关系蕴含的“权力结构”一并纳入考量,详见后文。
此外,近年还有一种试图区分同性恋与乱伦的做法是,宣称(
i7
)“不同于同性恋,乱伦行为并非受先天因素决定的生理必需”。
上文提到,如今确实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性取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天因素(
American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9; Sanders
etal
., 2015
),而且“性取向无法后天改变”这种看法总体上也确实更有利于主流社会对非异性恋的接纳(
Horn, 2013:245-246
)。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性恋在道德上的可接受性本身必须以性取向的先天决定论为前提:一方面,不少同性恋权益支持者争辩说,正是由于不同性取向在道德上并无高下之分,所以即便其来自后天养成或者可以随意选择,个人对自身性取向的自主权仍然应当受到尊重;另一方面,在坚定的反同人士眼中,即便性取向由先天因素决定,也只不过意味着人类应该尽早发展出筛查胎儿“同性恋基因”的技术,以便父母采取堕胎或基因改造手段防止自己的孩子“误入歧途”。
乱伦的道德性质与此同理:即便(
i7
)的说法成立,充其量也只意味着主流社会接受乱伦的难度大于接受同性恋,却并不代表乱伦在道德上一定不可接受,或者一定比同性恋更加不可接受。
以下简单列出若干反对多偶制的常见理由,及其问题所在:
(
p1
)“多偶制与现代文明的主流背道而驰。”问题同(
i1
)。当然,现代文明之所以(在异性恋婚姻上)坚持一夫一妻制,是有切实的道德基础的,特别是平等方面的考虑,详见后文。
(
p2
)由于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多妾)制在诸多文明中均长期存在,因此相比于针对乱伦的(
i1
)、(
i2
),基于“传统”或“自然观感”对多偶制的反对更难立足。若有人出于这两者反对多偶制,则他们实际上抵触的,只有婚姻中出现多名男性配偶(一妻多夫制或多妻多夫制)的情况。此外,这种抵触或许正体现出,男性对既有的、由自身占据优势的性别权力结构遭到削弱甚至打破这一前景的焦虑。
(
p3
)“多偶制易导致儿女对家长的身份认知紊乱等问题,对儿童成长有负面影响。”与上一点类似,鉴于多名女性配偶的婚姻在历史上长期广泛存在,即便在当代也不罕见(比如一些伊斯兰国家),而相关经验研究并无证据显示这类婚姻本身会对儿童造成伤害(
Goldfeder,2017: 73-96
),因此这个反对理由很可能同样是男性权力焦虑的产物。
(
p4
)“允许多偶制将为某些人钻法律空子大开方便之门,比如通过群婚方式集体享受政府颁发给家庭的福利补助。”问题同(
i6
)。
(
p5
)“不同于同性恋,多偶制并非受先天因素决定的生理必须。”问题同(
i7
)。
(
p6
)“真正的爱情是排他的,多偶制与爱情本质相矛盾。”但爱情的排他性并非无可争议的事实,比如哲学家
CarrieJenkins
(2017)
就力主“多边恋”(
polyamory
)的存在;另一方面,即便“真正的”爱情确实具有排他性,这也顶多意味着多偶制婚姻并非真爱的结晶,却并不能说明多偶制婚姻本身在道德上不可接受——毕竟现实中与爱情无关的婚姻比比皆是,而我们并不因此声称这些婚姻是不道德的,甚至主张立法禁止没有爱情的婚姻。
§4.2 多偶制
如(
p1
)、(
p2
)、(
p3
)所暗示的,相对于历史上长期广泛存在的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多妾)制,现代文明在异性恋婚姻上坚持一夫一妻制原则,其道德合理性来自对性别平等的承诺。很自然地有人会问:“多偶制”(
polygamy
)并不等于“一夫多妻制”(
polygyny
),后者从法律上规定了性别之间的不平等,而前者本身并不对男女任一性别的配偶人数做出限制,两性在其中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倘若仅以符合“性别平等”原则(外加符合“同意”原则)为必要条件,难道我们不是应当在道德上接受多偶制,并推动其合法化?
正因如此,以
John Corvino
(2005)
为代表的一些同性婚姻支持者认为,多偶制本身在道德上确实是可以接受的,所有对多偶制的批评都有意无意地将其与(在道德上不可接受的)一夫多妻制相混淆;既然如此,反同人士在多偶制与同性婚姻之间搭建的道德滑坡,也就对同性婚姻失去了杀伤力。换句话说,
Corvino
否定的是道德滑坡论的小前提。
但这并非同性婚姻支持者唯一可行的策略。正如
Corvino
也承认的,在现实人类社会中,多偶制合法化最有可能导致的实践后果是,绝大多数异性恋多偶婚姻是一夫多妻制,而一妻多夫或多夫多妻则寥寥无几;只是他并不认为这一实践后果对多偶制的道德性质有任何影响,因为性别平等的多偶婚姻仍然是可能的(
Corvino,2005: 527-528
)。问题在于,对“平等”的理解不可能完全脱离“权力结构”(
power structure
)的背景(林垚,
2015
)。多偶制合法化之所以最有可能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