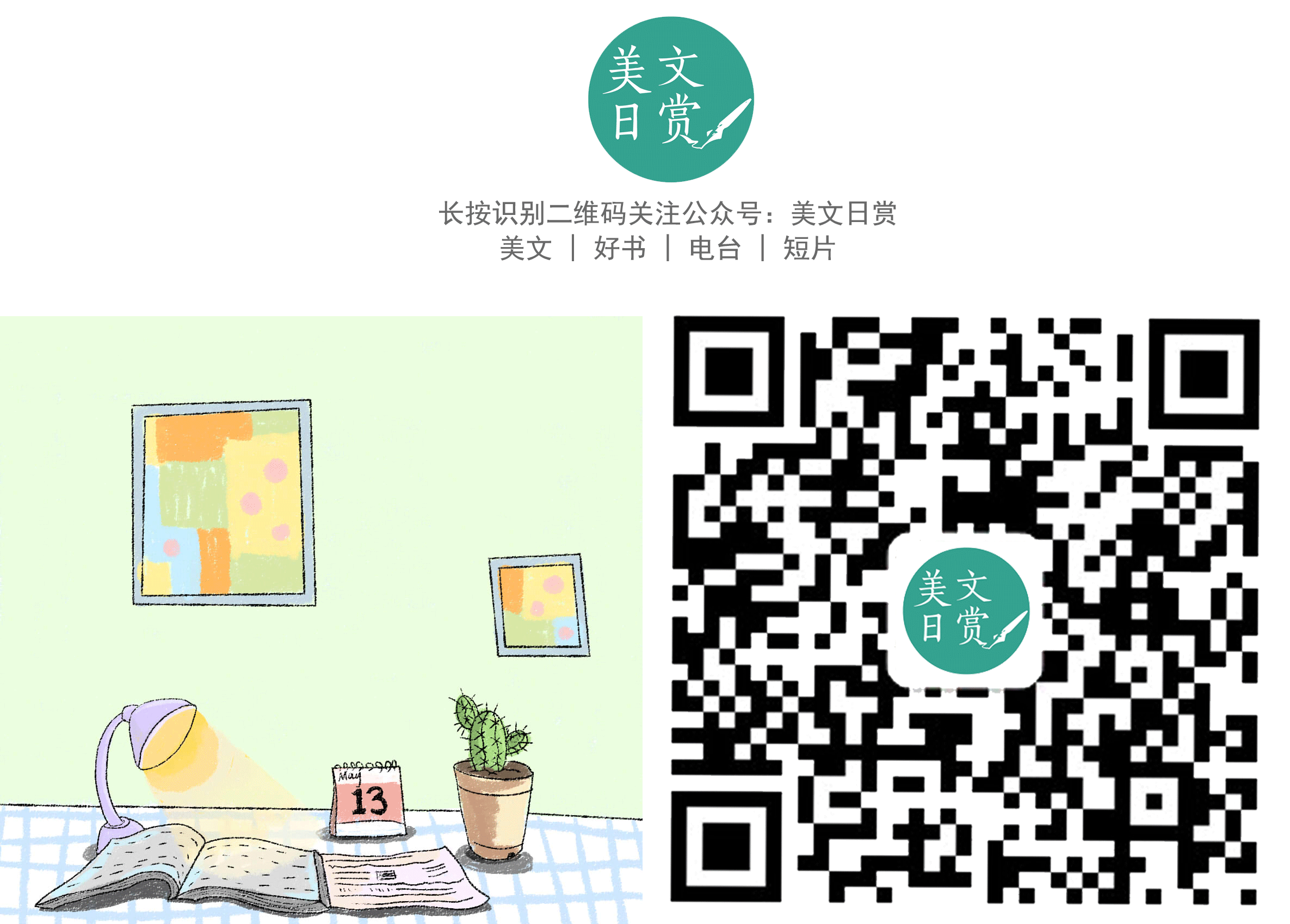在上海见到一个“下了海”的文化人。几个还在岗位上的文化人坐在他经营的饭店里,享受着他提供的精美菜肴,大谈文化的失落。最失落的,竟是老板。他苦着脸,反省自己越陷越深,离原有的文化理想越来越远——金钱,使人腐败。
他的忧郁与自责使我想起大陆媒体上对商品经济所带来的贪婪风气的种种批判。文人从商,以“下海”称之,就像从前人说良家妇女“下海”伴酒一样,是斯文扫地,是自甘堕落。
我向来理解权力使人腐败,却觉金钱是一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一个人有了钱,就可以放手去求取知识,可以在国内外游走,可以使家人丰衣足食。因为他有钱,可以不斤斤计较,可以不钻营奉承,可以不小头锐面。资源的充裕,使他比较容易成为一个教养良好、宽容大度、体恤弱者的人。当行有余力时,他可能在乡间铺桥修路、救济贫苦;当飞黄腾达时,他可能在社会上成立各种基金——帮肤基金用于帮助照顾残疾人,文化基金鼓励艺术创作;他也可能在学校里设置奖学金,策励学子,为国育才。
一个国家有了钱,它就比较容易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老人福利、失业救济、幼儿培育、残障孤儿的照顾,都需要金钱的促成。有了财富的基础,一个社会才比较容易达到“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境界。
现在对经济狂潮大加鞭挞的忧国之士不妨看看欧洲的发展历程。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是一个环境优美、人文素养高的地方。公园池塘里的天鹅悠游自在,无人打扰;路边野生的红艳苹果自开自落,无人撷取;搭地铁、公交车进进出出全凭个人自觉购票,无须检查;生了病去看医生,只要留下地址就可以得到治疗,账单会被寄到您家中。作家张贤亮和朋友在欧洲餐馆吃饭,忘了付钱。走出餐馆了,侍者才追来提醒,态度婉转客气,毫无猜疑的神情。
这样的雍容大度,不是天生的民族性,而是经济的塑造。如果张贤亮在20世纪50年代来到战后民生凋敝的欧洲,侍者对忘了付账的客人可是要怒目相对的。战后的德国,小孩在大街上抢美国大兵从吉普车上丢撒下来的巧克力糖,满脸胡须的潦倒男人在马路上弯身捡拾烟蒂,年轻的女人千方百计接近英美大兵以换取丝袜和口红。
马歇尔计划实施之后,德国经济开始复苏。钱,使人们活跃起来。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第一个狂潮是“吃潮”。人们拼命买吃的东西,谈吃的话题,做吃的计划。文化批评家们在报纸杂志上也拼命批判国人的贪吃丑态,“斯文扫地”。但是评者自评,吃者自吃。“吃潮”稍退,在20世纪50年代初,紧接着涌起“冰箱潮”。那白白方方的一大件,装得下好几天的吃食而且保质不坏,举国为之疯狂。男人女人努力工作、积极向上,不为救国救民,却为了挣够钱去买个大冰箱。文化人或农民工人,聚在一起,不谈灵魂上的事情,却和左邻右舍比较冰箱的品牌。报纸上则充满义正词严的道德指控:精神污染、文化失落、道德沦丧。德国知识分子们沉痛地问,西方文化往哪里去?
四十年之后的德国,是一个连最底层的扫街工人都可以每年出国度假的国家。于是你看见他们的孩子彬彬有礼,他们的公交车司机会等到最后一个乘客安稳落座才再度启动汽车,他们的餐馆侍者,见你没付账走了出去,还对你和颜悦色。他们的国家拨出大笔大笔的钱给饱受战乱的波希尼亚难民,给非洲因饥饿而濒临死亡的儿童,给民生困顿、政局不稳的俄罗斯。他们的大学,对全世界的学生开放。
这种百川不拒的宽容,与民族性格关系少,与有钱没钱关系大。钱,当然不会凭空而来,它必须通过劳心劳力去挣取;如果这个劳心劳力挣取财富的行为叫作“贪”的话,那么“贪”有什么不好?它根本就是经济动力,使一个个人,不倚赖国家的扶养,以自己的力量求温求饱求物质的丰足;没有这个动力,社会经济的发展将是停滞的,停滞在贫穷中。你说金钱使人腐败,我说贫穷使人腐败,匮乏使人堕落。“仓廪实而知礼节”反过来说就是,贫穷使人无法顾及荣辱的分寸,那才是道德的沦丧呢。
在经济狂潮中,我们所看见的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欺诈、钩心斗角,究竟是来自对金钱的追求,还是来自对金钱追求的机会不均等?前者可以是君子之争,后者,却势必释放出一个人对社会最深最痛的怨愤;集合无数个个人的怨愤,那就是一股动荡不安的毁灭力量。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却觉得,在某个发展阶段,不患多而患不均。如果游戏规则是公平的,对财富的追求可以推动社会发展,使它在物质不乏之余往精神文明层面提升;如果游戏规则是不公平的,传统价值的解体崩溃恐怕是无法避免的噩梦。
我多么希望那位“下了海”的文人老板能欢欣鼓舞地经营他的饭店,大赚其钱。然后有一天,他的钱实在太多了,他成立一个建设乡镇图书馆的基金会,使最偏僻的小村子也有自己的图书馆;他设置一个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大奖,鼓励天下有志未成的作家竞技;他组织一个翻译中心,使中文创作被译成各种文字,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读到……钱的好处太多了。有一天,当像他这样的人在中国比比皆是时,说不定,中国还要经援美国和德国呢。
腐败不腐败在于公平不公平,金钱,倒是无辜的吧。
(摘自《读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