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去了一趟柏林,有幸见到两次浩浩荡荡的游行。
不分青年老少的,他们每个人都拉着横幅,喊着口号:「对抗强权,反对压制,拒绝战争。」
今年,我在新闻里看也看到好几次这样,居民白纸黑字联合炸锅抵制的场面。
只是区别在于,后者针对抵制的人群,居然是:
绝症病人、残疾人、老年人….
前几天我又了解到一位26岁患尿毒症女孩,她因为生病辞去高薪工作,诊疗过程非常艰难,她离我们很近,就存在生活职场周遭,使我更觉得这更应该是和大家唠唠的严肃话题。
到底咋回事?又有多热闹?
这恐怕还要从近些年频频发生的:拒绝让血透中心进社区的纠纷开始说起….

耗时又耗钱,一次透很可能终生透,总而言之,透析很难。
前一段认识了一位叫婉婷的女孩,朋友的朋友,地点在我家。
「明天我就去面试啦!」一进门婉婷就欢脱得像只小鸟,第一次见面,她的自来熟把我这个社恐吓到。
细问之下,我才知道婉婷即将去面试的咖啡厅服务员,月薪6000块,在上周,她辞去了自己广告公司的执行创意总监的职位。
早就听说在广告公司上班的人没有生活,婉婷说自己最夸张的时候三天三夜没睡觉,不怎么上厕所,一开始是她工作中最大的优势,驻在线下活动场地,她就是下属眼里的铁娘子。
去年年中的时候尿毒症了,一周要去医院三次做透析,人住在朝阳,公司在家附近,医院在海淀,直线距离15km。
「虽然事出有因,但每次做完回到公司,总觉得愧疚。」
后来婉婷辞职了,钱和命之间,她最终还是做出了选择。
我和婉婷交换了微信,她确定工作搬完家的时候,给我发了咖啡厅的定位:
婉婷的经历或许并不那么艰难,毕竟,工作多年,她还尚有选择。
曾有个江都籍的大学毕业生,查出尿毒症后,因为治疗费用贵,医院距离太远。
无奈之下只能自查资料,买钢管、透明pvc回家,在家隔离出2平方米的空间,自建了无菌透析室。
汉阳的一位单亲妈妈,也在一间5平方米的卧室给女儿做出了「无菌透析室」。
每天睁开眼,她就开始忙碌透析的事,整理床铺、开紫外线等消毒,洗手,热药,给肚子“放水”,再给肚子“灌水”。
 血透,就是病人的一次小便
血透,就是病人的一次小便
透析肾脏病人,比如尿毒症患者的常见的治疗手段。
当患者肾脏暂停生产尿液的工作时,尿液就留在了他们的身体里。
患者透析一次就相当于正常人的一次小便,
主要作用是清洁血液,排除其中的尿酸和有毒物质。
而停止透析的话,会导致大量的水分排泄不出来,造成心力衰竭、肺水肿,
严重的患者存活时间很难超过三个月以上。
一般来说,透析频次为3次,一次4小时,费用800-1500一次不等,在公立医院透析室,总是一床难求,需求非常大。
△透析流程图
需求的背后,是逐年在攀升的肾脏病人。不去了解一些数据,你根本不会知道它有多吓人。
早在14年的时候,ESRD[终末期肾病患者]人数就已经达到了200万人,有专家预计在2030年的将达315万,
这攸关我们每个人。
除了换肾,ESRD患者常见的治疗手段是做血液透析。
根据CNRDS的统计,我国需要血透的患者近年正在大幅度增加,截止到2016年
需要透析的患者就已经达到44.7万。
△在我国,光是登记的就有44.7万患者需要透析
在公立医院血透室,每天大概有400人排在透析室门外,从2017年开始每张床就有几位患者轮流使用,晚上来的患者需要透析到半夜。
再夸张一些的患者,每天早上凌晨3点就起床,在家人的陪护下来医院排队治疗,一些人为了省下返回的交通费,也为了方便,开始举家搬迁到医院附近租房,开始蜗居。
△人满为患的公立医院透析室外。
情况是这么个情况。
公立医院资源不够,患病人数又一直在上升,那么该怎么办呢?
于是,国内便从2011年开始了「独立血透中心」的运营。
正规资质的血透中心,在国内目前数量为4089家。
而根据专家的预测,这还远远不够,应付逐年上升的肾脏患病率,共需要10000家才足够,如今未够一半。
△透析的三种方式:医院透析,独立透析,企业与医药共建
考虑到病人方便, 近些年血透中心一直都有扩张进社区的打算,本来是好事一桩,但最近五年内,抵制的声音却一直都不断,导致工作无法开展。
独立血透中心进社区一直在被搁浅,可极少的人看到这搁浅背后患者渴求的眼神,和生命无情消逝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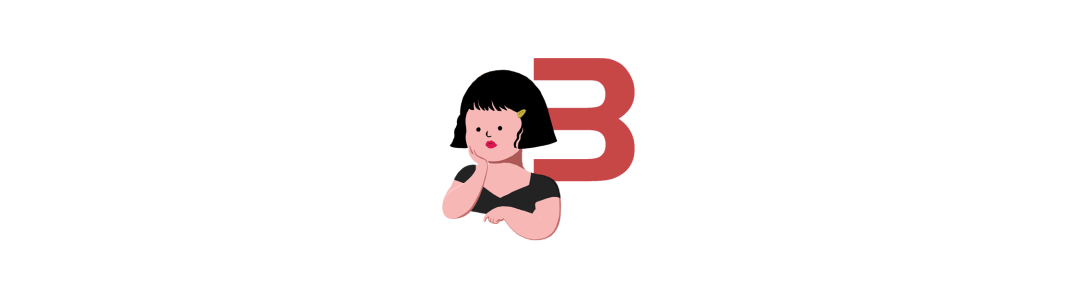 血透进小区等于白日做梦
血透进小区等于白日做梦
就在上个月, 在哈尔滨一个群力家园小区,一个本来已经建成的血透中心重新变回了原来地下车库的样子。
本来,这里将会拥有22台血透机
,同时成立相关病症诊疗项目,可谓是患者福音。
但居民受不了自己附近出现病房、档案室、医疗垃圾和成堆的病人,遂在开业前就开始联名上书,写信举报,白纸黑字的抵制:
「坚决反对透析中心建立,保护群力家园生活环境。」
居民又重新拥有了地下车库,
毕竟,相比较透析机来说,停车位更是日常刚需。
不止哈尔滨市民恐惧血透中心,武汉也有居民曾联名抵制血透中心进小区。
比白纸黑字更令人醒目的,是图片上鲜血淋漓的透析过程。
「这!就是血液透析!」短短七个字,透露出无限的歧视和凉薄。
不知道病人看了,心里到底是啥滋味。除了承受生理上的病痛,外界的不理和被迫边缘化也使他们倍感痛苦。
国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2019年5月天津紫乐明轩全体业主具体否决了,第一血透中心进小区的诉求。
2020年8月19日,市卫健委又将此血透中心的公示提上日程进行公示,二次公示后仍遭到反对。
细究抵制的原因,无非是害怕病毒传染,破坏居住环境,以及,肾病死亡率很高,居民们也害怕血透中心最后变为停尸房。
只是居民们害怕病毒感染这一点,都不用问专业的医生,动动手指百度就知道,肾脏疾病根本不具备传染性。
医疗垃圾?停尸房?昆明市德倍康血液透析中心的医生针对大家的疑虑也给出过答案:
“因为要社区化,所以感控的处理非常规范,省力也有专门的血液净化质控管理,该有的审核的流程都少不了,污水、医疗垃圾的处理也都是非常规范的,甚至比一些社区医院的处理还要规范。”
在我看来,如果救人治病的医疗中心,真的是人们众口铄金的怪诞之地,那又如何解释学区房、医院旁边的房价总要比其余地方贵出三分之一不止?
关键的是,血透中心并非医院,病人们只是来透析,
4个小时后便会自主离开,所谓「停尸房」也不过是无稽之谈。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但在我看来,那些抵制的理由脆弱也漏洞百出,除了一些私心和众嗨之外我实在找不出什么逻辑。
其推动力居然是数十名尿毒症患者,在北京通州的一个院子里私自组建了一间透析室,
很显然,这是违规操作,但他们想活下来。
搜索血透中心,可以看到许多患者发问:
「不想去公立医院做透析了,有靠谱的私立介绍吗?」
这其中,又或许牵扯出来私立医院资质不全,违规操作,清洁不到位等问题。
但凡是个投资人都知道,建立血透中心是一门血赚的生意,只是目前这个行业仍旧是一片冷门和蓝海,
自营血透中心迟迟不推进,社区无论如何都进不去,倒逼出来的压力,除了病人,还有公立医院。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在19年的时候出现了大面积感染丙肝的现象,波及人数高达69人。
后来东台市人民医院在做修整复盘的时候,才发现魔鬼全部都藏在细节里面。
问题的关键是:
患者多,人力不足,一忙起来,操作就不一定规范了。
血透中心进社区,解放的不仅仅是公立医院的压力,患者的焦灼,还有作为病患家属的轻松。
毕竟晚期的肾病病人,是需要家属陪同陪护下去医院的,有的还需要坐轮椅。而当下社会这个忙碌现状,4个小时又有几个人能抽得出来?
 国外
真的实现了社区透析
国外
真的实现了社区透析
你会赞同血透中心进社区吗?就这个问题,我采访了身边不下10个人。
有人说不——因为自身无需求,有人举双手赞同,这显然是一种人文关怀的进步。
而当我还在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在国外,血透中心设立在社区之内,已经是非常常见的事。
在新加坡和美国
基本上70- 80% 的透析患者都是在独立的透析中心来完成治疗
,而只有5%-10% 的透析患者是在医院接受治疗。
与国内现在完全相反,在我们这里是,5%-10% 在独立透析中心,
70- 80%堆积在公立医院,因为数量跟不上,民意难统一,项目难推进。
其中新加坡的独立透析中心可以说是楷模,他们输出一种家人式关怀,设点在社区,温馨的环境,积极向上的氛围,大大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除此之外,他们还提供多维度康复服务,身体复健、心理康复、技能培训等多重护理关怀,对于长期稳定的ESRD,在血透之外,正常工作生活,实现自我价值是非常常见的。
被挡在社区外,市场供不应求,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
中国的平均透析治疗率不到20%,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意思就是,
100个肾病病人,只有20个人才能得到有效治疗手段。
全球来说,平均透析治疗率为37%,光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治疗率就达到了90%。
被拦在社区外的,不止血透中心
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一句戳心的话,大意是:
现在残疾人都不允许上电梯了,讨论期变性人去哪里上厕所简直是高级问题。
一个血透中心背后我发现更大的口子,肾病患者、残疾人、老年人、病危即将离世的人….这一庞大的群体也正在逐渐被正常健全的我们遗忘,抛弃,乃至是歧视。
我这还正在看,「血透中心进社区怎么这么难!」马上又被关联出「养老院进社区为什么这么难!」的新闻。
18年的时候,兰州的一家社区里的托老所遭业主断电抵制。
11位老人在熬过了8个没水没电的夜晚后,不得不被迫搬回原处或被家属接走。
原因也很离谱诡异,
据说,楼里多一个养老机构,也能会影响安宁。
比起血透中心、托老所、更难的还有「临终关怀中心」进社区。
2019年22月,位于杭州市中心的朝晖九区,本来即将打算要建立的临终关怀中心,又因为居民强制抵制,被迫关停了。
居民们反应也是非常之强烈,不仅有联名的“抗议书”还多次向街道、省卫生厅、省政府强烈反映。
“临终关怀都是关怀快要去了的老人,到时候救护车、殡葬车呜啦呜啦地开进开出,叫我们怎么住?”
“不知道怎么想的,要把这种中心建到小区里!”还有人认为,小区的房价也可能因为“临终关怀”而大跌。
上海的一位女士,听说要建立关怀医院眼泪都吓出来了:
“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办?他们都才只有一两岁啊!”
这个逻辑关系,反正我是顺不过来。
其实,人们抵制的也不是临终关怀中心,朝晖九区的居民说:
「建在隔壁小区我们就同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