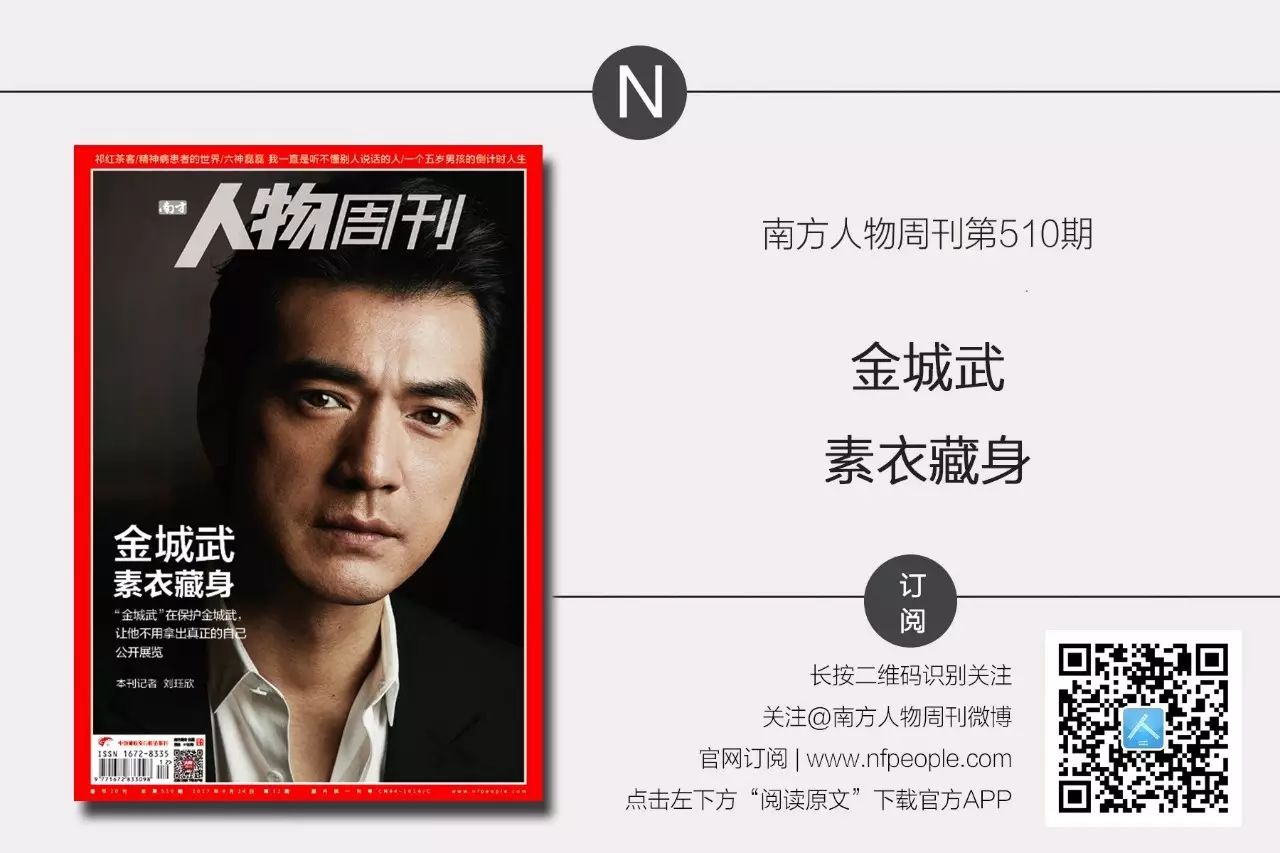但我可以毫不怀疑地说,“良质”,正是范雨素身上所拥有的品质。为了解释良质,请允许我引用《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中的两段话。
范雨素火了。《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的作者罗伯特·M·波西格死了。
一位中国女性劳动者,一位美国白人男性知识分子,站在社会阶层金字塔的两端,或许甚至不曾有过遥遥相望的机会。2017年4月24日,在这个平淡的周一,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人,以虚拟粒子的方式产生了惟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集——中国社交媒体网络是一片神奇的湖,你永远不知道扔下什么,会掀起10万+的涟漪,抑或是沉入海底。
我一向有种人多偏不往哪去的奇怪心态,往人性深恶处觉察,大概是文字工作者的嫉妒。
然而出于职业态度,哪怕在收藏里晾上
24
小时又
24
小时,也总是要看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当越来越多媒体圈之外的人也开始分享,好奇心便由不得人了。到底有多好?是否有那么好?人们竞相转发的心理是什么?
恰在此时,我看到另一则推送:《你也迷过吗?它的作者去世了》。
是的——我在心里频频点头——是的我迷过。这本书曾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价值观,影响了我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解决了我很长一段时间里形而上的困惑。什么,他走了?
伴着惊讶和哀叹,分享的指令迅速被执行。在一个晴朗、大风、树动不止的春日早晨,我甚至找出了当时的读书笔记,拂去笔记本上的灰尘,报以哀悼和沐浴更衣的虔诚一行行重温,重新触碰那个遥远的精神导师。
读着读着,范雨素走进了脑子里。
再读,罗伯特·M·波西格变成了范雨素。

曾有一个朋友问,《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写了什么,我在微信对话框里叮叮哐哐大半天,言不尽意,最后删掉回了两个字,“良质”。朋友很奇怪,这是什么?就这样?就这样一本看起来无甚新意的书,值得这么多人喜欢?我想他心里一定在想,你们啊就是书读得太少。
但我可以毫不怀疑地说,“良质”,正是范雨素身上所拥有的品质。为了解释良质,请允许我引用《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中的两段话:
“卓越”暗示着对生活的完整或惟一性的尊重,因而不喜欢专门化。它还暗示着对所谓的效率的轻视——它具有更高等级的效率,它不止要求生活的一部分卓越,而且要求生命的本身就很卓越。
所以《奥德赛》中的英雄是伟大的战士,足智多谋,随时能滔滔不绝地演说。他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无限的智慧,他知道要承担神明所指派的工作不可以有太多的抱怨。他也能自己建造并驾驶一艘船。用犁拉出来的痕迹和别人一样直,他能投掷铁饼击败年轻的吹牛家,也会拳击、摔跤和赛跑。他还会剥牛皮、剁牛肉,把牛煮了吃。同时也会因为听到美妙的歌曲而感动流泪。事实上他是个非常杰出的万能选手,他已经超越了希腊文里的“卓越”。(《禅》342)

在这一层面,我不能再同意淡豹在《关于范雨素的手记》中提到的,范雨素溢出了所谓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的范畴。实际上,当人们在用“底层”“打工”等标签框定某个人及其作品时,我们的评判标准已经有了芥蒂的栅栏。而这种阶级、身份的分野意识,来源无他,正是强调理性、结构与逻辑的现代认知框架赋予我们的。我们的教育是分科的,我们的知识是分专业的,我们的工作是分等次的,我们讨论“理工男”与“文科女”的特征,讨论“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区别……现代人在现代教育下所看到的世界,四分五裂成一个个边界分明的储物格,也因此成为牢笼。
当然,范雨素不修摩托车。但正如所有体力劳动一样,只要人全身心地对待手上的工具,无论是笔还是老虎钳,或是拖把扫帚、尿布,达到身器合一的状态时,TA就是完整的,足以称之为艺术家。我的意思是——
“它们背后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你做任何一件事都可以把它做得很漂亮,或是很丑陋。(《禅》266)”
“其实组合烤肉架是雕刻艺术早已失传的一支,多少世纪以来,由于知识错误的分野,造成两者的分隔,因而如今一旦把它们连起来,就会显得有些荒谬。(《禅》151)”
态度很重要。我甚至可以大胆推测,能写出这样文章的范雨素,一定也是一名让雇主放心的好月嫂。一个具备良质的人,无论做什么,都会拥有差不多的风范。问“范雨素是怎么写出这样的文字的”,这个问题就如同书中问,“你想知道怎样画一张完美的画吗?很简单,你先让自己变得完美,然后再顺其自然地画出来,这就是所有专家的方式。(《禅》293)”
我忽而明白了书中的一句话,也同时明白了其他的许多话。譬如,“良知会像水波一样荡漾开来(《禅》324)”;譬如,“我琢磨,他们的前生是帝王将相,今生是草芥小民。所谓的高层,底层都是同一个灵魂。(范雨素语)”
应景的是,最近圈内还有一篇文章很有趣,东林君的《修车去了》。我也相信他在4S店一定能参禅悟道,把车修好。
好的。
我也要认真吃饭去了。祝你也不与你手头的工作分离。
图片来自网络
文 邱苑婷
编辑 翁倩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