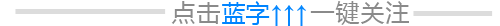

经公众号“香港凤凰周刊”(微信ID:phoenixweekly)授权转载。
1917年,段祺瑞以“讨逆军”成功镇压张勋的复辟闹剧,“再造共和”,却拒绝恢复国会,并欲废止临时约法。段的行径招来了南方五省的反对,护法运动展开,中国陷入南北分裂。自此时起,至1929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分裂与争战的状态竟在中国持续了十余年,以“军阀混战”的特色为今人所熟知。
打仗离不开军火,清末遗留的兵工厂不但产能有限,且多遭兵燹,海外输入理应成为大军系必须的考虑。然而,欧战后在美国倡议下,世界主要武器生产国联合对华实施军火禁运,一禁就是十年,直到国民政府完成统一方才结束。在禁运背景下,列强被迫保持中立,无法在军事上扶持那些他们想要支持的对象。皖系、直系、奉系的大军阀,虽长年背负“帝国主义傀儡”之骂名,却难以得到帝国主义的实惠,都是想方设法从别处挖来他们需要的军备。
五四运动次日——1919年5月5日,正当巴黎和会、中国南北和会分别在巴黎和上海召开之际,北京外交团领衔(英国)公使Jordan代表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西班牙、葡萄牙、巴西、沙俄八国政府照会中国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由于中国南北尚未统一,各友邦反对重滋战端,故在中国成立为各省承认之统一政府前,将约束其国民,禁止向中国输入“军火及制造军火之器料”。照会还提到,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丹麦驻华公使亦有赞成。其后,列强便不顾北京政府提出的外交抗议,径自管束其国民,令之不得将军火售予中国人。
禁运协议的达成理由虽被列强统一口径称为“推动中国南北和议”,但其实诸国各怀心事。西、葡、巴本来就跟中国没有什么军火贸易,参与禁运只是做个顺水人情;沙俄遭遇国内革命,自身存亡已成问题;法国在华支持和平运动,则是与其战时盟邦合作的延伸。真正值得追问其动机的,只有美、英、日三国。
作为商业强国和国际贸易秩序的维护者,美英两国确实希望看到中国和平统一,这对他们在华商业利益是极大的利好。美国驻华公使Reinsch甚至对中国抱有一定情感,他最早劝说中国派兵参加欧战(中国会因此实现军事现代化),并向段祺瑞许诺财政援助及庚子赔款的使用权,不料未获其政府批准,段氏因而转向日本。英国则有限制中国军事发展的心理,中国未能遣军欧洲,主要的阻力就来自英国。英使Jordan更明白说过:“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对军事体制全然无知的和平的国家……欧战已经过去了,应该建议中国放弃其军事计划,而回复其正常的状态。”
除此之外,提倡军火禁运对美英还有一额外好处:遏制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扩张。欧战期间,趁列强无暇东顾,日本大肆在华培植合作对象,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倒袁”的护国军,都在军事上仰赖日本人的援助。民国初年中国武器进口原呈列国竞售、德械居首的局面,到欧战末期,已为日本独占90%以上的份额。而日段合作推出所谓“中日军事同盟”,对美国倡导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更是严重威胁。1917年,Reinsch更觐见段祺瑞,要他收回抵押凤凰山铁矿从日本贷款的协议,被段氏反诘:“中国是否不必保持国际信用?如美国贷款,中国不也需要签订同样的协议?”
日本接受不利于自己的禁运协议,则是多方面机缘促成的结果。首先是1918年,积极介入中国内政的寺内内阁因米价风波辞职,继任的首相原敬转向与美英协调的外交路线。其次,当时中国与国际舆论都将日本视为在华滋造战端、阻止和议的恶势力,中国反日情绪尤其高涨,日本继续进取会陷入不利。最后,因为欧战已经结束,美欧将有大批闲置的军械可以倾销中国,日本不但难以维持目前的垄断地位,还反而可能要面对被西方列强武装起来的中国。鉴于这些考量,日使小幡一反此前力推中日同盟的态度,劝其政府接受了禁运协议。
禁运在南北和议的背景下开始推行,而列强本来以为中国的和平统一不久即将实现,故没有在条款细节上仔细推敲。对于禁运区域,英国的规定是“中国或任何中国的割让地、租借地和租界”,日本则只针对中国政府的管辖地,把台湾、旅大和青岛都排除在外。而无论任何一国,都并不禁止其在华军警商民在中国境内携带军火,仅不允许他们转给中国军民。对于禁运项目,军火本身自不必言,但“制造军火之器料”究竟为何?各国各有宽严不等的解释,这成为后来禁运国之间发生矛盾的一大缘由。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疏漏,禁运还是持续实施了十年。列强不但从此不与中国军阀签署军售合同,连以往合同的交付工作也就此搁置下来。禁运在1924年之前尤为严格,军火价格因之飞涨,在1920年的青岛,一颗步枪子弹卖到了1元,折合海关白银0.63两;在1924年的上海,一支法制左轮手枪及百粒子弹能卖150元,是法国马赛原价的十九倍半。
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高价是市场无货,零星贸易走入黑市所致。军阀作战需用,自然不能靠此等来源支撑,为他们提供军火的禁运破坏者,无论为商业还是政治的利益,都是大批量对华输入的。正是这些破坏者的作用,使军火禁运的效果在1924年后逐渐削弱,竟被许多列强外交人员视为“失败”。1929年,英国见全国已统一于国民政府,遂提议废止禁运,得到列强响应,长达十年的军火禁运,到这时正式宣告结束。
禁运协议条款定义不明,诸国参与又各怀心思,本就存在缺陷。更致命的是,代表中国的北京政府从未接受协议,列强在法理上只能约束其国民的军售行为,而无权禁止所有运售中国的军火。到1924年后,虽有英国利用自己的地盘及影响竭力制止,还是有大批来自德国、捷克等非禁运国的军火输入中国,对禁运实效形成冲击。
后人研究十年军火禁运的历史时,常把它划作两个部分:1919-1923年的五年是禁运前期,1924-1929年是禁运后期。禁运前期对军火输华的遏制效果甚好,但讽刺的是,这一时期正是禁运之参与国在扮演禁运的主要破坏者。
1919年10月,隶属北京政府陆军部的航空署向英商订购大批飞机。飞机虽名曰商用,但根据陆军部留下的文件,可知其暗怀待订货交齐便“实我边防”和借机发展制机技术的军事目的。列强自然也能料到飞机用途的模糊性,英国政府对此做了撤去机上所有武器装置、密令来华英员不得在内战中帮忙驾驶或协助飞机起飞、警告北京政府勿将飞机付诸军用等防范工作,还是遭到美、法、日三国强烈抵抗,合同不得不中止履行,此时已有159架飞机运抵中国。飞机之外,日本在安东设置火药厂,美、日、丹麦等国售予中国军阀军工机器,也都引起过一时争议。
最早给禁运带来大麻烦的,则是经列强多番游说方“加入”协议的意大利。意国从未与列强达成一致,它加入禁运协议有一“保留条件”——从前的军火合同不在禁运范围内。列强并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以英国为首,他们始终在与意大利周旋,意使则不断闪烁其词,不正面回应。就在英国以为意方已放弃“保留条件”之时,意国大批军火突然就运到了中国。这批军火究竟到了哪个军阀手里,数目多少,目前尚无确切的答案,仅从各方报告看,步枪有一万九千到四万支不等,野炮有二三十门,机枪可能有几十挺,枪弹则从300万到5000万颗皆有报告,波动范围很大。
意大利军火输华数目虽巨,究竟只发生一次,其后便偃旗息鼓,这次疏漏也没有挫败列强的禁运决心。然而,从1922年开始,来自捷克、德国的军火输华愈演愈烈,禁运也逐渐得到了“无效”、“反助德械”的评价。
捷克是依巴黎和会独立的新兴国家,其安全有赖于协约国的保证。虽然拥有著名的Skoda兵工厂,捷克政府并没有主动到中国捞一笔的心思。捷克军火输华,都是国际掮客借道欧洲主要航运国中转而来。而捷克自己是内陆国,并无港口可供输出,结果在中国海关的记录里,完全没有它的记录,反倒是在中国从未见到其武器的波兰,因作为中转站被记作来源,偶尔占据显要比例。尽管真实的销售数量缺少记录,但从Skoda代理商在华之活跃亦可推知其规模不应小觑。1925年徐树铮访欧,在捷克停留多日,几乎全为这里的兵工厂。捷克军火输华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二战:国民党军队是捷克轻机枪ZB26的最主要使用者,淞沪会战里,三个所谓“德械师”用的就多是这款捷克机枪。
德国军火输华,其政府亦非幕后黑手。相反,他们虽无诚意加入禁运,却有充分的理由撇清责任:一方面,德国作为战败国,已失去在华治外法权,没有资格管束其商民行为;另一方面,根据《凡尔赛条约》,汉堡被划为国际自由港,德国政府没有足够权力控制这里的货物输出。对中国军阀而言,德国人在中国没了特权,也是他们更愿意交往信任的对象。结果,大批军火从德国运往中国,却没有人“应该”对此局面负责。

国民党军队“德械师”
没有政府作为,德国并未有意借军火扶持其在华代理人,所有军售都是纯粹的商业逐利行为。德国军售也不分对象,直、奉、桂、晋、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广东的国民革命军都有购买德国军火和军工器材的记录,连局促在海南岛的邓本殷也由德商供售军火。其中大头儿还要数奉系张作霖,日本资料显示,在1925年5月至1926年4月间,德国向奉天销售了17.1万杆步枪、4500万颗子弹和62挺新型机枪,这个数字未必属实(日方情报一向夸大),但张氏大量购置德械应是属实。德械在华的影响也远较捷克深远,国民党清党后,其军队就开始换用德械,并因此雇佣了著名的德国顾问团,虽不至于真令国民党军队“德化”(包括三个“德械师”),却也真为抗战准备立下汗马功劳。
枪杆子出地盘,军火是军阀的命脉。在禁运的背景下,军阀们有必要想方设法寻找替代,填上列强袖手留下的空缺。替代手段有直接关乎军火的,也有看似无关的:禁运协议同时阻碍了军阀抵押国内矿山、税源去换取军事贷款的“卖国”之路,筹措军费全靠对内横征暴敛来完成,如张作霖便采取了向大户摊派、滥发通货等手段。
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想象:军阀的军火获取固然受国际政策、掌握资源、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限制,但真正决定他们手头枪杆子的质与量的,还是军阀大佬自己的个性。
袁氏之后掌权的皖系军阀便是一例。皖系唯一的首领是段祺瑞,他以亲日著称,却在“二十一条”交涉时非常强硬,未因军备不足而畏缩;南北分裂因他而起,但直皖战争中,他却不许部属用重炮对敌,“恐火力过猛,伤亡过重。”段祺瑞的信念决定了他这样一个人,自然不可能在搜罗兵器方面“想出高招”,不过,他的亲信徐树铮弥补了段氏的“短板”。

段祺瑞
为段祺瑞引进日械的就是徐树铮。1918年,第一批日械运抵秦皇岛时,段氏已辞去内阁总理一职,为帮他恢复权力,徐氏竟引奉军入关,劫夺军火。在对南方用兵时,也是徐树铮以日械换取曹锟、张树元、阎锡山等的支持。但即使是徐,也有为其他动机而忽略军事利益的时候,1919年秋,就是他率一旅之众远赴外蒙去强化中国的地位,在日本关注的核心利益——满蒙问题上与之针锋相对。1924年段祺瑞东山再起,徐树铮又被委为专使,到欧洲为段氏寻求军备,据称曾与墨索里尼谈判军援。可惜,徐在回国后不久就被冯玉祥部属扣留杀害,皖系也就此失去了重掌实权的希望。
皖系之后崛起的直系被称作“英美傀儡”,但其实英美只是看中他们对和平的态度。尤其是自称“不做督军不抢地盘”和“不借款,不入租界,不与外人勾结”的吴佩孚,深得英美在华人士及报章杂志的好评,说他有别于一般军阀,希望中国能被他统一。然而,英美两国的支持向来是口惠而实不至,表扬归表扬,能查扣的军火还是照扣不误,也正是在直系全盛时期,英美两国政府加强了对华的军火禁运,虽然不是冲着直系而来,但也由此可见做英美“傀儡”完全捞不着什么好处。再加上直系军阀本身对军火的懈怠态度,连汉阳兵工厂的技术人员都能被张作霖挖走,他们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装备远逊于奉军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奉系张作霖是军阀里发展军力的模范。他两次入关劫夺军火,还从西伯利亚撤退的日军手里收货。不过,奉军手里的武器,主要还是来自德械与自产,日本政府方面受禁运协议限制,外加不愿看到张作霖过于强大,并未直接向他提供军火。张作霖自己也对日本多有防范,他靠法国人培训飞行员,并雇佣日本、英国、白俄、德国多国顾问,刻意不让日本人形成垄断。1925年,奉系在掌控北京政府后,进口德国、捷克军火更为变本加厉,根据海关资料,从该年至1928年,全国进口军械的80%以上都为奉系所购。

张作霖
不光是进口,张作霖还在国产军工方面做到了独领风骚。他兴建的沈阳兵工厂,由丹麦、日本、德国引进器材,由丹麦、荷兰、德国、白俄、英、美多国引进人才,并从内地老厂高薪挖角,1924年大部分竣工开始作业后就取代了汉阳厂成为中国第一大厂。据齐锡生估计,1928年这个厂年生产能力约占全国一半:步枪80000杆、机关枪70-80挺,而炮的生产能力王铁汉估计有300尊——比关内的总和还要多,还是唯一一个能造出迫击炮的工厂。张作霖还是全国唯一企图建立一支舰队的军阀,但在禁运时期,他的努力过于“山寨”:两艘舰艇由商船改成,一艘由破冰船改造,一艘是卸去武装的日本鱼雷艇,到1927年均次第报废。
至于其他军系,大多因地理位置不利而多求诸自产,但远远做不到奉系的生产规模。如四川全省号称有143个兵工厂,其实大多为修理厂、弹药厂,只有少数可以生产粗糙的步枪,到1937年川军开赴山西抗日,他们手头也还是这类山寨武器,“往往打了二三十发子弹,不是枪机打不开,就是膛炸了。”唯一的例外,是在山西“保境安民”的阎锡山,他自建太原兵工厂保证军火供给,是北洋时期在沈阳厂之外的另一军工亮点。
前边所讲的,只是商业输入与国内自产的军火,它们的分配并不由中国境外的势力决定,也就很难影响到国内的政治局势发展。然而,尚有一种纯政治目的的军火输入,在列强禁运的背景下进入中国,即苏俄对广东革命政府与冯玉祥的“无偿”援助。这些军火的到来,打破了1920年代中国的势力平衡,并深远地改变了之后的中国历史,而列强费尽心力执行的禁运政策,恰恰为苏俄渗入中国搭建了舞台。
1920年,苏俄稳定在西伯利亚的统治后,开始找回沙俄在远东扮演的角色。他们与北京政府和奉天当局分别谈判,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并索回中东铁路的特权;第三国际派代表来华,红军也在1921年开进了外蒙,但苏俄在中国还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合作对象。一开始,他们想拉拢吴佩孚,因外蒙问题无法达成妥协,便在南方联络国民党,在北方联络冯玉祥。
1924年9月22日,第一批苏俄输华军火自海参崴启航。英国掌握了这一情报,并在随后报告称货物为两尊野炮及800杆日式步枪,但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10月5日,俄舰抵达虎门附近,在黄埔学生监督下起卸。次日,另一俄轮亦至,英方报称载有2000杆步枪及若干野炮,孙元良回忆则说黄埔军校收到500杆三八式步枪。
1925年秋,俄援军火始大批运至。为日本政府得到情报者就有三批,合计有步枪28000杆、机枪905挺(应有夸大)、炮90尊,此外还有子弹、炮弹及飞机机件。值得一提的是,苏俄提供的军火多为日制,大概是红军更换自产装备而淘汰下来的旧货。1926年,又有两批军火运来广州,此时已是北伐前夕。
在冯玉祥一侧,苏俄给予的军火多经陆路从外蒙送来,很难为列强掌握情报。根据被发现的两张收据,在1926年6月以前,苏俄以值630万卢布的军火交予冯玉祥,并准备继续付400万卢布的军火。军火内容难以查考,日本情报称有步枪、手枪、机关枪、各种炮、汽车和双叶飞机,但数量报得过于夸张。1925年12月,冯部俄国顾问有一说法,称冯军现有步枪约59000杆,其中包括“最近收到的13600杆”。可以确定的是,冯玉祥特别青睐手枪,还特地跟苏俄要来1000支俄制剑,应是用于装备著名的西北军大刀队。

冯玉祥
俄援军火大大降低了国民党组建自己军队的难度,提升了它的实力,国民政府顺利统一中国,俄援应为一大原因。一直以来,在国共两党的宣传里,国民革命军的火力优势都被刻意忽略,只强调战争性质、士气精神等意志因素。然全军采用一式步枪、饷弹充足,且拥有机关枪和炮队,在物质上就远胜于绝大多数军阀部队了。东征陈炯明时,这种对比尤其明显,蒋介石在攻克淡水后竟告诫将士,逆军没有机关枪,是用一串纸炮置在洋铁箱内封闭后引纸线燃,“在炮兵阵地上看得很清楚……以后本军切勿上当。”
国民政府享受了俄援的优势,并借此东风一口气影响大增,但同时第三国际也站稳了脚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以壮大。孙、蒋二人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层威胁,只不过自信可以掌控。苏俄也没有给过国民党太宽限的选择条件,特别是在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随两艘俄轮到广州,他自己先乘小艇登陆,与蒋介石会谈四小时,双方达成妥协后方让俄轮靠岸起卸军火。这次谈判如果破裂,鲍罗廷是可以把这批包含“两万支来福枪、数门野炮”的军火交给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武装的。
比较讽刺的是,1927年4月蒋介石宣布清党,与苏俄决裂,日本的第一反应却是借机游说苏俄加入军火禁运协议,但为俄方回绝。至于美国、英国,虽赞同国民政府反共,对禁运协议还是继续坚决执行,连当年12月爆发广州起义,有美籍华人前去推销镇压用催泪瓦斯,美国政府得报后亦电令驻华公使要求禁止。
总的来说,国民政府应当算作列强十年军火禁运的受益者。禁运不但增加了国民政府之对手购买海外军火的成本,还提升了他们自产军火的难度,国民政府自己的俄援则源源不断。只不过北伐二十年后,又一轮来自美国的军火禁运使国民政府深受其难,有些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的意味。
中国海军能航母出海,绕不开这位狠抓装备的海军司令
刘华清说:“我抓航空母舰,我这辈子肯定用不上,我是为以后当海军司令的人在做准备。”

△
点击图片进入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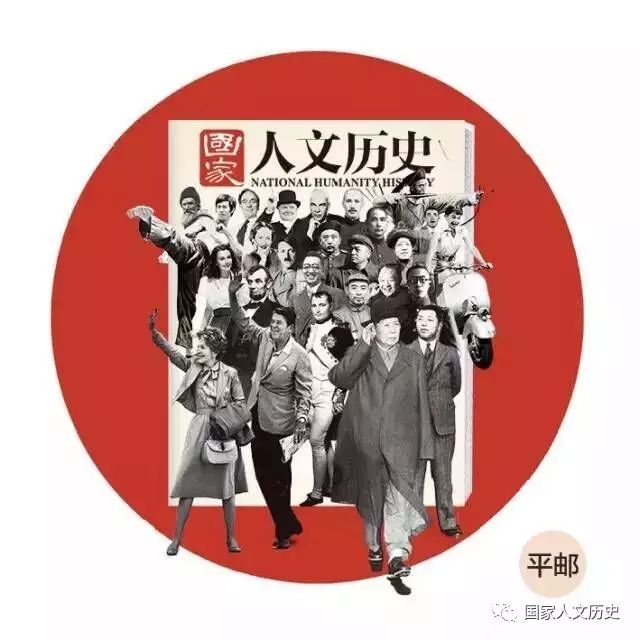
△点击图片,查看所有往期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