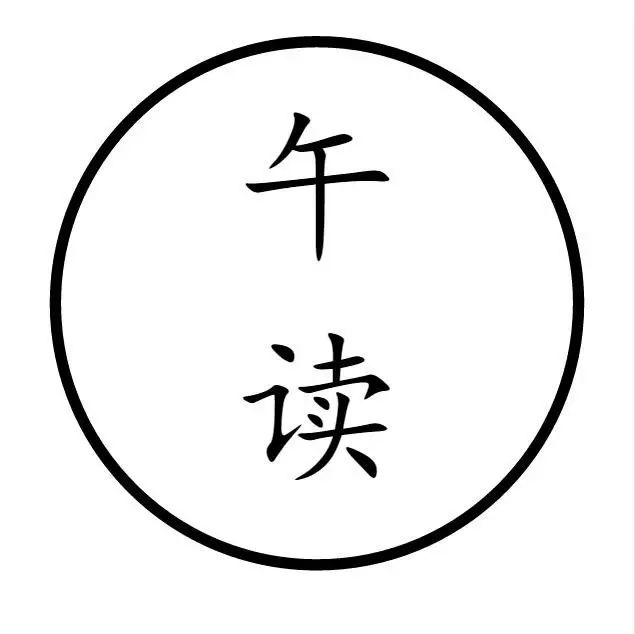我的2024年以6月为界。6月以前,是忙了一年工作积攒的疲惫、春节回老家见朋友充电后的放松、进入新一年在工作量考核压力下找选题的焦虑、进入工作状态后连续两三个月近乎无休工作的沉浸。然后急转直下。
起初是这样:2023年秋季体检时,身上不同部位长的若干结节中有一个较为可疑的乳腺结节,医生建议要密切随访。于是乎,2024年春节假期,我去了老家肿瘤医院。结合彩超,医生认为还可观望,三个月后复诊。
6月初,我回老家进行常规复诊。我心态乐观,医生开了单子,做个B超测个血氧我都嫌麻烦,到门诊排队等叫号,还在想这多耽误工作。没想到医生看到B超结果,扔下一句话:得赶紧手术。即便已经连续几年看到报道,讲如今罹患乳腺癌的女性呈年轻化趋势,我一时还是难以接受。我拿着打满一张纸的术前检查单子(包括CT、钼靶、磁共振等等),交了几千块住院押金,每天来医院一至两趟。那时我全心全意希望影像学检查结果可以“逆风翻盘”,让我免去手术之苦。如此跑了一周,端午假期结束后,我紧张兮兮给医生办公室打电话,得到回复:你这个看着是恶性了,当然要手术啦。
术前谈话。医生告知有可能最坏的结果,比方说,术中他们取下肿瘤,如果冰冻结果显示周边有癌细胞,就要扩切;如果边缘还有癌细胞,就要全切。那就意味着要化疗。在办住院后,我在住院楼的墙上宣传栏看到化疗的诸种副作用:恶心、脱发,等等。
每天我都有这两种情绪:希望病不要太坏,希望病不要太影响工作。我忍不住打听,放疗要多久?化疗要多久?(放疗要连续5周左右。化疗的周期是21天一次,每次要输液2-3天。)手术前一天我下载了北京不同医院的App,评估边工作边放化疗的可能性。

▲做手术前朋友挑选相见的咖啡馆,叫“真高兴”,朋友说,意头很好
这是个情绪病,大家都说。家人、朋友劝我,先别想工作了,身体最重要。接受这点并不容易。今年是我做记者的第七年,我从大学开始就在这个行业实习,眼见着一篇篇好稿诞生,自然也想写出有价值的报道,但是这几年媒介环境剧变,读者在长文章上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我想一边保证文本质量一边冲击新媒体速度,日日焦虑。再加上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不写稿就赚不到什么钱,北京的生活成本摆在眼前,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命当然重要,但谋生也很重要。
手术前一晚,不能进食,不能喝水。在病床上坐等手术通知的一整个白天,我刷手机,看了半本《世界小史》,又捡起《亮剑》重读。窗外的蓝天白云由明转暗,我同一病房的其他三位病友已去了手术台,我终于被“叫号”,排到了当天倒数第二台手术。

▲病房的窗景算是很好
手术后,麻药导致的强烈副作用让我第二天吃什么吐什么,在一层楼同时有至少一百人说话的菜市场般的住院部,我躺在床上回消息,打几个字得闭上眼(每一个字都让人眼前发晕),全身不同地方同时传导痛感——强烈的感觉涌上来,我现在想工作也没法工作啦。我在心里终于给自己按下了暂停键。
接下来的日子,我在身体的不适中等待结果。我和隔壁的病友(以及我们的家人)每天闲聊,我们等医生每天早上来查房,讲两句能给我们正能量的话;护士来输液,晚上查房。医生说,我术中冰冻切片的结果是好的——但这不能说明什么。在我隔壁病床的姐姐,只有一个小结节,做了逐项检查后,医生按良性做手术,术后几天,病理结果显示肿瘤为恶性,半个月内,她又进行第二次手术。同一病房的另一位病人已经是第三次做手术开结节。
又过了三天,医生查房时匆忙告知,可以先回家了(因为医院床位紧缺,要让位给下周同一时间做手术的病人)。“病理是好的。”那就说明顺利通关了吗?医生说,还有免疫组化结果,要再等几天。回家查,免疫组化结果用于判定肿瘤良性或恶性、确认癌症分期,等等。
术后八天,我拔了引流管,告别每时挎在身上、记录积液的引流瓶(这段时间,我的活动范围仅限家里的客厅—饭厅—卫生间—卧室,每到一地,引流瓶就往地上一放,睡觉时,引流瓶挂在床边,身体一夜不动)。免疫组化结果已出,万幸我的这一个肿瘤处在癌前病变阶段。不仅不用化疗,还不用放疗,算是大喜。至于其他结节,仍需密切随访。
在换药室外排队时,一位面色红润的女士抱怨,她5月做的手术,现在还不能放疗,因为患肢还不能抬过头顶、摸到另一侧耳朵。聊着聊着才知她已做过六次化疗。“该受的罪一样也少不了。”第二次化疗后,她说,睡觉醒来,枕头都是黑的,是掉的头发。
术后10天,我到医院查看伤口,下午,雨过之后,我到家附近的小公园里熟悉的咖啡馆,上二层,点了一杯热饮。忽晴忽阴。我刷了会儿豆瓣,抬眼看,一只肥松鼠在瞅我。
我能去电影院看电影,能出门吃饭。我和朋友去看了《走走停停》。把患侧的胳膊抬起来,这个动作对我来说还是很难。我走路变得慢慢悠悠,符合云南人的平均节奏(因为步伐加快伤口的痛感会加剧)。养病的大部分时间,我用于重读《鹿鼎记》,看韦小宝如何全不会武功,却成了最终的赢家。

▲拔完引流管去家附近的小公园,遇到的肥松鼠

▲老小区里充满西南地区常见的三角梅,在《走走停停》里也看到
7月初,我可以自如行走了,便订了回北京的机票。收行李那两天,我看到公众号“后浪研究所”的一篇报道《“带癌上班”的年轻人,和他们不能失去的工作》,反复阅读,心有戚戚。有位跟我年龄相近的同行,27岁时被第一次诊断出乳腺癌,请了一年病假,做化疗、保乳手术、三十多次放疗后,重返工作岗位。五年后她乳腺癌复发,晚期,伴随骨转移,这位同行每个月的月中要坐四小时动车到医院进行检查治疗。一位患上非特殊性浸润性乳腺癌的35岁女性,在十几个人同住的日间病房里,还带着笔记本电脑准备干活。“带癌上班不一定会死,但不上班肯定饿死。”她说。
该怎么调整自己呢?
理性告诉我,要保持好心情,要想开,工作怎么都没有身心健康重要。可是感性也告诉我,搵食难,一旦脱离轨道,想要重回轨道更难。
一个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可以让我得到缓冲的新爱好是徒步。去年下半年,我和同事孟依依结伴在京郊徒步数次,我们在夏末去了白瀑寺,一个雨后的雾天爬上了海坨山,中秋假期爬了大觉寺小环线,深秋走了香山后山,看到了一点点红叶。
我体能一般,手脚灵活度一般,怕高,是个绝对的徒步庸人。但徒步是我能找到的成本较低、出行便宜、又能较长时间将自己完全隔绝于工作的爱好了。每次进山后,大半时间手机没有信号,我们没法回复任何工作消息。在登山杖一下下戳着石块、泥土或落叶尘埃的笃笃声中,在喘不匀气、额头两颊冒汗、两腿酸软发颤的劳累中,我的头脑终于被迫放松,不想采访怎么约、选题该找谁、录音素材如何选取、稿件结构如何设计;不想工作究竟有没有意义、人这辈子该如何活着——哪怕只是几个小时不想这些,也是好的。
写下这篇小文时我开始了春节假期。回老家第二天,我忙不迭和两位好友相约徒步。我们去了离市区车程接近两小时的寺庙,徒步10公里有余。在二十来度的午后,我们坐在基站附近的草地上分食三明治。太阳很好,头顶几米处有电流流过的令人不安的滋滋声。我脑海里又冒出那句话:这些事,都比工作更重要。

▲徒步遇到的好像在微笑的羊

▲雨后的海坨山徒步,树好像来自《雾中风景》

▲2024年11月初,在香山看到了一点红叶

▲2025年春节前,与高中朋友去嵩明县法界寺徒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