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因为我不快乐。我写作,因为它是一种对抗不快乐的方法。——略萨
这次采访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提到,他原本坚持每天早晨在书房写作,一周七天都是如此,绝不中辍。然而,一九八八年秋天,他决意暂时放下自己长期严格坚守的日程,作为自由党候选人,参加秘鲁总统竞选。对于秘鲁政治,巴尔加斯·略萨一贯直抒己见,他有多部小说以秘鲁政治为主题。不过,直到近期几轮大选,他总是拒绝在政府供职。竞选活动期间,他说到,竞选政治的语言总是充溢着虚情作态和空洞辞藻,对此他实难接受。多党选举之后,一九九零年六月十日,他败给了阿尔韦托·藤森。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一九三六年生于秘鲁的阿雷基帕,一座南方小城。巴尔加斯·略萨尚在襁褓时,其父母离异,他随外公一家,迁居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一九四五年他返回秘鲁,入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其后就读于利马大学,修法律课程。十九岁那年,他娶了比自己年长十四岁的姨妈胡利娅·乌尔吉蒂·伊利亚内斯。这是他的第一次婚姻,这件事后来成了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1982)的主要情节。结束利马的学业后,巴尔加斯·略萨选择离开秘鲁,去国流亡。在长达十七年的流亡生涯里,他当过记者和讲师。也正是在流亡期间,他开始写小说。巴尔加斯·略萨的第一部小说《城市与狗》,一九六三年在西班牙面世,小说是基于他的军校经历写成的。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还有《绿房子》(1963)、《酒吧长谈》(1969)及《世界末日之战》(1981)等。
巴尔加斯·略萨还是一位剧作家、散文家,曾参与拍摄秘鲁电视台的一档访谈节目,每周一期。他已荣膺多项国际文学奖项,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九年间,曾担任国际笔会会长。他育有三个子女,与第二任妻子帕特丽西娅住在利马,从他们的公寓里可以俯瞰太平洋。
——苏珊娜·亨内维尔、里卡尔多·奥古斯托·塞蒂,一九九〇年

《巴黎评论》&略萨 魏然/译
《巴黎评论》:你是一位著名作家,你的读者对你的作品是很熟悉的。那么,能否谈谈你自己都读些什么书?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过去这几年,我的阅读经验比较奇特。我注意到,同代人作品读得越来越少,反而越来越关注以前的作家。我读过的十九世纪作品远远多于二十世纪的作品。最近,相较于文学,我的时间更多花在阅读随笔和历史上。至于为什么读这些书,我倒没有仔细想过……有时是因为写作这个行当。我的写作计划联系着十九世纪:我要写一篇关于雨果的《悲惨世界》的文章,还计划根据弗洛拉·特里斯坦的生平写一部小说。特里斯坦是个法裔秘鲁人、社会改革家,还是一位后世所说的“女性主义者”。不过可能另有原因:十来岁的时候,你觉得享受这世界的时间都在前头,无休无止,可年过五十,你就发现日子屈指可数,必须精挑细选。可能就是这个缘故,我不大读当代作家的东西。
《巴黎评论》:不过,在你读过的当代作家之中,有没有让你特别崇敬的?
略萨
:我年轻时,曾经是萨特的热忱读者,还读了不少美国小说家的作品,特别是“迷惘的一代”——福克纳、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多斯·帕索斯,尤其是福克纳。年轻时读过的作家里,有少数几位至今我仍旧看重,他算其中一位。重读他的作品,从来没让我失望过,重读其他作家,间或也有这种感觉,比如海明威。现在我不会再读萨特了。跟此后我的阅读相比,他的小说过时了,失去了主要价值。至于他的论文,我觉得大部分都没那么重要了,只有一篇是例外,那就是《圣热内:喜剧家或殉道者》,我至今还喜欢。萨特的文字充满着矛盾、模糊、言不及义和旁逸斜出,而福克纳的作品永远不会出现这些情况。
福克纳是头一位迫使我阅读时手握纸笔的作家,因为他的写作技术让我震惊。他也是头一个我有意识地重构他作品的小说家,比如我会追踪时间组织方式,辨识时空如何交错、怎样打破叙事,以及他从不同视角讲故事,创造暧昧含混效果,赋予故事深度的能力。作为一个拉美人,我觉得读福克纳,对我而言非常有用,因为他的书蕴藏了一个描述技巧的宝库,可供我拣选,而我所要描述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跟福克纳笔下的世界,差别并不那么大。当然此后,我也带着强烈的激情阅读十九世纪的小说家:福楼拜、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司汤达、霍桑、狄更斯、梅尔维尔。我到现在还是十九世纪作家们如饥似渴的读者。
说到拉美文学,很奇特,直到在欧洲生活之后,我才真正发现了她,才开始怀着巨大的热情阅读拉美文学。我要在伦敦的大学里教这门课,这个经验很宝贵,因为它迫使我将拉美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从那时起,我研读博尔赫斯——我对这位作家还算比较熟悉,研读卡彭铁尔、科塔萨尔、吉马朗埃斯·罗萨 、莱萨马·利马 ,整整一代作家我都进行了研读,除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我是后来才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甚至还写了一部关于他的著作,那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我还阅读十九世纪的拉美文学,这也是因为授课需要。我意识到,我们拉美有一些极为有趣的作家——这方面,小说家们或许还比不上散文家和诗人。譬如萨米恩托 ,他一部小说也没写过,但依我之见,他是拉美这片土地上诞生的最了不起的说书人之一,他的《法昆多》是一部杰作。但假如我只能举出一个名字,那么我不得不选博尔赫斯,他创造的世界,对我来说是绝对称得上独具匠心。
除了原创性,他还与生俱来地拥有出色的想象力和独一无二的文化修养。当然,他还创造了一种博尔赫斯式的语言,某种意义上,这种语言突破了我们的传统,开启了另一番气象。西班牙语这门语言,有一种繁复、盈溢、丰沛的个性。使用这门语言的大作家们往往喋喋不休,从塞万提斯到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巴列-因克兰 ,再到阿方索·雷耶斯。博尔赫斯跟他们不一样,简洁、凝练、准确。西语作家中,博尔赫斯是唯一一位想法和语词的数量近乎相等的作家。我们这个时代堪称伟大的作家当中,博尔赫斯算是一个。

COAT | Goran Despotovski 2013
《巴黎评论》:是作者挑选作品主题,还是主题挑选作者?
略萨
:就我所知,我相信是主题挑选作者。我总有一种感觉,某些故事会降临到我身上;你无法忽略它们,因为这些故事以某种隐秘的方式,联系着你最根本的人生经验——这不容易解释。举个例子,我还是少年时在利马的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待过一段时间,那段经历带给我一种写作的真正需求和着魔似的欲望。从许多方面说,那都是一段极端伤痛的经历,标志着我少年时代的结束——再一次发现我的国家里,社会暴力肆虐,到处都是苦难,构成社会的是绝然对立的社会、文化和种族派别,它们时不时爆发出凶险的恶斗。我猜这段经历对我产生了影响;非常肯定的是,它赋予了我创作和发明的需求。
直到现在,我的所有作品大体都是这样。我从没觉得我可以理智、平和地下决心写一个故事。相反,某些人或某些事会骤然降临到我身上,要求我特别关注,有时候这种体验来自梦境或阅读。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讲到在文学创作过程中,那些纯粹非理性因素具有重大的意义。我相信,这种非理性也能传递给读者。我希望,别人读我的小说,也会有我阅读那些我所钟爱的作品时的感受。让我心仪的小说,不是通过智慧或理性触动我,而是让我心驰神往。有些故事可以完全击垮我的批评能力,让我沉浸在悬念之中。
我爱读这类小说,也爱写这类小说。我认为融合到行动和故事里的思想因素非常重要,在小说中也必不可少,但故事不能靠观念吸引读者,靠的是色彩,靠的是它激起的情感,靠的是它能产生的悬念和神秘。在我看来,小说的基本技巧就在于如何创造这种效果,换句话说就是尽可能缩短、甚至消弭故事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个十九世纪的作家。小说对我而言,依旧是冒险小说。读这种小说,就需要我刚刚描述过的那种特定方式。
《巴黎评论》:你小说里曾经具有的那种幽默感似乎消失了?最近几部小说似乎和《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中的幽默风趣相差很远。今天写出那样的幽默文字是不是很困难?
略萨
:我从来不会琢磨,今天是要写一本有趣的书呢,还是一本严肃的书。只是近些年我写作的主题好像不大容易往幽默上靠。我不认为《世界末日之战》《狂人玛依塔》或是我写的剧本,它们的主题可以被处理得诙谐风趣。不过《继母颂》呢?那本书还是有不少幽默的,是不是?我从前对幽默“过敏”,因为那时十分天真,相信严肃的文学不苟言笑;假如想在小说里讨论严肃的社会、政治或文化问题,幽默可能是非常危险的。那时候,我以为幽默会让我的故事显得肤浅,给我的读者留下这些不过是游戏之作的印象。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一度排斥幽默,这极有可能是受了萨特的影响。
萨特一贯敌视幽默,至少他写作时如此。可有一天我发现,为了在文学中呈现特定的生活经验,幽默可以是一种相当有力的工具。写《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时候,我领悟到这一点。从此我就明白,幽默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生活的一种基本要素,因此对文学也特别关键。假如有一天,幽默再度成了我小说的重要角色,那我绝不刻意排斥。其实,已经有了这样的作品。我的剧本也一样,尤其是《凯西与河马》。

Swing for Stumps | Vasiliy Ryabchenko 1993
《巴黎评论》:回忆录作家佩德罗·纳瓦甚至会画出他笔下的人物——他们的面孔、发式、服装。你会不会也这么做?
略萨
:不,我不会这么做,但有时我会列出人物传记表。这取决于我感知角色的方式。虽然有些时候,角色确实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眼前,但我还是会通过他们表达自我的方式,或者角色与周遭事物之间的关系来确定他们。有时,人物的确是通过身体特征而得到定义的,你不得不把它写在纸上。但尽管你可以为一部小说做各种附注,可我认为到最后记忆选择了什么,那才算数。能被记住的,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考察旅行中我从不带照相机。
《巴黎评论》:那也就是说,在某一段时间内,你笔下的人物相互没有关联?每个人物都有他或她自己的个人史?
略萨
:一开始,一切都冰冷、造作、死气沉沉,而后一点点地鲜活起来,人物之间相互连缀,建立了关系。这部分工作妙不可言,让人着迷:你开始发现,磁力线天然地就隐藏在故事当中。但在达到这一点之前,只有工作、工作,再工作。日常生活中,某些特定的人或事,似乎能填补空白、满足需求。猛然间,你清楚认识到,为了完成手头的作品,你到底需要知道些什么。但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东西绝不总是忠实于原型人物,它们往往改头换面、似是而非。不过,这种“碰头”的情况要等到故事到达一定境界时才发生,那时,一切条件已经把故事滋养得差不多了。有时,这是一种指认:噢,这就是我要找的那幅面孔,这就是那种腔调,这就是那种讲话的方式……可有些时候,你的人物会失去控制,这事儿经常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写的人物从来都不是从纯粹理性思考中诞生的,他们都是创作时更强大的本能力量的表达。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物即刻变得重要起来,或者似乎在自我发展,而另外一些人物则下降到陪衬的角色,虽然我一开始并不是这么打算的。写作过程里这部分最有趣:你意识到某些人物在呼吁,要求更显著的位置;故事在遵循自身规律铺展,这些规律你决不能践踏。很明显,作者没法随心所欲地团捏他的人物,人物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地位呢。这个时刻也最叫人兴奋,你在自己的创造物中发现了生命,你必须对生命怀有敬意。
《巴黎评论》:你的不少作品都是旅居国外的时候完成的,这或许可以被称为自愿放逐。你曾说过,维克多·雨果也是在流亡国外时写出了《悲惨世界》,这种经历对写作助益良多。远离“现实的晕眩”或许能给重塑现实带来帮助。你会不会觉得现实让人茫然晕眩呢?
略萨
:确实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没写过紧贴着我的东西。贴得太紧,就意味着无法从心所欲地写作。写作时要享有充分的自由,让你能够改造现实,变换人物,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行动,将个人要素引入叙事,引入纯粹的自出心裁的东西——这些很重要,绝对必不可少。这就是所谓创造。假如现实就摊在眼前,对我来说,反倒成了约束。我总是需要保持一点距离,时间上的距离,或者更好的是,时空都保持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流亡是有益的,也由于流亡,我发现了写作的纪律。我发现写作是一项工作,而且通常,可以说是你的责任。距离总是有用的,乡愁对于作家有重大的意义。
一般来说,写作对象不在场,反而丰富了记忆。例如,《绿房子》中的秘鲁不是单纯对现实的记述,而是一个被迫离开故乡、怀着对故乡痛苦渴望的人的乡愁思恋的对象。同时,我以为,距离能创造一种有用的视角。现实把事情变得复杂,让我们晕眩,而距离可以捋清现实。要搞清什么重要、什么次要,从中做出选择是很难的。唯有距离才能帮我们做判断,它廓清了本质与短暂事物之间必不可少的等级。

RUMORS | Goran Despotovski 201
《巴黎评论》:几年前你发表过一篇散文,你说文学是一种激情,这种激情是排他性的,要求毫无保留地牺牲一切。“第一等的任务不是生存,而是写作。”这让我想起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句子,他曾说道:“航海是一种必需,生活却未必如此。”
略萨
:你可以说写作是一种必需,而生活未必如此……或许应该讲讲我自己的一些事,好让大家更理解我。文学对我一直很重要,从小时候起就是这样。但即便求学时读了不少书,也写了挺多东西,我也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完全投身文学,因为那时候,专事写作对一个拉美人来说是很奢侈的事,对一个秘鲁人尤甚。那时我还有其他目标:想从事法律工作,或者当个教授、记者。那时我接受了,虽然写作对个人是根本性的事,但我可以把它放在不重要的位置上。但读完大学,我拿着奖学金到了欧洲之后,我认识到假如今后还这么定位,那我就永远也成不了作家;唯一的办法,就是下定决心,不止把文学当成嗜好,而是当成自己的主业。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决定完全献身文学。
由于那时候没法靠文学养活自己,我决定去找份工作,但条件是让我有余裕的时间来写作,而不会占用我的全部精力。换句话说,我是根据作家这个定位来谋职的。我觉得,这一次下定决心,标志着我一生的转折,从那时起,我就有了写作的力量。那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转变。
这就是为什么说,文学对我而言是激情而非职业。当然,它也是一份工作,因为我以此为生。可即使写作不能糊口,我也会继续写下去。文学不只是稻梁之谋。我相信,如果某一个作家决心把一切献给这份职业,那就要倾其所有为文学服务,而不是以文学服务于其他,这一点是至为关键的。有些人志不在此,只把文学当补充或点缀,甚至是一种博取声名和权力的手段。倘若是这样情况,他们在创作中将碰到阻碍,文学会反身报复,这样的人也无法自由、大胆、原创地写作。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强调,投身文学必须毫无保留。我的情况是个奇特的例证,下决心从事文学时,我本以为我选择了一条艰难的生活道路,从没想过凭着文学可以养活自己,更别说过上富足的日子。
这似乎是个奇迹,至今我也不能全然释怀。为了写作,我原本并没抛下什么根本性的东西。还记得,去欧洲之前,在秘鲁时,因为不能写作,我那时多么懊丧、多么不愉快。我结婚很早,所以不得不碰上什么工作就干什么。我曾经同时兼着七份工!实际上,我当然没法写什么东西。只有星期天、节假日能写上几笔,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跟文学无关的乏味的工作上,这让我特别沮丧。现今,每天清晨睁开眼,想到竟然能把一辈子的精力都花在给自己带来最大快乐的事情上,还可以靠它生活,而且活得还不错,我就感到惊喜不已。
《巴黎评论》:文学有没有让你成为有钱人?
略萨
:没有,我不是个有钱人。假如你拿作家的收入和企业总裁的收入作比较,或者跟别的行业里那些声名显赫的人,譬如秘鲁的斗牛士或顶级运动员的收入作比较,你就会发现,文学还是个薪酬菲薄的行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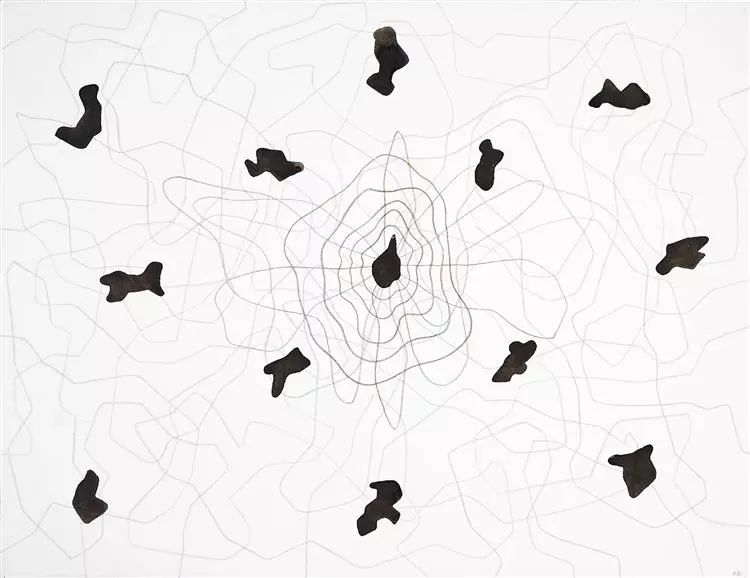
Espacio Recorrido # 102 | Pablo Rey 2000
《巴黎评论》: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你崇敬的作家和作品。现在来聊聊你自己的著作吧。好几次,你说到《世界末日之战》是你最得意的作品,现在是不是还这么想?
略萨
:我在这部小说上,倾注的心血最多,自我投入也最多。这本书花了四年时间才写成。我为此做了大量研究,读了很多书,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因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描述我祖国以外的不同的国家,时代也不同于我所处的时代,书里人物的谈吐也不是书本上能找到的。不过,从没有任何一个故事能让我这样激动不已。写作过程中的一切都让我着迷,从我阅读的书目,到穿越巴西东北部的旅行。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这本书有一种独特的柔情。这个主题也促使我去写一部自己一直都想写的小说,那就是历险小说,其中,冒险应该是根本性的——不是单纯的幻想中的冒险,而是跟历史、社会的问题意识有深刻联系的冒险。这或许就是我把《世界末日之战》当作自己最看重的小说的原因。
当然啦,这类判断往往是十分主观的,因为作家没有能力客观地看待自己的作品,来给作品排序。这部小说成了我想要超越的可怕的挑战。一开始,我非常焦虑不安。资料庞杂,让我头晕目眩。初稿很长,篇幅是最终小说的两倍。我自问,我怎样才能协调这样一大堆的场景和上千个小故事呢。这当中有两年,我总是感到焦虑。随后我出发旅行,穿越整个巴西东北部地区,走遍了内陆腹地,这次旅行成了转折点。在此之前,我已经写出了一份大纲。事先我就安排好,掌握一定研究材料作为基础,想象这个故事,然后出门旅行。结果旅行证实了许多事,也给其他部分带来了灵感。我还得到许多人出手相助。最开始,我并不打算把这个主题写成一部小说,而是想给鲁伊·格拉的电影写剧本。那时,我认识的一个熟人,是派拉蒙公司在巴黎的主管。
他有一天给我打电话,问我想不想给派拉蒙即将投拍的一部格拉导演的影片写剧本。他的电影我看过一部,叫《温柔猎手》 ,非常喜欢,于是,我就到巴黎跟格拉见面。他向我解释说,他头脑里想讲的那个故事,以某种方式和卡努杜斯战争 有关。我们不可能拍一部关于卡努杜斯战争的影片,这个主题太宽泛了,但我们想拍的电影,以某种方式联系着这场战争。那时候,我对卡努杜斯战争一无所知,甚至都没听说过。我开始研究它,读相关材料,而我最初阅读的一批葡萄牙语资料当中,就包括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 的《腹地》。
在我的阅读生涯里,读这本书是一次重大启示,就如同小时候读《三个火枪手》,成年以后读《战争与和平》《包法利夫人》和《白鲸》一样。《腹地》是一本真正伟大的书,它带给我一种根本性的经验。我完全被它震懵了,它是拉丁美洲贡献出来的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说它伟大有许多原因,最重要的是,它是一本“拉丁美洲精神”手册——在这本书里,你将第一次发现拉丁美洲不是什么。拉丁美洲不是舶来品的集合;她不是欧洲,不是非洲,不是前西班牙征服时代的美洲,也不是土著社会——但同时,她是所有这些的混合物,这些元素通过一种严酷、有时甚至是暴烈的方式共生在一起。几乎没有别的作品能以《腹地》那样的思想和文学高度,捕捉到所有这些要素构成的世界。换句话说,我能写出《世界末日之战》,真正应该感谢的人是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