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黑爪
刚开始约会的时候,我们两个木讷的人常常会冷场。为了对付这个局面,我们发掘出了一些两个人都知道的话题,“ways of seeing”是其中之一,也是最好用的一个。
这是刚才听见约翰·伯格(John Berger,或者约翰·伯吉尔,我遇到的英国人都是这么念这个名字的)死讯时,立即闪现出来的情景:约会的情景,在天坛以及其他几个地方。

▲
约翰·伯格(1926年11月5日-2017年1月2日)
“Ways of Seeing”是70年代BBC的一个四集电视节目,针对比当时早几年的另一部现象级电视栏目,肯尼思·克拉克的《文明》,它挑战《文明》所阐述的西方文化中的传统审美观。后来ways of seeing 的“剧本”被集结成书,以同名出版,甚至成为一些牛校本科生的教材,大概影响了西方一代文青。我那约会对象没想到居然会在中国,从一个写程序的小姑娘嘴里听见这个名字,很是吃惊。与其说他这吃惊是小看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读书人(或者像当时的我那样的入门读书爱好者),不如说低估了伯格的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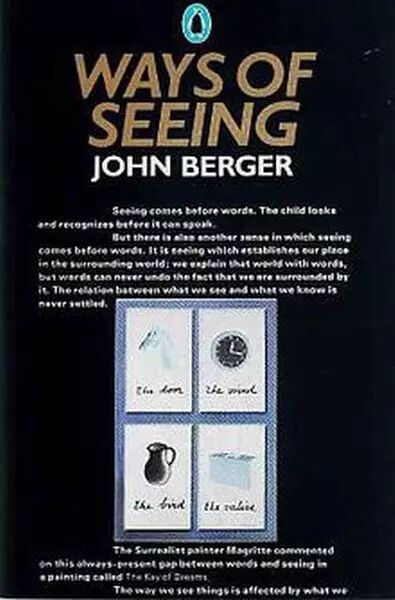
▲
电视节目Ways of Seeing海报
“企鹅”版的“Ways of Seeing”是这样介绍它的:它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绘画和艺术评论的认知,
这一分水岭般的巨作,通过文字和图像,展示了我们通常所见,是如何被一整套关于美、真理、文明、形式、品味、阶级以及性别的假设所左右。从各个层次探索了油画、摄影、以及图形艺术的意义。伯格说,当我们看见事物的时候,我们不仅在看,我们更在阅读图像语言。
如果要一句话简单粗暴地给约翰·伯格一个标签,我估计“当代白左知识分子鼻祖”相对清晰贴切。
最近一次密集地提起他,是18年后的今年(哦,已经是去年了)。2016年伯格90岁,他的众多粉丝搞了许多纪念活动,包括去他下半辈子定居的法国小村子拍摄他的起居。临近年底时,我查了一下是12月3日,我收到当时那位约会对象送来的一本新书电子版:“Landscapes: John Berger on Art”,这是Verso 11月为纪念他90大寿特意出版的艺术评论集。

▲
在伯格隐居地拍摄他生活的纪录片《昆西四季》
伯格最初是个画家,但是后来不画了,改写字,这点跟伊夫林·沃或者陈丹青有点像。只不过沃写的都是冷眼讥讽,而伯格则成为一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公知,shape-shifter。作为小说家,他最为人知的大概是1972年获得布克奖,发表获奖感言时不仅大呛金主的钱来路肮脏,更把奖金尽数赠予“黑豹”革命组织(黑豹,black panther,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活跃在美国加州的黑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毛粉,“黑豹党读毛选”的照片至今仍在网上流传,其领袖1971年曾访问中国,得到周总理和江青接见)。他本人作为一个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衰落过程中,以至彻底衰落后,不可思议地始终被普通读者及知识界认可和喜欢。一个处于社会中上阶层的英国人,伦敦人,半个世纪前,将炙手可热的都市文明抛在身后,住到了法国乡下,成为一名货真价实的国际主义者。

▲
黑豹党读毛选
从那一系列90大寿的采访以及影片中,看不出他的衰老,精神上和身体上都看不出,犀利、敏锐、英俊、充满魅力,就是比我记得的小了一号。但是,谁知道呢,这才几个月。
也许前面那个简单标签会让人误解,左派知识分子通常给人一种浪漫、热忱、激烈有余,而思考不足的印象。但伯格不是,真的不是。
就拿最近这一本,暂且称它为《风景谈》的书来说吧(“Landscapes: John Berger on Art”,国内的译本大概尚未出炉)。他最大的成就,在于写作,而伟大的写作源于思考,字里行间看到的是他对复杂事物长期而高强度的思考,看见的是头脑中各种思想的碾压和缠斗,最终,又并不仅仅终止于混乱和模糊,他把激烈缠斗后的思想精华,慷慨而清晰敏锐地分享给世界。

他对艺术和文化的清晰易懂的洞见,除了乔治·奥威尔,再无他人堪比。奥威尔成长于伊顿,成年后在缅甸做皇家警察,世界在他眼里是不可理喻,不对劲的,于是他穷尽一生想要搞明白。也许这是天生敏锐者的悲剧使命,他意识到不得不通过改变自己生活中的一切,来诚实地面对、梳理和写作。几十年以后,又出这么一个约翰·伯格,经历同样的转变。一个对艺术入迷的青年画家,在一个面对核战毁灭的年代,开始琢磨艺术的意义在哪里。
他的另一部书,1975年的《那个第七次出生的人》(A Seventh Man),这是一部关于季节性迁徙劳工的生存和工作状态的愤怒讲述,伴随了大量的瑞士摄影师约翰·摩瓦所拍摄的图片。40多年以后的今天,这部书仿佛还站在前沿。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写作和思考方式,在你以为清新文艺得不得了的题材下,比如谈风景、谈肖像、谈静物画(比如他的另一本书叫《一罐野花》[A Jar of Wild Flowers]),更多地,他在谈论政治暴力、镇压、恐怖主义和谋杀。并不太清新,也并不太静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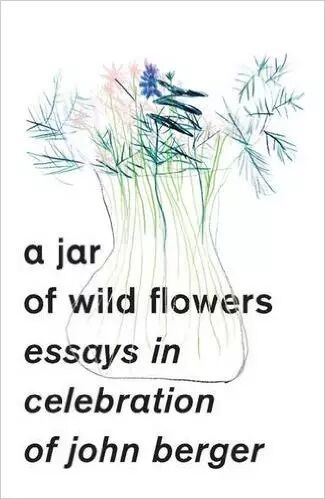
前文说到伯格身上并不具备那个标签所附带的特征。他怎么做到的,我想是最值得琢磨的一件事。首先,他是个天生的、终生的合作者。这不难理解,别忘了他是“艺术评论家”,也就是说,他的写作源于对话,他的思想火花迸发自别人的思想和作品,他一直都在努力去理解别人的画作,从别人的摄影、诗歌、雕塑、信件或者辩论中唤醒并折射出自己的思考。他是一个思考的大门永远敞开的作家。但你也并不能就此推论,他缺乏思想的深度和力度。
是的,强度和开放性,批判性思考与合作态度的对话,很难并行。
这就是伯格之所以宝贵。
2016年他有两本新书,前文提到我刚刚有幸拜读了的《风景谈》是一本,另一本“Lapwing and Fox”,便是基于他与友人的对话。
他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无需别人替他开脱,并不耻辱。他首先是个艺术评论作家,对他来说,他最关注的是画作中板结的土块、衣服上的皱褶、汤盆里飘出的味道,这是他的世界里的内容。而他对资本主义的厌憎,更多的不是代表理论,而是对现代世界的种种丑陋的厌恶,以及对自然的背离(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他提到过自己小时候对自然和自然形态的眷恋)。
这就回到那个纠缠了他一辈子的问题上来:艺术的意义在哪里。他在他的小说处女作《我们时代的画家》中,借小说主人公,一位流放中的匈牙利艺术家之口,抨击当代艺术的形式主义,认为艺术发展到今天,已经沦为商品,是富人之间用来进行财富流通的货币。这是个值得质疑的极端观点。艺术家的创新,无论到哪个年代,都值得期待,只是,我们都应该知道,它有多难。
伯格在四十年代后期放弃了油画创作,不过线条画却画了一辈子。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将艺术家的敏锐眼光与对人类历史的广泛理解结合得那样准确。作为作家,他的写作风格也许得益于他对绘画技能的把握:对颗粒的敏感,对线条和细微阴影的关注,因此在他的评论文章中,可以大笔一挥,将文艺复兴到当代艺术在一个段落里说得明白。此外,他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善于在细微处吹毛求疵,大作文章,引导读者发现自己过去完全忽略了的东西。比如开篇提及的《风景谈》,里边收录了他写立体派的小散文,文章短小精致,却有“啊,原来如此”这样的让人眼前豁然一亮之感,立体派就得不偏不倚出现在那一刻啊。更不乏凶巴巴地对美国抽象派表现主义的严厉批判,以及对当代画廊/美术馆文化的小幽默。

▲
画画的约翰·伯格
也许是偶然,也许是有意而为之,这部终于成为他遗作的书的亮点,是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克拉科夫》。文章独特而深邃,好像一封写给早期的老师的情书,其主旨在娓娓叙说中一点一点地散开,道出。读这篇堪称“美文”的文章,你会忍不住感叹:一篇好文章,一定有好的样貌。而《白鸟》一文,则明确打通了那个政治愤青伯格和柔和的艺术审美家伯格之间的通道:“
在这个魔鬼猖獗的苦难世界里,在我们感受不到自身存在的世界里,在这个我们必须要拒绝的世界里……是对美的审视给我们带来希望。当我们看见水晶或者罂粟花的美时,意味着我们并不孤独,我们深深地被种植在更广阔的存在中间。
”
这也许仍然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验性奇谈怪论,但这段话点醒了我,自己为什么喜欢他。是他让我相信,我们不孤独。
【注】
本文原标题为《我们都不孤独》
【作者简介】
黑爪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