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虹膜翻译组出品。希望加入虹膜翻译组请发信至[email protected]。
对电影业而言,性、金钱和死亡向来都是极具吸引力的概念——它们总能唤起灵肉间隐秘而禁断的愉悦,但在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的世界里,这些词汇却并非如此。

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
性爱和金钱纯属交易,生活充满绝望而循环往复,死亡也变得与之无异。人们利用他人也被人利用,而通常的成功标志(和谐的家庭、稳定的工作以及物质消费)最终看来也毫无意义。
通过《狐及其友》,法斯宾德将这一思潮展现得再彻底不过。随着影片剧情的发展,悲剧逐步加深,愚钝的主角渐渐走向死亡,他终究没能看清周围人肆意利用他的现实。

《狐及其友》
影片中,财富的无常和主角的感情坎坷完全一致,而人类作为社交动物,所有人都无药可救,无论你是利用他人,还是被人利用。
这位来自西德的导演自然明白这种阴郁的氛围最适合创作黑色幽默或者悲惨世界,而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也并非明晰:有什么比关乎生存本身的悲剧来得更为荒唐呢?比起看着某人跌入泥沼更为有趣或者恐怖的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扭动四肢,企图脱离困境。
《狐及其友》是导演的第22部长片,创作于他二十九岁的时候——大部分导演在这个年龄能有零星半部作品就已是幸运至极了——展现的是挣扎沉沦,直至灭亡的主题。这很有意思,甚至也很搞笑。

《狐及其友》
身处一个有着劣质毒品和私交甚为混乱的快时代,法斯宾德却抛出了系列巨作,大概,他希望通过《狐》强调权力的不平衡对于感情关系有着本质影响的观点,这在他早期的一些作品如《柏蒂娜的苦泪》和《玛尔塔》中皆有贯穿。
不过,该片让这个公开的双性恋导演首次将目光聚焦于同性恋者之间的情感互动,当然了,他们并不比导演的异性伴侣表现得更好。

《狐及其友》
不似法斯宾德早期情感泛滥式的纯粹产物《当心圣妓》和《四季商人》,《狐》以冷静的视角走近一个天真的乐透大奖赢家,叙写他最终落破潦倒的苦情故事。
主角弗朗茨(昵称福克斯,即片名中的「狐」)由法斯宾德本人扮演,如同他的第一部作品《爱比死更冷》,主角的名字来自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写于1929年的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的愚蠢前科犯,因为这部作品对他影响巨大。
不同于罪性未泯的犯人,弗朗茨在《狐》中属于工人阶级,平时是一个漫无人生目标的男妓,有时也在嘉年华上揽工。(在影片开头,他暂时负责表演嘉年华制造噱头的附加吸睛项目《福克斯,会说话的头》,这个头能和身体分离却依然侃侃而谈,我们都知道,这极好地象征了他思想和下半身的分离。)警察查封嘉年华以后,弗朗茨像日常一样买了乐透奖,不久就中了50万马克——不出意外地,他混进一个高雅时髦(「世故」双关词)的新团体,正是他步入中年的「老司机叔叔」(同性恋文化中开车搭男妓回家的成熟有为的男子)麦克斯(由卡尔海因茨伯姆饰演,他直勾勾的眼神你一定熟悉得恨不能忘记——他也出演过《偷窥狂》)所引见。这样一个高贵冷艳的精致男团,显然不是为了弗朗茨的幽默、高贵或聪明而来。

《狐及其友》
熟知法斯宾德的不羁生活和传奇的同时代观众一定会对他饰演弗朗茨时轻声细语的表现大为吃惊,除了穿上通过铆钉点缀出自己小名的衬衫而显得有些自信外,他没有任何招摇的表现。一张娃娃脸,身材又很纤细,法斯宾德扮演的弗朗茨透露着痛苦的无辜,让你充满保护欲,如果他有什么值得保护的话。
就法斯宾德而言,扮演福克斯简直就是神来之笔,而对于我们,导演亮相屏幕意味着没有人在镜头后面与角色感同身受,而这种感觉来得如此强烈——福克斯表现得十分茫然无措,他所遭受的任何苛待似乎都像是自然社会法则造成的结果,而非什么严重的不公。

《狐及其友》
在影片的后续情节中,弗朗茨发现自己被人利用且抛弃后,并没有认命自己所该扮演的角色,而是与之挣扎对抗,他或许是固化的社会阶层的受害者,但在法斯宾德看来,福克斯相信通过金钱可以提升自己的低等阶级无疑是可笑的。这种价值观使得这部剧情片不同于诸如罗伯特·布莱松的《钱》等描述金钱如何万恶的作品。
布莱松认为,在一个内核已经彻底腐烂的固化体系里,人们无法可施;法斯宾德认为,悲剧在于,人们本可以选择抽身而退,免入泥沼,却常常义无反顾。
在众多娇贵的新「同志」朋友里,弗朗茨爱上了苗条纤细,留着长八字胡的欧根(彼得·夏托饰演),这让菲利普(法斯宾德的主用演员之一哈里·贝尔饰演)总是气急败坏(译注:他和欧根之前应属恋人关系)。

《狐及其友》
尽管欧根看上去对弗朗茨提不起什么「兴趣」,弗朗茨甚至粗鲁地穿着鞋子蹦上他的床,欧根还是在当晚和他共寝一室。法斯宾德对他们初夜的去情欲化处理足以让我们质疑这段克制关系的本质,同样的还有欧根带着这个无药可救的下民去到高冷法国餐厅的场景——对于弗朗茨选择比尔森啤酒和面条而不是红酒和甲鱼汤的偏好,他表现得羞愧不已。
这位新恋人究竟想从弗朗茨身上得到什么?当我们看到欧根的父亲(阿德里安·霍文饰演)时便明白了——这位厂长所经营的图书生产装订线曾一度辉煌,如今却面临着严重的资金流问题。受到所谓真爱的驱使,弗朗茨为欧根的父亲提供了10万马克的贷款,虽然他也在合同中增加了一条充满希望的条约,规定只要债务还清,他就会成为合伙人。
当律师大声朗读合同细节时,弗朗茨难敌睡意,似乎对这一纸胡言不自觉地有些抵触。

《狐及其友》
尽管这笔贷款在弗朗茨的奖金中占了相当大的份额,但欧根这伙人清楚地知道他的富余程度,花言巧语地引导弗朗茨投资不动产(欧根可是很想要一个豪华公寓!),购置时髦衬衣领带(菲利普可正巧开着一家店呢!)以及典雅的老式家具。(麦克斯可是卖古董的!)
巴洛克躺椅、镀金镜框、中国的丝绸地毯、奇彭代尔式的烛台:这样的消费在70年代的西德可是风光至极,毕竟60年代以来国民经济一直萎缩低迷,虽然二战后的50年代经济曾有过辉煌的表现。
尽管诸多物质挥霍,法斯宾德的执导实际上较为冷静,大体上摒弃了他早期浮夸作品中一直以来更为明目张胆的奢华影像。镜头只是耐心地等待和记录一切恶劣勾当的展开。

《狐及其友》
弗朗茨温顺随和,欧根却变本加厉地苦待他,强调他没有品位,不带他欣赏歌剧因为他「对此一窍不通」,只随便抛下一些空泛的安慰诸如「我们迟早会让你成为一个正常人的。」然而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弗朗茨遭受的是愈发去人类化的待遇,只等他与欧根分手——带着所剩无几的奖金,被迅速赶出这片虚假的天堂——才近乎结束。
还有最后羞辱的事情:在同性恋酒吧和一对美国士兵暧昧调情时,一人直接问弗朗茨:你卖多少钱?
《狐》上映后便引发部分人的愤怒,他们认为这是对同性恋文化和同性恋社区污名化的观点,因其描述暗示由男性朋友和情人构成的圈子全是肤浅、诈欺和物质。

《狐及其友》
比如,批评家安德鲁·布里顿曾于1976年在《幸存的基佬》中写道,它「对同性恋的描述让我们低人一等,应该严厉谴责。」在身份政治对于批评主义如此重要的现今,以及群体代表性作为流行文化的关键因素的情况下,这种电影解读依然未曾消失——它当然也不该消失:导演无处不在的犬儒主义思想无疑让描绘一个早已沦为嘲笑对象的团体深受污染。
对于他个人而言,法斯宾德否认影片有任何特指同性恋的意向。在1975年的戛纳电影节上,他说,「在这里,同性恋再正常不过,(真正)有问题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这是个爱情故事,一个人如何寻求另一个人的爱,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故事。」如果这么说显得有些不够坦诚的话,那么可以确定的是,本片关注的是爱情和社会不公这样的普世价值。

《狐及其友》
也许,比起影片所显露出的阴险肤浅与同性恋的相关性更为有趣的是,这些同性恋者接受并推动了一个更大的文化所划分的阶级,尽管仍受到它的压迫和边缘化。
最终,《狐》囊括了一种严厉的社会批评——针对那种为了维护既得地位而愿意自相残杀的群体——这点在影片后期欧根和弗朗茨一次去往马拉喀什的旅行(当然是弗朗茨花钱)中显得尤甚。
他们穿着招摇的白衬衫在集市漫游时,遇到了一个健硕硬朗的当地人(艾尔·海蒂·本·塞伦饰),他是突尼斯来的打工移民,法斯宾德在澡堂里遇见他,两人开始了一段纠缠痛苦的情事,后来为他拍摄了令人难忘的中年妇女的爱侣——《阿里:恐惧吞噬灵魂》中的男主。
在交换几个意味深长的目光之后,本·塞伦所饰演的角色接受了另外两人的邀请,一起回到所住的国际度假客栈。正值进门之际,旅馆经理拦下了他们,不允许本·塞伦进入,因为阿拉伯人不可入内。欧根指出了他的双标:旅馆经理本人也是阿拉伯人。他很惊讶,一个群体可以因为主流社会的压力评判并驱逐自己的成员;显然法斯宾德不是这样。

《狐及其友》
法斯宾德描写摩洛哥的场景是为了给本·塞伦一个角色,后来他在酒吧里捅了三个人后就逃离了德国。虽然如此,《狐》却是献给他后来的男朋友的——工人阶级的阿尔门·迈尔,据说他们一起像电影中夸张的那样和不同阶级的人炮制了类似的关系。
因此,《狐》被视为一种撕开面具式的自我批评,法斯宾德在其中交代了自己轻视和利用他人的倾向。
多年之后,两人分手,迈尔自觉无缘于法斯宾德的人生,在这位导演的生辰之日选择了自杀。而本·塞伦则在一年前死于一个法国监狱。台前幕后,爱恨生死都与法斯宾德的事业交织在一起。
《狐》最后呈现的景象无比悲惨:弗朗茨面朝地板,躺在肮脏的地铁站里。他的身体被生前的两位熟人踩过,钱包和他最爱的铆钉夹克被几个小孩尽数偷去——显然,他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金钱虽然买不到爱情、快乐或自由,却能购买安眠药。
生活便是如此可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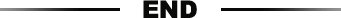
往期精彩内容
明星号召力对电影票房有多大的影响?定量分析来了
从周润发到吴亦凡,这小鲜肉时代真的在世风日下?
如果你只想当一个电影明星,那你已经落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