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声明两点:
我不是学法律的,我不懂法律;作为一个弱者,我对杀死辱母者的于欢完全持同情态度,支持重审此案。
既然这样,那我还想说什么呢?
我是想讨论一个问题,很多人在说这个判决体现了法律的无情或者法官的无情,看起来的确是这样,一个似乎普通人都能辨识的是非,法官为什么要做出如此判决,把自己放到民众公敌的位置呢?法官就不是正常人,没有普通人的判断能力吗?

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我的道理一般都是从生活常识导出。
十几年前,我在《法治中国》栏目兼任评委。记者的节目能否过关,一般由我和一位最高检的人士决定。我从电视的角度把握节目的艺术性,最高检的那位从法律的角度把握法律上有无瑕疵。
很快,几乎所有的记者都站到了我这一边,我看着很不错的案例,往往被那位检察官说得一无是处,他总能找到某个细节后面法律逻辑的不严密。
我很佩服他的专业性。从法律的角度看,他说的99%有道理,但我们仍然没有办法按他的要求操作节目,那样的话会把节目搞得像一个判例教科书,我们的故事完全无法展开,可能在第一个证据的调查中就迷失了方向。我一次一次地跟他解释,这是一个电视节目,不是法庭调查,我们要的是在情节的感染中让人明白法治的道理,我们并不是调查案件的警察。
从那时起,我就领教了
法律思维与常规思维的不同
。
我百度了一下,看到了这么一段——
法律思维是
法律职业者的特定从业思维方式,是法律人在决策过程中按照法律的逻辑,来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考模式,或叫思维方式。
一位普通人看到钟表不走了,可能会说“这只钟表坏了”,但一位法官或律师看到钟表不走了,只会说“这只表不走了”,绝不会说“这只表坏了”。这就是普通人与法律人思维的不同。
从这段话里你看出了什么?
法律思维是超出情感反应和常情道理的一种独特判断,它和我们一般人基于常情常理的判断不一样。
“清官乱断家务事”,现实中的纷争是全息的、纷乱的,我们对它的判断使用的是情感逻辑和常规事理,这种判断有对的时候,也有不对的时候。
比如你的亲人被人打了,从情感上我们肯定站在亲人一边。但有旁观者说,你的亲人之所以挨打是因为他踩了人一脚还不认错,这就上升到讲理的层次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道理讲不清,就只好诉诸法律,法官会基于最毫无疑问的事实,最没有缺失的证据链,最简单明确的是非判断(法律条文)来判断问题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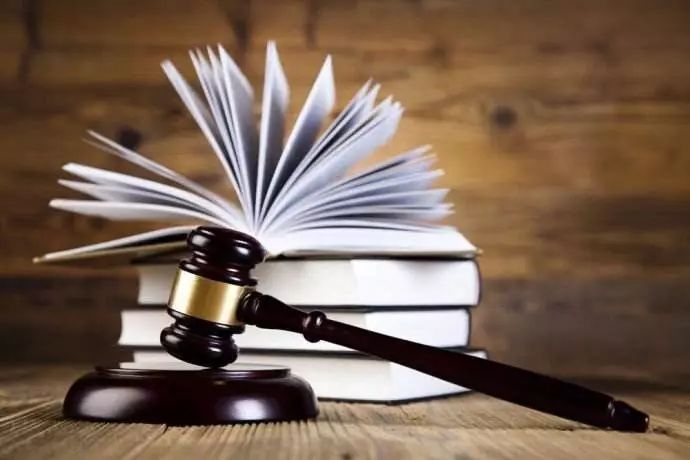
法律是经过筛选的人情,经过提炼的道理,它来自人情道理,但不同于一般的人情道理。
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逻辑:
情感的反应是第一层楼,道理是第二层楼,法律是第三层楼,第一层筛选后进入第二层,第二层筛选后进入第三层,第三层的东西跟第一层绝对不一样;
这个逐层筛选的过程是按照最保守、最明确、最简化的原则来进行的,以便法律工作者能够根据尽量简明的原则来判断是非,做到“清官能断家务事”;
这个提料的过程完全有被“污染”、歪曲的可能。
打个拙劣的笔法。这个过程有点像把苹果打成浆,在提炼出维生素,维生素来自苹果,但我们在吃维生素时不是在吃苹果。
在我们这些法律的外行看来,于欢杀人案一审判决不能接受的地方在于一个关键点:我们认为那杜志浩的兽行已经超出了正常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任何反击都是合理的,这是我们按照常情常理做出的判断。而
法官根据法律思维认为,这种行为不是正当防卫,因为于欢的生命并没有受到威胁。

从法律思维的角度看,法官错了吗?他可能说他没错,但我们说他错了。
法官错在哪里?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再提炼、再抽象也要基于人性,也要基于我们挂在墙上的那些核心价值观。法律再专业,它仍然是在讲人间的道理,而不是讲非洲大草原上狮群的道理。
如果一个法律的判断在技术上是正确的,但在最终判决上违背了常情常理和核心价值观,那就是歧路亡羊,那就是在将苹果提炼成维生素的过程中变成了有毒药品。苹果可以提炼维生素,但我们总不能说提炼出来的东西可以于身体有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