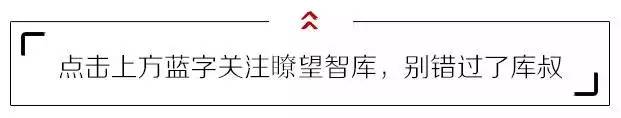

最近,有两件大事。
第一,15日,习近平将开始新年首访。这次他要去瑞士访问,之后参加达沃斯论坛(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参加),再去联合国日内瓦总部。
第二,20号,特朗普正式上任。
这两件事,都关系到世界上最重要的一项议题:全球化。特朗普自不必说,从竞选到现在,诸多的言论、政策,都与反全球化有关,诸如贸易保护、边境修墙、控制移民等;而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看来,在过去30多年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是显著的受益者之一。
除了特朗普上台,2016年,也有很多反全球化式的“黑天鹅事件”,包括英国脱欧、全球范围内的右翼思潮回潮等。人们之所以这么关注这些事件,是因为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宏观背景下,这些保守的甚至是极右的观念和做法,可能给世界政治经济都带来更深刻的不确定性,甚至引发更大的动荡。
也正因此,外界才会如此关注中美——毕竟这是全球化的两大支柱国家。两国元首会怎么做,谁能继续扛起全球化、自由贸易的大旗,势必是2017年最有看点的重大事件,也将深刻地影响未来的历史走向。
带着这样的认识,侠客岛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他也带来了许多有见地的洞解。下面是谈话实录。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侠客岛”(ID:xiake_island),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问:2016年,人们谈得最多的就是“全球化水平的倒退”。这种倒退体现在哪些方面?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格局力量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郑永年:
全球化有进有退,历史上是发生过的。2016年开始的“全球化倒退”,我个人的担心主要是结构性的。
这是大的形态的退化,不是一般性的起伏。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现在说的全球化,指的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那一波全球化,是由西方,尤其是美国推动的全球化。它由资本和政府这两种力量推动。当然了,还有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参与,但主要是西方力量。
现在担心在哪里?是它的主导力量,也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开始退缩了。美国和西方现在不但不能继续对全球化起到领头羊的作用,而且大家都去搞贸易保护主义了——这对世界经济、对全球化的冲击,是结构性的冲击,非常严重。
这种结构性的冲击在一战、二战前都发生过。这一次有点类似。但现在,贸易保护主义在那么多的西方国家成为主流,大面积地衰退,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更深刻的地方在于,
现在从美国到欧洲,反全球化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已经形成了。
虽然反全球化从很多年前就一直存在,但之前只是一种社会思潮。政治人物是“不管你(社会上的声音)怎么反对,我都要推进全球化”。但是现在,逆全球化成了政治思潮,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都有。这很关键。
问:为什么会有如此大面积的衰退?我们觉得,很多跟其国内产生的问题有关,比如财富分配不均、精英和民众分离等等。中国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郑永年:
是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波全球化,的确产生了很多问题。
它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是财富的只是流到了一些国家、和极少数人手中。社会分化、收入分配,再加上技术因素造成的工作机会的流失,在各国都有,包括中国本身。我们现在的收入分配也是受全球化影响的。
这个是关键。一战、二战,都是西方国家内部出现问题。内部的问题转化成国家间的战争。现在西方也是这样,因为内部问题,才转化成外部的贸易保护主义。
当然,贸易保护主义只是第一步,以后解决不好的的话,地缘冲突也可能发生。这是世界历史的逻辑。
中国也一样。一方面,我们要推进全球化,做领头羊,但主体还是国内发展和建设。中国领导人很多年前就说,
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首先把国内搞好。
这一点到今天也没有变化,而且永远不会变化。国内搞不好的话,绝对做不了国际的领头羊。
从这一点上说,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一波全球化,中国确实获得了好处,但是国内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包括成为世界加工厂后带来的污染问题等等,都非常棘手。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把国内的改革推进下去,把发展搞好。我们的政策、目标、口号都有了,但要把这些改革落实下去,否则外部的全球化很难支撑。
道理很简单,没有内部的继续发展,哪有外部的加速崛起?外部的崛起,完全取决于国内可持续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关系要搞清楚。
问:特朗普就要上任了。怎么看他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郑永年:
如果是像特朗普所说所做,要通过贸易保护主义解决经济问题,那可能近期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一些正面影响;但如果从长远讲,反而对世界经济会产生衰退性的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
全球化不仅是国家间的贸易、投资,还是一种公共产品(Public Good)。
全球化体制下,各种的全球生产要素都在流动,一下子刹车停下来,要素就都不能流动,这个影响是全球性的。
现在世界经济变得非常复杂,以前中美贸易只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但是现在呢,中国出口给美国的一个产品,可能是几十个国家生产的,中国可能就是组装一下。很多零件都是日本、韩国或者东南亚国家生产的。所以中美贸易受损会影响到很多国家。
更重要的是,中国加入了全球化贸易体制后,成为了一个很大的推动者。中国的经济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还加入了很多西方的,比如西方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如果搞贸易保护主义,收这么高关税的话,不仅仅会影响到中国经济,也会影响到美国经济。
这些复杂的因素,我想特朗普的团队还远远没有考虑到。特朗普是个地产商,是一个传统的商人,他还是以一种传统思维来看全球贸易。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看到了这一点,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会促使全球经济发生比较大的衰退。
特朗普看到了贫富差距、制造业空心化等问题,但是他的手段是错误的。
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要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解决,更需要通过国际合作,用新型的全球化来解决这些老的全球化产生的问题。要通过继续全球化、继续发展来解决问题。
从这点来说,中国的态度和做法对世界下一步发展是很重要的。
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是世界的两个支柱。
如果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也针锋相对搞贸易保护主义,那世界经济体系就彻底就完蛋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习近平此次出席达沃斯论坛充满期待的原因。
问:最近几年,我们明显感觉到中国越来越主动地去维护自己的主权利益,显示军事存在,外界也有不少质疑,认为这种行动不是和平崛起的态度。该怎么平衡这一点?
郑永年:
不矛盾。主要矛盾是,话语上我们没解释清楚。我非常认同一位哈佛教授的说法: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军事行动,不是去挑战世界秩序,而是巩固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
这是两码事。这个军事现代化,并不是要挑战现有的秩序,而是正大光明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的国防力量体现在防卫意义上,而不是扩张。
说来说去,中国的军事动作也主要体现在南海问题上,这是中国在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主权利益,而且中国是反应性的。越南、菲律宾都在做,中国一做,就说你是大国,人家是小国,大国欺负小国?没这个道理。西方有人故意误解,但有些人看得很清楚,知道中国不是要挑衅。
即使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也一直强调,航行自由没有问题,这是美国的利益,也是中国的利益。中国85%的海上贸易都要经过这里,怎么会去影响航行自由?我要做的只是保护自己的岛礁,保护自己主权的利益。
西方的帝国主义,像马克思列宁所说的,到处在全球占领人家的土地,驻军,也是跟他的经济利益相关。中国也要思考,当我们走向全球的时候,怎样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如果不走西方的老路,中国走什么样的路?尤其是海上的航道安全,海盗要不要防呢?这些都要考虑到。
像中国在吉布提建基地,还是需要的。这不是驻军,而是海上力量补给、供给的地方。这些中国的舆论有点扭扭捏捏,我觉得是光明正大可以说的东西。西方国家现在全球有多少驻军? 中国除了维和部队还在哪个国家驻军了?没有。
所以,不说清楚反而被人猜疑。我们不是做错了,而是我们没有话语权。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推进全球化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问:您觉得习主席在达沃斯的讲话可能会突出哪些方面?未来中国将在全球化上提供怎样的中国方案?
郑永年:
首先是结构。全球化是公共产品,贸易体制是公共产品,在美国不能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时候,中国能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这是首要的问题。
其次是政策。全球化、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一个世界的自由经济秩序,确实对每个国家都有好处。至于国内收入分配不公平,那是国内体制改革的问题。但是自由贸易,几百年来确实是一种很好的体制,每个国家都能共赢。我们要考虑的是,中国跟现在国际自由贸易体制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公共产品,对哪个国家都会有利。以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作为一种制度,还是有利于各个国家的。中国要处理好跟自由秩序、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西方扛不动自由贸易的大旗的时候,中国接过来扛下去就行,没必要纠结于那么多的意识形态。
西方早期推进全球贸易是非常赤裸裸的、暴力的,首先是殖民主义,后来搞帝国主义,用船坚炮利打开其他国家的门户。以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走不下去的时候,西方就在二战以后确立了今天这个秩序。尽管我觉得这套秩序、制度是西方建立起来的,但是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公共产品。所以中国首先是要维持这套公共产品。
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这么做的,叫接轨,而不是另起炉灶。第二点,中国要在这个体制里改革这个体制,做一个改革者。
第三步很重要,中国能提供什么样新的体制来补充?这几年,一带一路、AIIB、金砖银行,都是让大家看到中国吸收了以前全球贸易体制的规范和规则,只是这次是中国主导罢了。这是中国推进全球化的重要抓手。

中国一吸收,二改革,三创造,我们要向世界说清楚。
我们承认,全球化确实产生了问题,同时也要指出,像特朗普还有欧洲的这些贸易保护主义不是解决方式。我们要提出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这就是大家期待的。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旦西方意识到他们还要继续引领全球化的时候,你很难在这个体制里面往上爬。当西方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国的机会就来了。美国当年的运气实在太好了,欧洲在一战、二战的时候,互相之间打得不可开交,后来就等于邀请美国来,你可以当世界老大了。现在也不是说西方在邀请,而是现在确实是缺少领军国家、领头羊。所以中国完全可以在这种形势下,考虑怎么样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附文:
郑永年:特朗普与逆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
文︱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ID:IPP-REVIEW),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开始讨论逆全球化对国际安全的可能影响。这个重要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如果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出现逆转,这种逆转对西方所建立起来的全球安全秩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二,如果中国成为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又会对全球安全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提出这些问题并非毫无道理。无可否认,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尽管其它大部分国家也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但它们毕竟是配角或参与者。同样,今天的国际安全体系是近代以来西方力量主导下的全球化产物。经济全球化是国际安全体系形成的重要因素。全球安全体系的形成和维持与西方力量在全球的扩张密不可分。也就是说,西方建立全球安全体系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其全球经济利益。
很多迹象显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衰退。
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长开始低于全球经济增长。
在意识形态层面,因为1980年代以来的这一波全球化,导致了各国收入差异的急剧扩大和社会分化,西方社会开始怀疑自由贸易,民粹主义已经崛起。这也已经影响到西方的政治人物对全球化的态度。自由贸易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西方视为其软力量的核心之一,政治人物言必称“自由贸易”;但今天为了迎合快速崛起的民粹主义,“自由贸易”已经变成负面的概念,甚至是一个肮脏的词汇。这已经深刻地影响到西方各国的内部政治。英国公投脱欧、德国右派选择党的崛起、法国右派国民阵线的扩张、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无一不是标榜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全球化的另一产物)的。
出现地缘政治问题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逆全球化的同时,世界各地地缘政治日渐重要。美国在中东力量的衰退,使得中东出现权力真空,不仅导致了中东秩序乱局,导致了大规模的难民潮,也导致了大国之间(主要是美俄)的竞争。亚洲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好、最稳定的领域,但随着美国所谓的“重返亚洲”,地缘政治竞争也越演越烈,东海钓鱼岛、南海岛礁主权争议等问题,本来只是有关国家之间的双边问题,和美国毫无关联,但因为美国的介入,就演变成为地缘政治竞争问题。
即使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也开始出现地缘政治问题。东欧表现得很明显。苏联解体之后,东欧落入西方的怀抱,北约东扩本来已经挤压了俄国的地缘政治空间,导致了俄国伺机反扑(例如制造克里米亚危机)。民主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深刻矛盾,更是强化着那里的地缘政治气氛。长期以来,西方关切的只是那里的民主政治发展和地缘政治问题(亲西方),而非那里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但无论是对当地的政府还是老百姓来说,民主固然重要,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因为这攸关他们的切身利益。要发展社会经济,这些国家就必须寻求除了西方之外的发展动力,尤其是中国。但西方对中国在那里的发展,保持高度的地缘政治警惕。
无论是西方内部的民粹主义还是外部的地缘政治,已经对全球化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即逆全球化。这种逆全球化会不会对国际安全体系产生负面的影响呢?一些人已经提出了“1930年代陷阱”的概念。二战之前,西方各国内部民粹主义崛起,表现在外部便是民族主义,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地缘政治竞争,最终演变成各国之间的对外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
使人欣慰的是,今天地缘政治的变动主因是西方,而在西方及其势力范围之外,地缘政治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不是主线。
再者,新崛起的大国中国本身并没有类似西方那样的地缘政治概念,同时也具有了足够的能力,来遏止西方的地缘政治竞争。
西方作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出现了逆转,并不是说全球化的终结或死亡。以中国和印度等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充满着全球化的动力。
尤其是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化的领头羊。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长下行,但较之其他国家,增长速度仍然很高。如果中国在今后十来年里能够维持6%至7%的增长,势必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也是今天全球最大的贸易大国。经济的继续增长必然会继续扩大内部中产阶级的规模,这使得中国有条件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家。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所具有的推动全球化的动机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