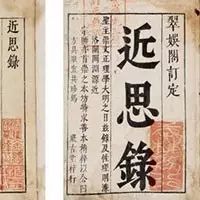放眼全球,能够对气候变化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各方势力中,美国是唯一唯二的存在。因此,谁将主宰白宫权力也将直接冲击世界能源格局。
刚刚得以重返白宫的特朗普,在气候问题上的全球“口碑”并不好。在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内,曾经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决然退出《巴黎协定》。
事实上,尽管还没有搬进白宫开始主政,一贯鼎力支持油气并对新能源持保留意见的特朗普,已经在静悄悄布局气候能源的“颜色革命”了。
近期两项重要人事任命值得关注。美国当地时间11月11日,特朗普宣布了一项人事任命,将提名前共和党众议员李·泽尔丁(Lee Zeldin)出任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署长。

作为著名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泽尔丁随后在Fox News新闻节目中表示,他上任后将迅速撤销环保法规,
“在第一天和前100天里,我们将有机会撤销那些使企业陷入困境的法规”。

克里斯·赖特(中)
一周后,特朗普又提名了下一届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Chris Wright),
并表示将设立国家能源委员会来推动美国的能源生产。克里斯·赖特现任一家油田服务公司CEO,他一贯的主张是“化石燃料对促进经济繁荣和摆脱贫困至关重要”。
这场山雨欲来的特朗普“旋风”,无疑将给中国新能源企业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
这主要基于两个事实:
一是作为“大买家”,美国是中国新能源企业重要的出口、出海目的地;二是特朗普的
气候能源政策还将搅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棋局,这将进一步影响各国的新能源采购。
凡事预则立,面对特朗普的施政冲击波,中国新能源企业需要做出哪些准备并制定相应预案,在全球范围内去调整贸易与出海布局呢?
特朗普关于气变的三重“冲击波”

继任者特朗普在传统能源与清洁能源上的态度,他会怎么改变拜登政府能源气候政策的“颜色”。还会不会如当年“退群”一般激进。将直接影响全球气候行动进程。
第一,特朗普会不会废除《削减通胀法案》IRA?
拜登政府任期内,在气候行动上堪称积极:在重返《巴黎协定》后,拜登提出了美国版“3550”目标,即到2035年通过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实现电力脱碳,到2050年全面实现净零排放。
为此,2022年8月,拜登还签署了《削减通胀法案》,该法案规划了总计3700亿美元的补贴和税收优惠,用于全面扶持美国本土电动汽车、光伏、风能、核能、储能和氢能等一揽子清洁能源产业。法案还带动各大公司宣布在美国投资900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和制造业。
而在本届大选期间,特朗普多次抨击民主党为应对气候变化出台的政策为所谓的“绿色新骗局”,并承诺
将改变美国当前的能源、气候政策方向,大力支持美国国内的化石能源开采,削减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的资金。
共和党反对拜登的气变政策,强调能源与电力的“可负担性”,倾向于支持经济性更优的传统能源。而特朗普则更进一步,他认为新能源还远不够成熟,因而在竞选中承诺大力支持油气行业。
第二,特朗普十分执着于油气出口。
由于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特朗普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国家,能够大量购买美国油气产品。2023年,美国首度成为全球第一大LNG出口国。
2024年1月,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由,拜登冻结了LNG项目出口审批程序。而特朗普势将扭转这一局面。
第三,特朗普冲击波,其关税政策也将是重头戏。
特朗普先后两度崛起,与逆全球化浪潮,或者说民粹主义有着根本关联。
近些年来,美国“铁锈地带”蓝领工人反全球化声浪一浪高似一浪,他们认为是进口商品以及外国移民让他们丢掉了饭碗。特朗普于是就顺势提出“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竞选口号,主张严厉收紧移民政策,并在国际贸易中对外国商品收取高额关税,普遍征收20%的关税,对中国则要征收60%的高关税。
不能幼稚地以为特朗普的关税主张仅是“竞选口号”。
特朗普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口号背后,有着一整套纲领,核心则是“给美国企业减税”。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美国企业所得税已经从以前的35%降至21%;未来他希望将这一税率进一步降至15%。
给企业减税,那美国政府居高不下的债务又要怎么去解决呢?
特朗普开出的政策“配方”是,对进口商品征税,用于弥补财政赤字,进而为国内降税创造空间。对这一税收“组合拳”,特朗普深信不疑。
因此,特朗普的关税魔咒,势必会继续影响对中国新能源出口,只是程度问题了。
左右为难的欧洲

某种程度上而言,
全球气候能源政治就是一场中美欧“三国杀”,或者说是一个中美欧战略“大三角”。
好的方面是,特朗普的民粹主义,“粹”起来是不分对象的。特朗普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旗高征关税,就是对欧日韩等铁杆盟友,也是不肯含糊的。
加之在“美国优先”理念下,特朗普早就扬言让北约的欧洲伙伴多出钱甚至以美国退出北约相要挟,俄乌战争狼烟未熄,这让美国的欧洲伙伴深感不安。
在这样的战略大环境下,出于为了牵掣平衡特朗普疯狂举动的考量,欧洲是有着对华接触的意愿和需要的。而在气候能源政策方面,资源匮乏的欧洲又只能将能源转型进行到底。
在全球化以及气候能源领域,中欧本来是有共同语言与合作条件的。
但事实上,一手与中国产业界保持合作,一手为了保护本土产业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对华恐惧心理作祟,欧洲还是在新能源贸易领域单方面对华发起了贸易战。
影响最大的一项贸易制裁,即今年10月29日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征为期五年的正式反补贴关税。这是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终裁结果,认定中国产电动汽车受益于不公平的补贴,这些产品大量进口会伤害欧盟汽车行业。
除电动汽车之外,针对风机、光伏组件、储能电芯、制氢电解槽等产品,
欧洲国家也是一方面需要优质低价的中国产品,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新能源产品保持着高度戒惧心理。欧盟委员会还将这种戒惧心理命名为“去风险”。
所谓的欧盟对华“去风险”,表面上的理由是欧洲国家需要保护本土企业,保护本土就业,在相关产业尤其是战略新兴产业方面不能够过于依赖中国,否则日后就容易被中国“卡脖子”。
而实际上,欧盟对华去风险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还是对日益恶化的中美关系的担忧。
欧洲一直以来执着于全球战略均势。在欧洲看来,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将会逐渐上升,两强角力之际,欧洲需要完成“去风险”,也就是说届时需要在欧美之间保持某种独立性;同时,
由于在安全方面以及油气供应等方面,欧洲十分依赖美国,一旦美国要求欧洲选边站队,那个时候欧洲至少要保持“不过于依赖中国”。
基于这样的三角关系,尽管欧洲一直会是中国新能源企业重要的贸易首选地,但是,指望欧洲毫无顾忌对中国新能源产品洞开贸易之门,是不切实际的。
虽然性质上与美国对我国的新能源封锁不同,但欧洲也一样在助长贸易保护主义。
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还体现在动议中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也即碳关税方面。事实上,近些年来,面对强大得多的中美,欧洲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得很严重。欧洲认为,欧洲企业竞争力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的环保标准高,这在贸易中是不公平的。因此,欧洲需要针对中国企业征收碳关税。
目前,中国国内企业对欧盟征收碳关税的决心,还是有所低估的。
中国新能源企业如何“见招拆招”

特朗普重新执政后,尽管全球能源转型进程会阶段性受挫、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会大幅抬头,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会抬头,但大多数声音并不认为,这些压力能够“压垮”强大的中国新能源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