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少女小渔》到《小姨多鹤》,从《金陵十三钗》到《陆犯焉识》,如果要挑一位最受电影圈欢迎的当代作家,严歌苓当之无愧。她的小说画面感极强,加之对时代的敏锐观察,每次基于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都能收获票房口碑的双丰收。
最近,严歌苓推出了新作《芳华》,由冯小刚执导的同名电影也已经开拍,预计今年就能跟观众见面。严歌苓是个多产的作家,却不是一个在媒体上经常发声的作家,此次借着新作《芳华》出版的契机,我们有机会跟严歌苓聊了聊她的小说创作与她对时代的观察。
严歌苓坦诚,《芳华》是她写得最诚实的一本书。如今这个时代,做任何事情都讲究快。不仅搞建设要快,做工作要快,就连谈恋爱,也要快。在这个没有情书的年代,我们对爱情的想象力也越来越苍白。《芳华》却讲述了一个并不着急的时代里,一个并不着急的故事。我们的时代一切都很快,成熟很快,盛放很快,然而如此发展,凋谢也会很快。如何能不那么着急,不那么快?在严歌苓的言语文字之间,或许我们能放松片刻。
严歌苓:
这个时代不可恨,只是缺少诗意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张畅
严歌苓,生于1958年,著名旅美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代表作《陆犯焉识》《小姨多鹤》《扶桑》《床畔》《金陵十三钗》等。

腿还没有抬到最高的时候,摄影干事抓拍下这张照片。严歌苓穿军装跳舞的照片没留下几张,那时部队有严格的纪律:除了正式演出之外,不能随便穿演出服装照相。这张照片中的严歌苓,正值二八年华,脸上还带着婴儿肥。
从1971年12岁入伍,到25岁部队裁军退伍,严歌苓在军队足足待了十三年,整整跳了八年的舞。之后,军队生活被她“反复咀嚼”,揉进一部又一部作品里,从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到《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谁家有女初长成》,再到后来的《灰舞鞋》、《白麻雀》,每隔一段时间,严歌苓就会想起部队文工团里的某个人,然后围绕这个人写一部小说。“那段生活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它左右着我一生的走向。”
去年4月,严歌苓完成新作《芳华》的初稿,那时书名还叫《你触摸了我》,小说围绕上世纪七十年代西南部城市某部队文工团中,男兵刘峰因“触摸事件”被处理的一系列情节展开。与之前的作品不同,新作《芳华》具有浓厚的个人自传色彩:“所有的心理体验都是非常诚实的,这本书应该说是我最诚实的一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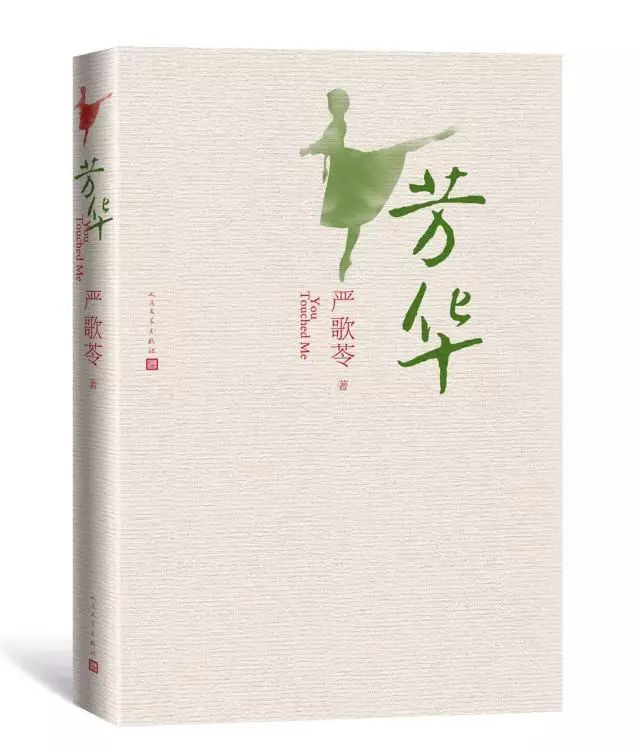
《芳华》
作者:严歌苓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4月
同样在年轻时有过部队文工团经历的冯小刚,在看过这个故事后,当即决定将它搬上大银幕。几天前,导演冯小刚邀请编剧严歌苓观看初剪后的《芳华》,严歌苓看着看着,就掉了眼泪。她说:“看这个电影,好像在看别人的故事。”
或许是因为时代和生活的脚步越来越快,回想自己从前的事,总像看别人的故事。严歌苓感慨,“生活来不及品味,一天就匆匆过去了”,“现在没有人喜欢诗了,觉得写诗、读诗挺没用的,有用的事还来不及干”。自90年代移居美国,虽然至今也不过二三十年,她却常感觉时空的错位,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什么,他们怎么谈恋爱,怎么说话,怎么与人相处。在国外,她偶尔见到的华侨,至今仍保持着八十年代出国时的状态,穿着、举止、思想都是,“好像给冻住了,智慧、生活都在那个时代冻住了”。
长达两个半小时的采访中,严歌苓始终保持同一种坐姿,身体远离椅背,后背挺得笔直,几乎能想象她当年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样子。采访结束,她起身,略微歉疚地说:“我不怎么会讲的。”然后开始关心起采访过她的记者的近况、编辑的咳嗽。在一部部作品中,她就像这样,时刻关心所处的世界,关心这个世界中的人,不断追问没有结果的答案。
写反思
“不停问自己:有没有诚实地写?”
作为一名职业作家,严歌苓是出了名的认真。
写《陆犯焉识》时,为了写好陆焉识在西北大荒草漠上二十年的劳动改造,她花了很多钱去青海体验生活。写以中原农村为背景的《第九个寡妇》,她特地到农村去住,看农民怎么起红薯,怎么摘棉花,她一直记得一次上厕所的时候,一队人排在她后面,一个小姑娘搓着作业纸站在她面前,一脸急不可耐。写《小姨多鹤》,为了了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和心理活动,她住进了日本长野的一个村子,看到了日本老人是如何跪着端来茶和食品,又如何退着走出去,多鹤的倔强和温柔才有了眉目。写《老师好美》,为了进入高中生的语言系统,五六年间,她几次跑到北京的一所中学做起了旁听生,“卧底是非常难的,人家把中学生组织得特别好,很难看到真相”。写《妈阁是座城》,为了写好赌徒的心理细节,她又跑到澳门,当起了赌徒,结果一路猛输下去,赌徒没当成,却成了一个失败的赌客。
这一次,严歌苓终于不必费力创造和想象细节,而是无比自然地回忆起文工团的老红楼、排练厅、练功房,还有那些让她感到“自责”的人和事,脑子里的地图一点点铺展,《芳华》就这样写成了。

冯小刚执导的同名电影《芳华》预告海报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年男女从大江南北挑选出来,进入部队文工团,担负军队文艺宣传的特殊使命。《芳华》的主角就是文工团里被公推为“模范标兵”的男兵刘峰,他任劳任怨,自觉承包了团里所有的脏活累活,原本在大家的需要和表扬中活得心满意足,并偷偷恋上独唱演员林丁丁。不想却在向她表白时被拒绝,并发生了所谓的“触摸事件”,得到与大家平时的“推崇”截然相反的反应。何小蔓则是刘峰的另一个极端,平时受尽侮辱和欺凌,却在荣誉到来时,精神失常。
《芳华》中,严歌苓反复追问:什么是好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善与恶之间的分野是什么?平凡是否意味着伟大?英雄的意义何在?“对那样一个英雄,我们曾经给了他很多的褒奖和赞美,最后却没有一个人把他当真正的活人去爱他、给他女性的爱。好像是很不负责任把所有荣誉都给你——谁让你做好人?”事实上,好人做尽的刘峰和受人欺辱的何小蔓各有其原型,严歌苓想要借此表达对两人的忏悔:“我从‘我们’当中走出来,来表达我们当时的集体来忏悔。”
如果剔除掉所有年代的元素,《芳华》讲的还是人性:“人性当中永远不可能消失不安感,你要结成集体迫害这个人的时候,其实是你转移了这个不安感。人对另外一个人施暴的时候,整个人群都在退化。”
自记事以来,严歌苓就始终在“乌央乌央、喧喧闹闹”的不断变化的大环境里:“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总是一个戏剧中心,总是能看到戏剧围绕着我在发生,我非常幸运地能够既是一个主角,又是一个很近的观察者。”
主角和观察者,两种身份在《芳华》中第一次合体,“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是所有的心理体验都是非常诚实的,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心里会不停问自己:有没有诚实地在写?”
写爱情
“那时的爱情,是盛大的节日”
“芳华”,冯小刚和严歌苓敲定这个名字后说:“‘芳’是芬芳、气味,‘华’是缤纷的色彩,非常有青春和美好的气息,很符合记忆中的美的印象。”除了反思时代外,《芳华》还着力写了青春荷尔蒙冲动下少男少女的懵懂感情:“那时候恋爱是件漫长的事,似乎滋味太好了,一下子吞咽首先要腻死,其次是舍不得,必须慢慢咂摸。”
慢慢咂摸,细细品味,曾经的爱情缓慢、持重、节制,正是这些特质,才使得小说中轰动一时的“触摸事件”真实可信。严歌苓对此颇有感触:“我觉得最理想的爱情,就是写情书,两个人用心去表达。情书都不会写、也没有这种交往,是不是很大的遗憾?爱情的各种段落,缺了很诗意的段落,那不很惨吗?”
1992年,严歌苓与美国外交官劳伦斯•沃克在旧金山结婚。结婚前,两人常互相以英文写情书。有一次,她在卧龙,发现红桦树的树皮很美,就在上面写了字,寄给他。她将情书看做是“一种白纸黑字的结盟”:“这种结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在潜意识里让你一次一次确认爱情。”
眼下,好像什么都图快,什么都在赶,短信、电邮取代了情书,爱情也没了质感:“在这个没有情书的年代,我对爱情的想象力非常苍白……那时,接到情书简直就是你的一个节日,特别私密而盛大的节日。现在这种可能都没有了,是不是爱情从生到灭的过程也就短了?”

冯小刚执导的同名电影《芳华》剧照
爱情如此,生活亦然,忙碌和快节奏成了常态。如今,严歌苓刚刚为BBC的一部动物电影写完解说词,同时创作和修改三个剧本,又要完成电视剧的脚本,她说自己这点随母亲:“一天发现自己没干什么有用的事,没让自己哪怕成长一点点,就慌。”为了不被打扰,她永远将手机放在厨房,摘菜或做饭的时候看上一眼,早上喝咖啡的时候统一回复,尽量让自己不被打扰,“我对这种方式的交流非常质疑,我坐在你对面,你不跟我交流,你和看不见的人交流,本身就很奇怪,起码是不尊重的。我跟你在一起,就要集中精力享受你的在场。”她说。
写作经验
“时空距离,把我从局中拔了出来”
1979年,八年舞蹈生涯结束,严歌苓做起了战地记者,采访了大量伤员和从前线撤下来的战士。她渐渐发现,舞蹈不足以表达自己,“原来在一个舞者的身体里还休眠着一个作家的人格”。调到部队创作组后,她以军旅作家的身份创作了长篇《绿血》和《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二十岁出头的严歌苓,从文字里找回了在舞蹈上丢失的自信。她飞快地写,一天能写上一万字,获奖的小说大多也是“一挥而就”。1990年秋天,严歌苓考上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的文学写作系,成为这个系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唯一一名外国学生。她至今都记得老师告诉她:Try to see it happen。日后,当她的作品陆续被拍成电影时,她将其中的画面感归因于那时的专业训练:用直觉去写,把小说写得视觉化。或许正是因此,《芳华》开始的几个场景像极了电影镜头的运动,“因为这个叙述人是全能的存在,收回来就是此人,放出去就是全知全能全方位的观察。一双眼睛代表所有人的眼睛,你想看到他的内心就看到内心,你想看到他的内裤就看到内裤。”对于严歌苓来说,“小说要更加有机,更有活力,更鲜活”,这是她对自己的要求。

严歌苓 摄影:周鹏
严歌苓坦诚自己是个“很激情的人”,常说一个故事“非写不可”、“不写就会死”:“一个创作者最大的幸事就是,你笔下的情节和人物忽然反过来惊喜到你——我没有设计,他怎么会这样说呢?——其实你当中埋了许许多多的逻辑在里面,到这时候他一定这么说,反而让你大吃一惊。这就是写作最棒的地方。”
为了体会如此“幸事”,严歌苓不断抽取、抽象着自己过往的生活,在海外反复咀嚼中国的故事也好,当下反复回视过去的故事也罢,都是为了拉开时空的距离,恰恰是这种距离,将她“从人在局中的状态拔出来,超越亲身体验本身”。
保持距离、抽离自我,也让她过着“吉普赛人的生活”,对什么都不信以为真,对什么都保有侧目而视的姿态。
“这个时代,一切都太快了,太昙花一现,出现的很快,成熟的很快,盛开的很快,怒放的很快,最后凋谢也会很快。”
“我不恨它,只是觉得太缺少诗意。”她说。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编辑:张婷。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