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之前先说个让人又想笑又无语的事情,大家知道前几天我们发的文章《从滴滴到隔离门,你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被删除了。应读者们要求,本来准备在今天第二条重发,结果在发送的时候,系统显示以下提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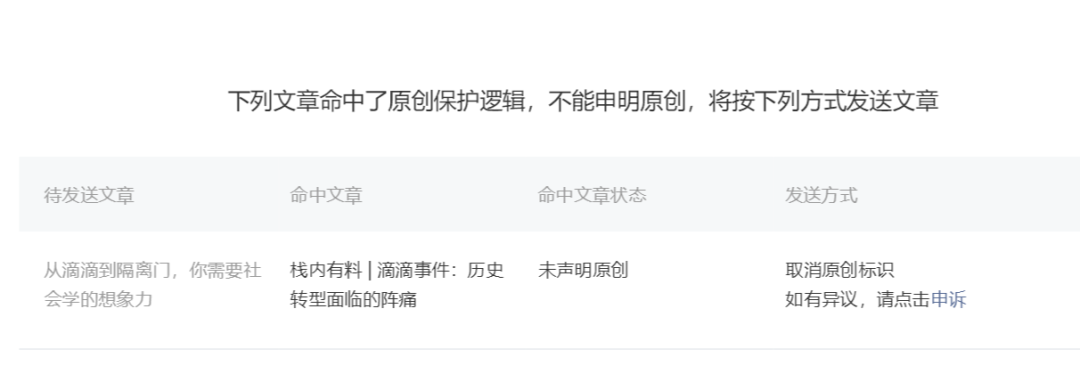
蒙了一会,我才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在我号的文被删除之后,这个号全文剽窃了该文然后以
《栈内有料 | 滴滴事件:历史转型面临的阵痛》
为题发布,并申请了原创保护。而公众号系统对于已被删除的文章,识别不了是已经发布的内容。所以该号得以申请原创保护。这个案例我前几天才看人说过,没想到这么快就碰到自己头上。
对于公众号生态来说,原创号本来就是很辛苦的事,业内有一大批靠着转载洗稿甚至抄袭都能活得很滋润的公众号。一般对于想转载我们文的,我们都很欢迎,也不会索取报酬。很多没有授权就转载的我们也不理会。但碰到今天这种情况,确实也让人很无语。如果这个号的相关负责人能看到的话,希望自觉点主动删除吧,别的不说了。
▽
在人类的近现代政治史上,大国在意识形态工程建构中都需要一种分别内外的标记,通过塑造共同体本身的特殊性来作为主体视角,并通过这个视角去重构外部世界的认知图绘,大国的内外之别,族群之辩实际上就是建构本国政治意识主体的通用法则。
比如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美国,其天命昭昭,例外主义某种程度是保守性质的公民文化下的身份边界,而其认同模式,
我们可以将其等同于于一种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
其他类似的例子还有英国的“国际社会”,法国人的共和想象,以及各种本国特殊论。
哈贝马斯在《缺失的意识》中按照黑格尔主义的标准去区分了信仰和宗教。信仰往往被视作启蒙之前的阶段,充斥着仪式和被主导,服从和真理教化。而黑格尔主义的宗教则类似于一种包含权威可错性的理性主体共同立法。这使得所谓的公民宗教实质上是一个基于共同体实体制度和共同认知模式的一种混合制造。
一些学术界的观点将美国这种公民宗教的认知模式视作一种公共理性的基础。整个国家共同体默认的一套意识形态前设,他同时规定了我们参与公共生活的身份和讨论方式,并且在这个制度性基础上进行政治参与。
这种公民宗教的认知模式往往是整全性但不系统的,虽然大部分人没有接受政治哲学的训练,但几乎都能靠一两条价值观公设加上一套朴素政治逻辑去解释所有的政治事件。这也是各大国网络键政公民的一大理论基础。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 贝拉解释过这种公民宗教与真正宗教的相似性,公民在谈论美国时,想到的主体不是美国这个主权机器,而是想象他们的共同体提供了宗教里救赎世界,地狱天堂那样的价值维度。就如同当代美国政治的党派分野,虽然已经某种程度违背了联邦党人的理想初衷(他们国父们所谓的Novus Ordo Soclorum,即千秋秩序),但是在公民宗教的想里可以通过不断自我改良来无视这类事情。美国例外主义既框定了对内认同的基本底线,又从这种内部认知去重构世界观,这类似于某种美国人的内外之辩。
这种公民宗教还体现在一种对于政治价值的神圣性建构。
卢梭提到过属于人的宗教(Lareligiondel’homme)和属于公民的宗教(Lareligionducitoyen),前者还是需要通过仪式和主流话语来保证宗教基础,而后者更体现为一种制度性共同纽带,其最重要作用的是在政治变迁多次之后,公民宗教仍然能让这个共同体保留一种共同的政治尺度。
于是从联邦党人文集开始,美国精英的自我神圣化就与美国这场建国实验捆绑了起来。
“通过他们(联邦党人)的行动和示范决定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人类社会是否真地能够通过反思和抉择建立良好的政府,抑或注定要在自己的政治体制方面听任机遇和强大的力量?”显然联邦党人的自我神圣化漂亮的回答了这一话题。
这也是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有很多人家美国建国先贤不断拔高吹捧的缘由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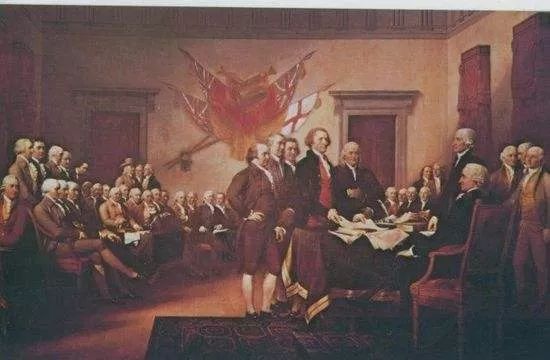
美国例外主义这个公民宗教,奠定了美国共同体的内外之别。美国的对内认同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理查罗蒂在《构筑我们的国家》中提到了《雪崩》这个小说,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资本家完全僭越在公民社会和治理机器的社会,特许权和特许权内部的企业法规已经践踏了规则,特许经营者如同加洛林王朝的领主一般,而木排上那些飘离在河流上的边缘人和贫民则是苦难大众的代表。
虽然一般解读上这是斯特劳森对二十世纪美国政治的无情讽刺——利润丰厚的资本集团和特许经营团体通过代理人组成了美国的治理机器实体,这种精英政治在美国被视作理所当然。但是理查罗蒂却在这样一部批判性的小说中看到一个特性,即使对美国存在反思和讽刺,但是小说作者依然保持了一个美国公民的先定承诺,
默认了这个共同体的合法性。
用中国的话来说是反贪官不反皇帝,在美国则是反资本家,但不反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机器本身。
另外,在理查罗蒂看来,价值的产生与实践是“政治性”的,不是被预设的。然而在美国例外论中,到处存在这种价值预设。这种预设是一种关乎美国公民社会合法性资格的“常识”。如果你和美国人交流过就知道,美国人无论什么政治立场,都很喜欢强调用自己个体的常识来推广应用到全世界上,自由派能用民主神话和政治正确价值来解释全世界,保守派可能除了自己一亩三分地其他压根不关心。
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开始建构对外部的想象。基辛格在《大外交》里面提到过美国执拗的民主神话,这种民主神话的世界观是从威尔逊主义的民族自决开始和冷战分割思维搅和在一起形成的外交模式,而基辛格等人实际上在试图改变这种对外模式。比如基辛格在《论中国》里面提倡中美共治。
但是基辛格对于中国的解读也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背景“过度简化”之上的。他把我国的文化背景等同于一种支撑现有局面的共同纽带,一种由精英阶级主导的文脉主义,即中国是一种永恒的天下,而各个政治体只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这和上文提到的美国人对自身的想像是一致的。
赵汀阳吐槽过这种“美式天下”(Pax Americanna)观,把观点总结一下:
1.极端相信一个无外的,无排他性的的世界,那么治理这种世界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而美国的这套认同及建立的这套制度,在美国人那里被视作一种“世界宪法”。
2.但他又必须坚持美国的“个别性”(parochialism),即美国的特殊性,并且要求从美国治理的基础上去建立所谓的“和平”。
3.这种例外论其实是一种个体主义(可以理解为价值观缺位,于是想办法给给自己缺位的自我价值观做填充),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利益的保存。
这种认知模式看起来互相矛盾,美国利益优先是美国一种奉行的原则,然而他又觉得自己是世界城邦的主体。
这种看起来好笑的模式成了美国的“世界”想象。
正如同罗斯福关于“新秩序”演讲一样,这种新秩序是把美国自己作为民主和世界治理的主体。
于是,似乎美国的外交干涉和区域政治平衡手,市场经济秩序在美国国内被视作一种奇怪的“正义”。而美国的左派右派对于这种逻辑进行了不同的填充。对左而言,是进步主义和世界主义;对右而言,是美国秩序。
这种认知模式在欧洲也存在。上文已有举例。在特朗普上台以后,认为特朗普主义是对原有西方秩序的践踏的齐泽克,甚至认为通过对抗特朗普,欧洲可以形成自发的国际组织实践,最后建立起一个欧洲“新世界”的模式,使欧洲再一次凝聚,欧洲要当西方社会最后的堡垒,用欧洲模拟世界。
当然,这种公民宗教和例外主义也慢慢开始被现代性解构。比如在美国进步主义逐渐取代传统的精英主义,我以前文章也写的很多了。
进步主义至今的世界观是建立在既定的现代性美国而不是重塑美国建国史,讨论的议程设置也是现代传媒主导下造成的舆论代表性(当然这种代表性是建立在在某些保守主义受众失声的状况下来的,这也造成了某共和党候选人的受欢迎),在这个议程设置中平权和共同生活是主要议题,这些才是目前被视作政治价值的事情。保守主义者坚守的所谓尚武和拓殖,政治现实主义等所谓美国精神早就被赶出主流舆论外,
过长的和平时期和消费主义文化让这种价值观依赖的重度匮乏社会和扩张带来的武力需求消失了。
而舆论政治本身是通过改变我们的语言习惯和世界观定义开始的。进步主义运动后形成的政治语境,改变公共舆论中的语言习惯,对性别和种族保证绝对的中立;新形成的社交文化也重塑了传统父权白人社会中的身份扮演,也形成了新的社交规则和身份原则。正如同瑞典军队开始执行性别中立和招募女兵之后,将雄狮标志的性别特征阉割掉一样;
让代表废奴主义,社会运动家加上少数族裔和被剥削性别的代表人物作为的新的符号不过是当前政治语境的表达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