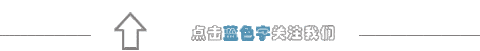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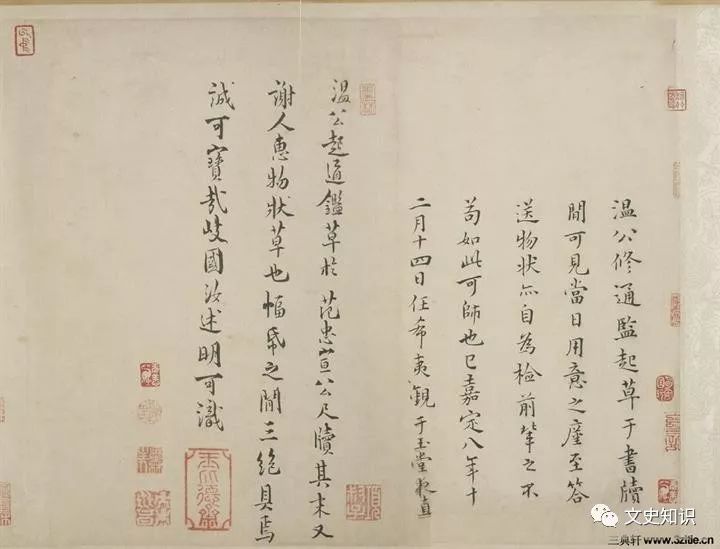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编次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
到五代后周恭帝显德六年(959),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为一编,首要工作是
以历代可信文献为依凭,逐年逐月逐日地叙述历史发展过程,清理历史脉络,
还原历史真相。
其编纂方法是先做长编,在此基础上分清主次,删繁就简。
其
中部分历史阶段是以编年体史书为基础编成,如汉有荀悦《汉纪》、袁宏《后汉
纪》,六朝有许嵩《建康实录》,唐有历朝《实录》与柳芳《唐历》等书,五代也
有十多部《实录》。
这些编年体史书都有各自的局限,如叙事过简、忌讳掩饰、
彼此冲突矛盾,以及事件发生过程交代不完整等问题。
没有编年体史书可以参
考的部分,工作量更大。
司马光依靠三位杰出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的帮助,
对当时可见文献作了竭泽而渔式的网罗,又以妥当的裁剪和精密的考证,完成了
全书的编纂,前后历时十九年,司马光在进表中也称平生精力尽于此书。
由此,
这部伟大史书在中国史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司马光能完成此书,我曾总
结六条原因,曰皇家支持,曰知所进退,曰助手得力,曰史观通达,曰方法得体,
曰亲力亲为,缺一则难以蒇事。
从《资治通鉴》全书看,虽然如书名所示,全书对历史过程的叙述,是要给
当代和后世的君臣提供治理国家的参考,但全书却将此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
作了细大不捐的叙述,且于时间、人物、地点、真伪、制度等所涉细节,也都不
辞琐碎地加以考证,可以看出司马光在追求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方面,与
现代学术之务明原委之精神完全相通,超越在他前后的几乎所有史家。
当然,
作为皇家支持的大规模纂著,司马光也要考虑现实的参考启发意义,以史论的
方式,发表他对史事的看法。
在编纂《资治通鉴》前,司马光曾著历代编年简史《稽古录》,其中《历年图》
部分,附有三十六篇断代史论,对周至五代历朝施政得失,对历代君主之能力
性格、成败得失,都有具体而微的评价。
虽然这种面面俱到的史赞为历代史书
所因袭,但司马光显然觉得不能满意,他认为应就历代成败的关键问题,参
考历代史家的意见,表达他独到的见解。
司马光所采前人之史论,计有荀子、扬子《法言》(三则),贾谊、荀悦(七
则)、太史公、班固(十三则)、李德裕、班彪(三则)、袁宏(二则)、范晔
(三则)、华峤、习凿齿(四则)、孙盛(二则)、陈寿、虞喜、干宝、崔鸿(二
则)、裴子野(八则)、沈约(三则)、萧子显、陈岳(二则)、欧阳修(二则)
(以在《资治通鉴》中出现先后为序),凡六十三则。
所引崔鸿、裴子野、陈
岳等所作议论之原书不存,其他原书大多具在,可以看到司马光在采择时
非常慎重,且大多仅摘其要点,未必皆详加引录。
司马光本人所作议论,皆以“臣光曰”标出,是向皇帝明确表达他对史事的
具体见解。
通检全书,凡一百一十九则。
后人评判读《资治通鉴》而后知司马光
有宰相胸襟,主要是就这些史论而言。
其中约半数是对具体人事的评价,读者
比对叙事可以理解分析,这里不作罗列。
约半数皆就历史和为政之重大问题发
表见解,具体可作以下介绍。
正统之争。
是宋代史学争议的重大问题,更是编年体史书在分裂时期不
能回避的关键所在。
司马光的看法与他同时的欧阳修所见有异,与南宋程朱
学术盛行后以蜀汉承汉、南唐承唐的见解也完全不同。
他认为上古“有民人社
稷者,通谓之君”,而“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即君之
正统所在应得到举天下普遍之拥护,天下不违,人民拥戴。
如果“不能使九州
合为一统”,皆不能为正统。
如刘备称中山靖王之后,刘裕称楚元王之后,南
唐李昪称唐吴王恪之后,或族属疏远,或是非难辨,他皆不认可为正统,因而
能在《资治通鉴》之三国部分以曹魏为主,南北朝部分兼叙南北,五代承认中
原五朝之实际存在,不对任何一方作主观的拔高。
正统确立,受天之命统治天下的君主如何治理天下、统摄群臣,即为君道,
是司马光最重要的论述。
重视礼乐教化。
司马光认为,人主统治天下,应重视礼乐教化,目标是使天
下“动静有法而百行备”“内外有别而九族睦”“长幼有伦而俗化美”“君臣有
叙而政治成”“诸侯顺服而纪纲正”,这是他认可的天下秩序。
对叔孙通定朝仪,
他认为仅得“礼之糠粃”;
对汉光武帝征讨天下之际,尚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
开广学校,修明礼乐”,表示极大赞赏;
对唐太宗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深不
以为然。
司马光认为君主要成为守礼的典范。
他对晋武帝颇有非议,但对其能
守三年之丧,则极表赞同。
从大的方面说,礼的大端是君臣各存分际,使上
下不乱,则秩序可以维系。
《资治通鉴》开卷即述三家分晋,痛斥周天子不
能坚守先王之礼,使三晋犯礼侵义之行为得到合法的承认,造成长期大乱,
根本在于“天子自坏”礼义,最终“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
祸患无穷。
类似情况则如唐方镇之祸,司马光认为肇始于肃宗之姑息苟且。
他认为君臣“尊卑有分,大小有伦”,但肃宗幸而复国,没有为天下及时确
定长久之纲纪,而是“偷取一时之安”,命将帅,授方镇,“无问贤不肖,惟
其所欲与者则授之”,终至积习为常,至“偏裨士卒,杀逐主帅”而不治其
罪,以至“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进而“将帅之陵天子”,终
至天下大乱。
这段话对宋前二百多年之动乱,可谓诛心之论。
从小的方面说,则为能否善用刑赏,控驭群臣。
司马光认为应“度德而叙位,
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赏,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
对历代不知此者,批
评最多。
如批北魏允许勋贵不死为弊法,责梁武帝优厚其弟为枉“王者之法”,
周武帝对高遵漏泄大罪不行戮而借伊娄谦之手赦之,违背了君主“赏有功,诛
有罪”的原则。
人主必须有信。
刘裕既据关中,初委王镇恶以关中事,复命沈田子以图
镇恶,司马光给以严厉谴责,认为使臣下争斗而致乱,使中原故土“得之艰
难,失之造次”。
再如唐武宗诛郭谊,在下诏鼓励昭义将士背叛帅而归朝后,
对郭谊杀叛帅归朝,反追究旧恶而亟诛之,有失人主之信。
进而则将信及夷
狄。
对傅介子诱杀楼兰王,历代多有赞誉,司马光则斥为“盗贼之谋”,盖以
权谋虽得胜于一时,失信终贻患于无穷。
对东汉段颖袭杀散羌的行为,他认
为不能仅肯定他“克捷有功”,谴责他对边民“视之如草木禽兽”,任意诛杀,
恐“华夏之民亦将蜂起而为盗”。
了解于此,也就明白他对牛、李维州纳叛事
件的态度,赞同牛僧孺将归唐之吐蕃叛将悉怛谋归还吐蕃,是在唐与吐蕃修
好以后,应坚守信义,不应贪图维州小利。
此事今人多有歧见,在司马光是
坚持始终,且于牛、李并无明显偏颇。
建储是王朝存续之关键所在,司马光本人也目睹仁宗晚年因东宫未立而造
成的危机,在仁宗病重时劝皇子早入内,保证了英宗的顺利接班。
“臣光曰”有
多处涉及建储问题。
如汉武帝已立太子,在钩弋夫人生子弗陵后,命其所居为
尧母门,乃让奸人逆知武帝偏爱少子,欲以为嗣,遂危及皇后、太子,人为造成
巫蛊之祸。
隋文帝既知嫡庶多争,孤弱易摇,但又造成兄弟间“势钧位逼”的局
面,司马光特举辛伯之言,认为内外宠及嬖子配嫡,为乱国之本。
对“玄武门之变”
之“蹀血禁门,推刃同气”,更有“贻讥千古”之痛惜。
宦官问题是汉、唐政治之突出问题,对宦官之祸的议论,历来以范晔《后
汉书·宦者列传》“论”最为精当,说“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之命”,自是
东汉的景况。
而唐代宦官专政绵历近二百年,却绝非幼主、女君可概括。
司马光
分析,宦官出入宫禁,“人主自幼及长,与之亲狎,非如三公六卿,进见有时,可
严惮也”,君主对内臣、外臣亲疏有别,加上唐代宦者握兵,乃至“太阿之柄,落
其掌握”。
司马光赞赏太宗“深抑宦官,无得过四品”之举措,认为从玄宗“始隳
旧章”,让宦者“进退将相”,乃至数代权宦“窃弄刑赏,壅蔽聪明,视天子如委裘,
陵宰相如奴虏”,乃至国事日非。
他虽然认为宫禁寺人不可无,但君主不能过分
借以权柄,是于北宋一些特殊现象有感而发。
君臣之际,大约是古今一大难题,司马光议论亦多。
他对战国养士之风深
恶痛绝,认为如孟尝君所为,“上以侮其君,下以蠧其民,是奸人之雄也”,绝
不值得提倡。
对东汉清流当四海横流之际,“臧否人物,激浊扬清”,他也深不
以为然,感叹“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反而
赞赏郭林宗之“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他对欧阳修的史观多有异见,唯独
对冯道之批评,引为知己。
司马光认为忠臣当“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
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
若遇天下无道,可以灭迹山林,优游下僚,
不可“依违拱默,窃位素餐”,更不应如冯道那样,“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
自如”,斥此为“奸臣之尤”。
在谈到西汉霍光家族之祸时,他认为关键在于人
君之器为“人臣执之,久而不归”,终招大祸。
对臣下结为朋党,他认为根子在
于君主“明不能烛,强不能断,邪正并进,毁誉交至,取舍不在于己,威福潜移
于人,于是谗慝得志,而朋党之议兴”。
对历代君臣,司马光多有评骘,所见大体公允。
他对历代君主最赞赏之人
物,应为后周世宗。
他赞誉世宗有“宏规大度”,其所为“以信令御群臣,以正
义责诸国”,在众多事件处理中都能见到他的处事得要,如“王环以不降受赏,
刘仁赡以坚守蒙褒,严续以尽忠获存,蜀兵以反复就诛,冯道以失节被弃,张
美以私恩见疏”,在统一战争中,“江南未服,则亲犯矢石,期于必克;
既服,
则爱之如子,推诚尽言,为之远虑”,指世宗征南唐,前后态度之变化,恰见有
道君主的胸襟。
司马光的史论,内容极其丰富,难以备述,以上仅举“臣光曰”所议论之
大端而已。
与司马光在其他论著中的议论可以互相参考,陶懋炳《司马光史论
探微》(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有详尽罗列,在此不备举。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
2020年第2期“特别关注”
栏目
编辑絮语:因新型肺炎病毒影响,《文史知识》2020年第2其期纸刊可能要更晚一些送到广大读者的手中,在此向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另外,因编辑部亦未得到纸本刊物,故近期刊登的电子文本可能均与最终纸本有差,祈读者多多包涵。
感谢您对本刊的厚爱,2020《文史知识》继续贴心陪伴您,忙碌中别忘了订阅哦:
一、去往邮局征订,邮发代号2-271。
二、咨询伯鸿书店购买,联系电话:010-63458912、010-63265380。
三、北京的读者可以去往三联韬奋书店、万圣书园、伯鸿书店购买(伯鸿书店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中华书局一层)。
四、需要网上购买的读者,请登陆“杂志铺”网站(www.zazhipu.com),京东商城中华书局官方旗舰店(http://mall.jd.com/index-84097.html)然后在搜索栏搜索“文史知识”,即可看到《文史知识》的订阅信息,按照网站购物流程购买即可。
五、集体订购电话:010-63458229。
六、您也可以添加《文史知识》的微信公众号“wszs1981”及时获取《文史知识》的更多信息!征订在即,请千万别错过。
七、敬告读者:自2018年7月1日起,《文史知识》编辑部不再接受任何购买咨询,如欲购买《文史知识》新刊、过刊、历年合订本等销售问题,敬请致电中华书局伯鸿书店(010-63458912、010-63265380),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文史知识》(月刊)邮发代号2-271,每月1日出版,定价15.00元,全国邮局均可订阅,国内统一刊号 CN11-3153/K
国内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2-9869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邮局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文史知识》编辑部收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458229
(邮购 每册15元,挂号每次另加3元)
微信号:wszs1981
QQ群:363031535(迁移中) 713071938(新群)
新浪微博:@文史知识杂志
官方网站:中华书局/文史知识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电话:010-63397473
010-63458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