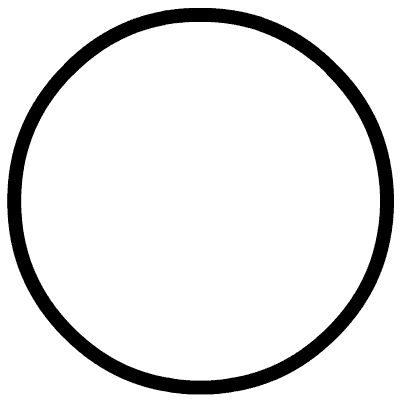
点击上方关注我们

✖


作者:(澳)凯蒂·巴尼特/(澳)杰里米·甘斯
译者: 邵逸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2025-1
ISBN:9787100240352
导言
1386年,法莱斯法庭以谋杀儿童的罪名判处一名刑事被告死刑。行刑前,被告穿上了新衣服,为了反映“她”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她”的头和腿被弄伤了。然后,“她”在人群前被绞死。
这一悲惨案件有何特殊之处?被告其实是一头母猪,却像人一样被押上审判台,宣告有罪。尽管在法莱斯的居民看来这次审判不同寻常,但事实上,对动物的审判在全球多个地区都有记录,从欧洲到非洲,从印度到东南亚,再到新西兰,动物被当作刑事被告的现象并不罕见。
在《有罪的猪》一书中,这些不同寻常却又充满趣味的“审判”案例被生动地一一呈现。凯蒂·巴尼特和杰里米·甘斯两位法学教授将带领读者深度梳理动物在法律史上的地位,探寻这些奇特审判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审视人与动物共存方式的全新视角。
一、为什么是猪?
在历史上遭到起诉的杀人动物记录中,为什么猪如此普遍?美国学者和语言学家爱德华·佩森·埃文斯(Edward Payson Evans)撰写了迄今为止关于中世纪动物起诉最详尽的图书,他给出了以下解释:
猪经常受到审判和被判死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被允许在街上到处跑,而且数量众多。它们受到圣安东尼的特别保护……这赋予了它们某种豁免权,因此它们变成一种严重的妨害,不仅威胁儿童的生命,还产生疾病、传播疾病。
1100年左右圣安东尼医院牧师修道会(The Order of Hospitallers of St. Anthony)出现于格勒诺布尔,旨在照顾受病痛折磨的人;他们尤其擅长医治食用被真菌感染的谷物引发的麦角中毒。为了感谢他们的善举,将一窝猪崽中最小的一只捐给医院牧师成了传统,因为圣安东尼是猪和其他家养动物的守护神(据说他做修士时曾有一只忠实的伴侣猪)。医院牧师们给他们的猪脖子上挂上铃铛,让它们在城市里觅食。“安东尼猪”因为跟随任何看似有食物的人而臭名昭著,尽管中世纪的英格兰城镇至少尝试过控制它们。
中世纪历史学家杰米·克里纳(Jamie Kriener)提出,猪在古代和中世纪初期被例行饲养,它们的肉在很多社会中都颇具价值,包括罗马社会。然而,猪非常聪明且体格强壮——它们可以跳4英尺高,游几英里。它们能够向其他的猪学习并拥有很好的空间感。猪也喜欢解谜,如果被囚禁则喜欢尝试逃跑。古代和中世纪的人们知道这一切,并试图约束它们,征召猪倌控制它们。
在中世纪早期,猪倌倾向于在森林里牧猪,土地所有者甚至向猪主人征税,这被称为“猪只放牧费”(pannage)。然而,在中世纪晚期动物审判开始出现时,猪更经常被养在城市里,引发越来越多针对其气味和粪便的投诉。
人们不禁会问:幼儿是否是饥肠辘辘的猪容易得手的目标?众所周知,猪是杂食动物,吃死去的动物、腐烂的垃圾和人类排泄物。我们也知道,家养母猪如果感觉紧张或不适,会吃掉自己的猪崽。而且,猪确实偶尔会吃掉跌倒在猪圈里的农民或婴幼儿:过去10年,世界各地发生了好几起这样的事件,包括在美国。这些事件没有发生在澳大利亚郊区,因为猪主要生活在工业化的农场中,不在我们的街道上游荡——尽管澳大利亚的灌木丛中确实有野生猪。
二、杀人的猪
相较于被视为本性狂野或凶猛的半驯化或野生动物,驯化动物会因为不当行为受到更严厉的对待。驯化动物按预期是可控和温顺的,因此对它们的控制涉及更多的法律。当驯化动物杀死或伤害他者时,至少有两个可能的犯罪者:动物和动物的所有者。法律对待动物的方式各不相同。
本章开头我们讲述了法莱斯的母猪致人死亡,这绝非个例——过去有很多猪被指控杀害儿童。1457年,1只母猪被判害死了萨维尼5岁的男孩让·马丁。6只猪崽身上沾有血迹,它们最初被指控为共犯,但埃文斯指出:“由于缺乏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它们协助伤害死者,它们被归还给了所有者,条件是如果有进一步的证据证明它们是母亲罪行的共犯,所有者必须为保证它们出庭而缴纳保释金。”有意思的是,就像对人的审判一样,在判决不杀死小猪时,它们的年龄和共犯证据的不足被认为是相关的。虽然小猪免于被处死,但原主人表示不想要它们,因此它们被作为无主财产没收,交给萨维尼夫人凯瑟琳·德巴诺。
在1494年另一个案件中,1只猪因“压死摇篮中的幼童并使其毁容”而被逮捕。审判时,几名证人称:“复活节早晨,由于父亲在看守牛群,母亲吉隆去了迪济村,大人都不在,婴儿单独留在摇篮中。猪在该时间段进入房屋,啃咬婴儿的脸和脖子。婴儿因被咬伤而丧生。”提出指控的是住在这家人隔壁农场的修道士。法官对猪进行判决时说道:
出于对上述罪行的厌恶和惊骇,和以儆效尤、维护正义的目的,我们讨论、审判、判决并宣布,命令涉案的猪——现已被作为囚犯关押在上述修道院——遵循崇高的旨意,在属于上述修道士的绞刑架和刑场——该地与他们位于阿文的永久租佃地产相连——附近的木绞刑架上吊死。
有时牵涉罪案的猪会被赦免。1379年,在圣马塞尔勒热塞,两群动物混在了一起,一群是社区共有的,一群属于当地的小修道院。3只母猪被1只小猪的尖叫激怒,撞倒猪倌的儿子佩里诺特·米埃并致其死亡。母猪被判处死刑。据说“由于两个畜群都迅速到达谋杀现场,并通过其叫声和攻击性行为展示它们对袭击行为的赞同……它们作为共犯被逮捕,并被法庭判处接受同样的惩罚”。然而拥有其中一个畜群的修道士要求赦免除3只肇事动物之外所有其他的猪,勃艮第公爵批准了这一要求。
有时所有者也会被惩罚,如杰汉·德拉朗德和其妻子1499年他们的猪伤害并杀死一个叫吉隆的小孩。猪被判死刑,德拉朗德夫妇也被罚款,理由是他们在照顾孩子方面有过失,而非任何与猪相关的过失。埃文斯提到,一般来说“动物犯下血案,其所有者被认为完全无过失,有时甚至会因损失获得补偿”。正如我们所见,英国法律对此持相当不同的看法。
对杀人动物的惩罚不尽相同。有时,动物会受到折磨,似乎是为了获得它们的“供述”(尽管我们不清楚它们如何认罪)。埃文斯讲述了欧洲13只猪被吊死的例子,还有3只被活埋、1只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全都是因为犯下杀死婴幼儿的罪行。有趣的是,遵循适当的程序仍然很重要。在施韦因富特,一只母猪咬掉当地一个孩子的耳朵,并撕破他的手,因此被关进了监狱。刽子手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绞死了母猪,这一事件激怒当地民众,刽子手被迫逃亡。"Schweinfurt Sauhenker"(施韦因富特母猪刽子手)这一短语,后来被用来指无视法律的无赖。
正如我们所提到的,杀人动物一般不会被食用——哪怕这类动物一般是被人类食用的——因为它们的肉被认为受到了玷污。埃文斯记录了1553年的一个事件: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些猪杀死一个孩子,结果被处决并扔进了河里。同样,1621年,在萨克森州马赫恩,一头牛杀死一名妇女,结果被杀死并焚烧,其肉和皮均未被使用。然而,1578年在根特,一头牛杀死人后被宰杀,其肉被出售,所得的收入一半给了受害人的家人,另一半给了城里的穷人。牛的头被砍下,放在绞刑架附近的木桩上,以示惩罚。
三、动物审判的背后
罗马人喜欢看罪犯被角斗士或野生动物处决,面包和游戏(panem et circenses)满足了公众对这种场面的需求。在帝国时代的罗马,公众有权投票决定斗兽场上的生死,这让他们有一种权力感,同时又不威胁到皇帝。英国公众也喜欢看罪犯被绞死、戴上枷锁或遭受各种羞辱,如打上烙印。伦敦附近泰本1571年竖立并一直使用到1783年的“泰本树”(Tyburn Tree),是一处臭名昭著的绞刑架,可以同时处决多名罪犯。动物审判肯定也有表演性的一面:它们和对人的审判与处决一样,都是一种奇观。
拉开距离来看,我们很容易认为动物审判的存在反映了一个更加迷信的时代;然而,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威廉斯(James McWilliams)认为,这关系到一个事实,即在前工业化时代——从中世纪到19世纪——人和动物的关系更加密切:
生活在前工业化农业社会的人们几乎一直在与驯化动物互动。17世纪的农业账簿表明那个时代的农民每天花16个小时观察和照顾驯化动物。他们看着这些动物做出选择、对人类指令做出反应、形成社群关系并彰显自己独特的个性。这种观察到的亲密关系持续到19世纪,直到饲养场和食品加工厂整合畜牧业的业务,最终取代了让动物和农民相对长期地近距离相处的做法。在这种整合之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类开始把动物当作物品来谈论和对待。“猪,”1880年的一部农业手册解释道,“是农场上最有价值的机器。”如今,近99%的动物产品都来自这种“工厂化农场”,将动物视为物品的观点仍占据主流。
尽管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不应过于夸大麦克威廉斯的观点。在中世纪社会,尽管动物一直在人的周围,但仍旧被视为财产。圣托马斯·阿奎那明确认为牛可以被拥有,杀死一只牛绝不等同于杀死一个人。而且,中世纪很多人认为人类优于动物,并认为人类有权对动物发号施令。确实,有人认为家养动物受到审判不是因为它们被等同于人类杀人犯,而是因为它们颠覆了自然规律:它们杀死了本应掌控它们的人类。
相反,历史学家彼得·丁泽尔巴赫认为,动物审判开始盛行,要归功于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的先决条件:传染病、经济萧条和社会冲突带来不安全感;相关地区存在罗马法和法律程序;看到法律程序和司法被实行,能给人带来安慰;举行这种审判,律师、贵族和法官能从中获得利益;此外,人们在极端状况下有将动物人格化的倾向。丁泽尔巴赫设想这些审判仅在极不寻常的状况下发生,目的是帮助地方社群应对难以驾驭的威胁——不是因为它们被证明有效,而是因为它们能够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即当局正在以合作和坚决的方式不懈地维护法律与秩序。
在以天主教为主并继承了罗马法的区域,依法惩罚动物的倾向似乎更加普遍。然而,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罗马法不归罪于动物本身;相反,依照“动物致人损害之诉”(actio de pauperie),户主应为其奴隶、孩子和动物的行为造成的损害负责。因此,思维方式明显发生了转变,至今也不知其原因。不过,对动物进行法律惩罚,也许与罗马法将动物等同于儿童和奴隶而非物品的做法是一致的。
四、现代法律与心理观念的转变
如今,我们可能并没有像我们以为的那样远离中世纪的思维方式。心理学家杰弗里·古德温(Geoffrey Goodwin)和法律学者亚当·本福拉多(Adam Benforado)最近进行了一项很有意思的心理学研究,探究是什么触发了我们的报复欲望,尤其是和动物相关的。他们向参与者呈现了动物发动袭击的几种不同可能性:在某些情形下,受害者是人类依照不同的设定,包括10岁女孩、55岁无家可归的男子、48岁的恋童癖患者(但没有因其罪行受到惩罚)在其他情形下,受到损害的是财产或其他动物(如家养的狗)。肇事者包括野生动物和驯化动物。
研究显示,当动物杀死年幼的孩子时,参与者惩罚动物的欲望,显著高于它杀死年纪更大的人或另一只动物的情形。同样的结果多次出现。古德温和本福拉多称之为“受害者身份”效应。他们指出,如果受害者值得同情,哪怕动物不再危险,这种效应也会存在。因此,参与者赞成某种惩罚,似乎是基于这样的观点:相较于杀死其他不那么令人同情的人,杀死儿童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古德温和本福拉多还向参与者呈现了当局杀死一条“无辜”的鲨鱼的情景,以及杀死因致人死亡而“有罪的”鲨鱼的情景。他们称所发现的现象为“定向惩罚效应”,这个研究结果也多次得到确认:参与者表示,只有杀死正确的鲨鱼,才能对受害者的死做出适当的赔偿;他们不太赞成杀死“无辜的”鲨鱼。此外,参与者更倾向于赞成对“有罪的动物”而非“无辜的”动物施加痛苦,特别是当受害者是儿童时。但如果受害者有恋童癖,则不那么赞成。这表明报复动机占主导地位。尽管我们不再审判或绞死致命动物,但现代人似乎和中世纪人一样可能判定动物“有罪”且应受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