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四部曲
自
面世以来,从来没有像第四部《大秦赋》这般「
批评如潮
」。
人们对《大秦赋》的批评,要害不在于演员不够好,也不在于剧情设计有多荒唐。
看过这系列剧的人都知道,它的主调是在赞颂秦国及秦朝。尤其最近这部《大秦赋》,对秦始皇的美化更是露骨。
这种历史翻案,与秦始皇暴君形象相背,过于违逆传统认知。
在理解秦国自西方崛起、直至秦朝武力统一上,传统历史认知一直很稳定。
所以,与其说批评者在批评《大秦赋》,不如说就是在批评大秦。
影视剧虽然可以戏说,但美化「
暴秦
」与「
暴政
」,也触达到人们内心深处最根本的一根弦。

对于中国各个历史朝代,我们大都会有一个总体印象,并会找到一个与之相对的凝练词汇,比如「
雄汉
」「
盛唐
」。
但对于秦,我们常会听到两个词汇,一个是「
强秦
」,一个是「
暴秦
」。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
很显然,《大秦帝国》展现的是「
强秦
」。
可是,对于大秦的认识,历代都有共识,主流就是「
暴秦
」。

|
国漫剧《秦时明月》是一部以「暴秦」为历史逻辑的动漫,图中人物为淮阴侯韩信;与《大秦帝国》一样,二者均有大量粉丝观众。
图片来源:《秦时明月之沧海横流》
人们对「
暴秦
」的批评,最直接的就是「
徭役繁重
」。
「
强秦
」强调的是秦国国家力量强大的一面。它可以东扫六国,北击匈奴,南向面海,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奠定中国基本版图。
从表面事实来看,国家的「
强
」肯定优于「
弱
」,但「
强
」的表面事实下,往往隐藏着更多的其他事实。
据历史学家朱绍侯编著的《中国古代史》所述,秦朝人口约有2000万,全国军队数目约在100万以上,修建秦始皇陵约70万人,再加之修建长城、驰道,服役人口至少在200万以上。
如果一个社会每10人就有一人从事国家役力,这种社会状态可想而知。
这种役使人口的方式,是秦国走向「
富国强兵
」道路的基础。
这一方式也可以囊括在「
耕战主义
」的旗号下。
「
耕战
」一词出自商鞅及其后学汇著而成的《商君书》,《商君书·慎法》中便有这样一句:
「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
「
耕战
」是秦国人的首要任务。「
耕
」以保证基本温饱,「
战
」以维持国家力量,在「
耕战
」之后,人民方可「
得其所乐
」。
但在生产力低下、战事不绝的先秦时期,如何做到「
而后得其所乐
」?
不过幻想罢了。
因此在一些更为激烈的批评者看来,秦国所奉行的「
耕战主义
」,多多少少有些近代「
军国主义
」的味道。
|
秦能统一东方六国,离不开李斯这位政治家的参与。在
「知鸦」通识课
《中国人物》中
,我们
讲述了李斯如何从一介布衣,摇身变为丞相,在战国时代一展身手的故事,深度分析他与秦始皇如何共同奠定了延续两千年的秦制。
《中国人物》
以政制、思想、
财政、文学等六个面向为切入点,通过描述这些人物的选择,以及后世人物对前人选择的再选择,透视中国历史的本色。
现在扫码订阅,享受7折特惠。
这就涉及到对「
暴秦
」的第二个批评:「
军事至上
」。
对于秦人「
好战
」的批评,人们常常关注到的还有「
军功授爵制
」,即普通人可以通过军功获得一定的爵位。
军功爵制在春秋时期出现,战国各国都有存在,但秦国表现最甚。
据朱绍侯论著《军功爵制研究》统计,自秦孝公八年(
公元前354年,即商鞅变法时期
),到秦昭襄王五十一年(
公元前256年,即秦灭周之年
),在军功的激励下,秦国在99年间有记录的杀人数目就达到了1617000人。
也就是,平均每年要杀掉他国军民16000余人。
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
这正是秦国强大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秦国之所以为「
暴秦
」的原因之一。
「
强秦
」与「
暴秦
」,本就是同一件事物的两个面向。
这种屠杀式的攻伐,最后连秦国人自己都不愿接受。
据《吕氏春秋》载,吕不韦当政时期,曾提出「
克其国,不及其民
」
的「
义兵
」主张
(
《吕氏春秋·怀宪》
)
。故《大秦赋》中所演绎的「
吕不韦召令勿杀俘虏、平民
」,虽言过其实,但确有其源。
同样,对于剧中嬴政「
解天下庶民于倒悬
」(
典出《孟子·公孙丑上》
)的正义式宣言,《吕氏春秋》亦有同类说辞——尽管很可能是虚言。《大秦赋》挖掘出了这些细节,倒也能看到他们的用心。
所以,批评者不必对这些历史细节苛责与否定,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影视剧历史表达背后想要传达的对「
秦国模式
」的赞美之情。

|
《大秦赋》中,由段奕宏饰演的吕不韦在对秦国传统的军功爵制提出异议,这也是《大秦赋》饱受批评的桥段之一。
图片来源:《大秦赋》剧照

秦国正是依靠上述这种强大的军事扩张而崛起,从而寻找到一种促使国家崛起的「
秦国模式
」。
这种模式下,国家崛起速度之快、国家力量之庞大,在农业社会的确可以造就奇迹。
集中力量能办大事,表征之一
就是浩大的国家工程。
如今被人们视为奇迹的秦始皇陵与秦长城,当然是人类文明不可磨灭的遗产,但对于2200年前的秦朝劳力来说,可能并非如此。
除了「
徭役繁重
」和「
军事至上
」,谈秦国模式,还应该谈到「
思想控制
」与「
秦律严苛
」。
思想控制方面,最常谈的是焚书坑儒,这里不再多说。按照现代话语来说,就是打压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
秦律严苛方面,历代论述也有很多。一般认为,秦国严密法令的建构始自商鞅。
历史上不乏对商鞅、对秦法严厉批评之人,如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评价说: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杜甫在《述古三首》中也说:
「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司马迁虽对商鞅所实施的法令很不满意,但也承认商鞅之法确使秦国富强——不管他使用了何种手段。
而苏轼直接否定了秦国崛起是商鞅之功的观点:
「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
——苏轼《商鞅论》
当然,苏轼之所以这样否定商鞅,是因为有「
王安石变法
」的历史背景存在。但不管从哪个角度说,「
秦律严苛
」已成一个不争的事实,批评秦之暴政,也是历代学者的一个共识。
尤其商鞅,作茧自缚,最终也死在自己定的法令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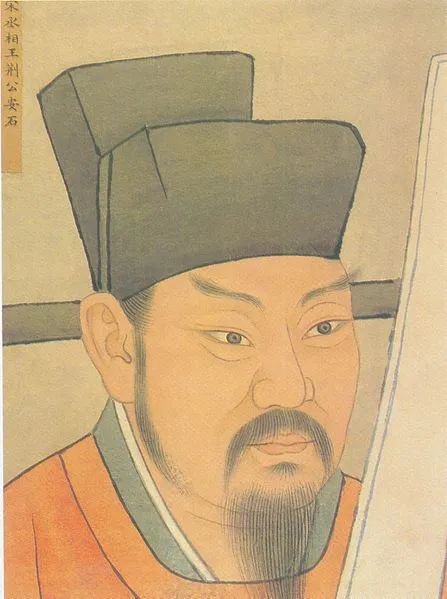
|
力主变法的王安石,曾写下诗句「今人未可非商鞅」,对世人批评商鞅变法的言辞表示异议。
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但是,《大秦帝国》原著作者,孙皓晖,却对法家、对商鞅极为推崇。
孙皓晖对法家的推崇,貌似还不仅仅来自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热情。
他曾任西北政法大学、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因此另有一层「
学术
」角度。他从法律制度的角度来回望商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它(秦朝)的败亡,是因为秦始皇没有把商鞅确立的战时法律制度,转型为和平时期法律制度。」
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重新演说历史,还带着这样的遗憾:
战时「
为天征伐
」的革命力量,没能及时转化为执政的根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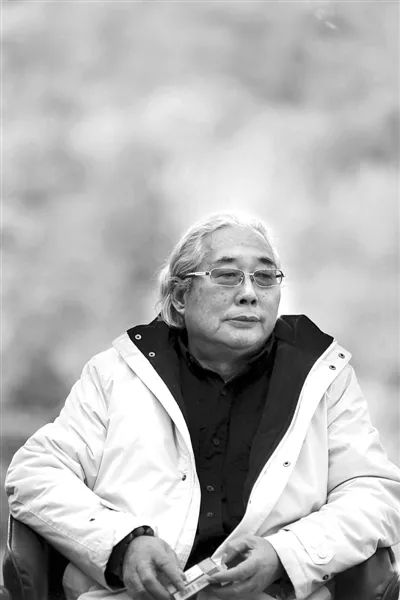
|
《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新京报记者王叔坤 摄。
图片来源:新京报
似乎是陆贾对刘邦所言「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的翻版。
然而,把商鞅的法家只视为「
马上得天下
」的手段,视为「
战时法令
」,包括商鞅在内的历代法家,都会不服气。
另一方面,把法家视为可以转型为和平时期的法律制度,似乎法家还能变成今人眼里的「
法治
」。
《大秦帝国》的真实意图
民国历史学家张荫麟在其著作《中国史纲》中对法家有过这样一段评述:
「别家讲政治总是站在人民的一边,替全天下打算。法家则专替君主打算,即使顾人民也是维护君主的利益。这是无足怪的,法家的职业本来是替君主做参谋。一个君主的利益没有大得过提高威权和富强本国,而且这些越快实现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