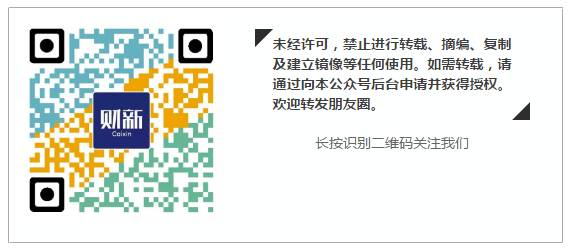“5·12”大地震后,隐藏在汶川崇山峻岭深处的夕格村被整体搬迁至成都平原上的邛崃南宝山镇。八年过去了,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羌族文化堡垒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现在,他们想要什么?
友情提示:全文约11000字,读完约需16分钟
5月12日,距离汶川县300多公里开外的邛崃市南宝山镇是个难得的晴天。
5月的南宝山还是雨季,往常都是阴雨绵绵,空气潮湿,棉被都极易发霉。头天还是阴雨天,5月12日一大早天放晴了,阳光照在南宝山木梯羌寨的金色招牌上褶褶发光。村口一块巨石上,红色字体上写“5•12地震异地安置纪念碑”。

在邛崃南宝山帮夕格羌人新修了一座现代化的羌寨,取名木梯羌寨,这是一个地震异地安置村。 图/财新记者 萧辉(下图同)
木梯羌寨是成都平原上一颗独特的羌族文化“活化石”。九年前的“5•12”汶川大地震地动山摇,把远在岷江上游深谷高山里的古老羌寨夕格村摇得支离破碎,2009年5月,全村249人离开羌人生息上千年的家园,整体搬迁到成都西部的邛崃市南宝山。如今他们是成都平原上千万人口中仅有的数百羌族人。
69岁的杨贵生一大早起床了,即使搬到这里八年了,他还是不习惯多雨的气候,从老家带来的猴头帽、羊皮鼓长了不少霉点。他的老家汶川,深山里气候凉爽干燥,皮料从不发霉。
杨贵生是一名“释比”,巫师的意思。释比在羌族人中是最有地位的人,他们能通鬼神,掌管祭祀招魂、驱鬼驱邪、祭山还愿等法事。猴头帽、羊皮鼓是杨贵生从师父手中传下来的,据说传了十几代,猴头帽檐黝黑发着油光,透出岁月的痕迹。

祖传的释比法器很少能用上,孤零零放在屋子一角,天气潮湿发霉,遇到晴天,释比杨贵生会点香请愿晒法器。
从汶川深山迁徙到邛崃后,杨贵生极少能用到他的祭祀法器。除了一年一度的羌历年演出,猴头帽、羊皮鼓大多数时候孤零零地躺在新盖的羌楼角落里,就像总是沉默着抽旱烟的杨贵生一样落寞。法器长霉点,杨贵生很是心疼,“祖师爷传下来的的东西不能弄坏”,因此在这个难得的晴天,杨贵生点燃香烛,小心翼翼请出法器,摆放在太阳下晒。
木梯村支书陈永全比平日起得早。这一天他的手机频繁响起,多是老家那边的干部和朋友发来的问候。8年前,陈永全在考察邛崃南宝山情况后,动了异地搬迁的心思,“至少南宝山交通方便,能把村民们从肩挑背驮中解放出来。”
2009年5月8日,他带着248名村民跨越高山和沟壑,在成都平原邛崃安了家。这是一次史诗般的“出埃及记”,他一心想带着羌人寻找一块安居乐业的家园。
在和记者的交谈中,他还是习惯叫老寨子的名字夕格村——那个隐蔽在海拔3000米深山里的古老羌寨,“夕格村”在羌语中意思是云朵上的羌寨。
八年过去了,47岁的陈永全头发白了一半,比原来也瘦了10多斤,但他从来不问自己:“我们搬出来,是对的吧?”
迁徙:告别世外桃源
木梯村的老人时时会面朝着北面,遥想深山中的故乡。夕格村位于汶川县龙溪乡3000米以上的深山里,是全县唯一不通车的边远村寨,仅有一条在悬崖峭壁间踩出来的崎岖碎石子山路与外界相通,这段山路距离最近的通车村庄有10公里,一般人要攀爬两三个小时。很少有外人进村,夕格村人也只是在需要买大米、盐巴等日用品时,才牵马下一趟山。

被废弃的夕格老寨子,如今成为牧马的地方。
与世隔绝的环境使得夕格村保存了最原始的羌族文化。2007年,阿坝师专研究羌族文化的教师陈安强到夕格村采风,从险峻的山路进入夕格村,他用“世外桃源”形容看到的一切:高山上草甸鲜花盛开,牛马点缀其间;龙潭坝前五座山峰耸立,村民称之为“五龙归位”,两条溪涧若龙吐水,由林丛淙淙而过,这是高处雪山融化的冰泉水,也是村民日常饮用的水。居民聚集点古朴的羌碉墙挨着墙,顶连着顶,房屋错落有致,阡陌纵深。

王龙清的石头房子位于高山草甸龙潭坝中,鲜花盛开,冰川融化的泉水淙淙流过屋前,俨然现代版“世外桃源”。
陈安强在村里住了一个月,挨家挨户的村民请他到家里做客,吃烟熏腊肉、摆龙门阵。村民们在坡度呈60度的田地里耕作,在山林里敬拜天地神灵,高兴时便扯开嗓子用羌语唱山歌、跳锅庄(羌族的特色舞蹈),日子简朴而快乐。
“20多年我遍访阿坝州的羌族村寨,夕格村的羌族文化传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陈安强告诉财新记者,“村民的衣食住行,都是活生生的羌族文化展示。”
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把夕格村撕扯得支离破碎,村里一半以上的房屋倒塌,没倒的房子也裂开成了危房。所幸村中仅有一个人因地震去世,而且是在别的村遇难的。“释比”杨贵生认为这得益于村民敬畏神灵,天神保佑夕格村。
但灾后重建面临难题。不通路,重建房屋需要的石料、木头只能靠人力和马、骡子驮上去,这是一项极为艰险的工程,夕格村的重建工程比别的村慢一大截。
村支书陈永全告诉财新记者,四川省政府在2009年出台地震安置政策,对那些失去耕地、在原地重建困难的村庄,在自愿的基础上可以申请易地安置。2009年3月,有一批青川县的地震移民搬迁至成都市下属的邛崃市南宝山,那里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因为监狱内部系统调整,劳改农场搬迁,留有大片国有土地,可以安置地震移民。
2009年4月,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组织多个地震受损严重的村庄代表去邛崃考察,陈永全也跟着去了。让他心动的除了这里离省城近、交通方便,还有一点:据邛崃的干部介绍,南宝山的高山茶叶一亩产值可以达到5000元,人均分二亩茶地,年收入就能达到1万元。而在夕格村,村民全部的收入靠在山里挖冬虫夏草等名贵药材换钱,一个家庭年收入仅5000元,日子贫穷拮据,到年底买敬神的酒肉还需要赊账。
回到夕格村,陈永全向村民宣传邛崃如何好:告别肩挑背驮,种茶叶远比挖草药赚钱,娃娃读书也方便了。陈永全甚至把自己在邛崃闹的笑话告诉村民,在高档宾馆里他第一次见到抽水马桶,他不知道该往哪里拉屎。
外面的新奇世界就在眼前,多数年轻人同意搬迁,但多数老年人不同意。“不去别人的地头,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陈永全的大舅子杨永富是不肯搬迁的顽固分子,他拒绝在“自愿搬迁书”上按手印:“下山有啥子好的,我们的大山里有虫草、贝母,那边的山上没有,也不能养牛、马,难道有了公路就能吃饱饭了?”
陈永全逐一上门做思想工作,反复开会,号召年轻人动员家里的老人。半个月后,村民终于就搬迁达成一致。
4月底做的决定,政府通知5月初搬迁。牛、羊、马等牲口不能带走,仅带必要的食物和生活用具。留给村民们变卖家产的时间只有十天。种在地里的玉米、土豆、蚕豆来不及收,留在地窖里的去年的土豆和玉米背下山去卖,还有带不走的桌椅板凳、牲口要变卖。
村民杨永顺告诉财新记者,那时候他和媳妇见天背着上百斤的粮食和家具,赶着牛、羊往返山下三、四趟卖东西。由于时间紧急,对方压价,只能贱卖东西。两头耕地的牛,每头足有七八百斤,光卖肉一头牛也能卖好几千块钱,最后作价每头1000元卖掉。
对杨贵生来说,卖掉他养了十年的马是件非常难过的事情。他称马为“孝顺儿”,马能驮粮食和盐巴,还能作为山路上的代步工具。平时杨贵生会牵着马去后山吃草,用羌语和马聊天。
马被买主牵走的那一刻,杨贵生把脸贴在马头上,“马的脸贴着我的脸,它眼睛里有眼泪,我也流眼泪,舍不得”。杨贵生还卖掉了留给自己和老伴的两副实木棺材,每副180元,“现在值好几千元”。
定下来5月8日出发。最后三天,杨贵生天天到母亲坟前哭。杨贵生和母亲感情很深,母亲36岁守寡,拉扯大他们兄弟四人,几年前96岁高龄去世。他边烧纸钱边哭:“妈妈,我就要永远离开你了,以后再也看不到你了。”
2009年5月5日,全村人聚集在玉帝神庙,最后祭拜祖先和神灵。杨贵生穿上全套行头,主持祭拜仪式,村民们跪在神庙前,杨贵生用古羌语唱诵经文,祈求神灵:“天上的神仙呀,为你献上神羊;敬神的时刻到了,我的呼吸是那样急促。天上的神仙哪,我们就要离开故土;请你跟着我们,一路保佑我们。”
搬迁的最后时刻,村们纠结带哪些东西走。杨贵生一定要带走的是师父传给他的释比法器和母亲的画像;杨永富决定把家里的神龛带走,“到哪里都要敬神”;杨永顺把家里的火塘铁圈和铁锅带走,“没有火塘,怎么生火做饭,一家人聚在哪里闲聊”。
陈永全忙着做村民工作,只带了铺盖走。到现在他还后悔没拿走家里的神龛,“那是与故土联系最紧密的东西”。
离开的日子到了,在那条走过无数次的羊肠小道上,老人牵着小孩一步三回头,中年人沉默地背着锅碗瓢盆和家具,全村人浩浩荡荡下山了。杨贵生凄凉的古羌语唱经回荡在山谷间:“天山的神呀,地山的神呀,我们要离开故土,我们将要爬过九十九座山脊,没有云雾没有雨,没有飞石没有猛兽,我们依然供奉你。”
独立纪录片导演高屯子跟拍了夕格村迁徙的过程,他说:“那是我听过的最为幽怨哀伤的曲调。”
陈永全忍着没有回头。“决定搬出去,就没有回头路走了。”背倚五龙,面朝深峡的夕格老寨子就丢在身后,从此他们有一个崭新的身份:邛崃人。
羌人没有自己的文字,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他们历经过几次大迁徙。羌人曾经纵横在华夏西部广阔的地带,及至唐宋与中原文明相遇,一部分羌人融入汉、藏、蒙古等民族之中,另一部分羌人在战败后越来越深地躲进大山,到现代只剩下岷江上游和湔江上游的高山深谷里,聚居着不到30万的羌人,与现代文明隔绝,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
汶川大地震的重灾区落在西南羌人最后的聚集区,这个经过无数次战乱迁徙的民族不得不再次外迁。与祖先相比,他们逆向迁徙,这一次他们将遭遇什么,羌民们心中都没有底。
适应:与现代文明相遇
杨永顺没有用上他的铁锅,村民们也没有用上他们的铺盖。
2009年5月,在邛崃的临时接待点鲁川小区板房里,政府给每户羌民准备好了崭新的炊具和铺盖。村民们第一次用上了电磁炉和电饭锅。杨贵生还闹了一个笑话,淘米插上电,他忘记按煮饭的按钮,全家人等了两个小时也没有吃上早饭。
不适应的还有亮堂堂的厕所。过去村民们习惯在木板搭的简易茅房上厕所,换成干净的旱厕反倒不习惯。老年人说:怕把厕所弄脏,使劲憋着,拉不出屎,悄悄到小区附近的灌木丛,找个隐蔽的地方才拉出屎来。
夕格村的羌族人很少洗澡,有些老年人一生没有洗一回澡,身上浓浓的汗味。邛崃天气热,空间狭窄,体味很大。陈永全号召村民洗澡,有些老年人不习惯,由子女摁着脱了衣服,拉到淋雨喷头下冲洗,渐渐也就习惯洗澡了。
最难熬的是搬下山的第一个清明节。当地汉人在祖坟上挂亲,纸钱烧得亮堂堂,羌人却没有祖坟可以祭拜,只能遥想大山里杂草丛生的祖坟,暗自垂泪。
刚开始和汉人接触,语言沟通困难,一些老年人只会讲羌语,听不懂汉族人的方言普通话,看到生人就躲。村支书陈永全负责和汉族人干部对接,对于汉族干部的普通话他经常听得一头雾水,对方交待工作,他连蒙带猜,口头应诺:好,好,好,但实际并没有听懂。对方反复交待,多次沟通,他才知道怎么做。南宝山镇党委书记杨永胜告诉财新记者,做羌族地震移民的工作,比别的汉族村庄多花了两倍的功夫。
很多羌族人是第一次到城市,完全找不着北。到邛崃的第一个月,一位老人从小区走出去,不知道怎么回来,走丢了。陈永全心急如焚,向政府报告,邛崃出动了100多警察和社区干部,沿着大街小巷找走丢的老人,最后老人被热心的群众送了回来。
刚开始,邛崃政府动员几十家企业来鲁川小区招临时工,有纺织厂、啤酒厂、建筑公司,但大多数羌族壮年劳动力不识字,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数数也数不清楚,打了几天工就做不下去了。
在鲁川小区过渡四个月后,2009年9月,夕格羌民们搬到南宝山,改名为木梯村。木梯村所在地原是劳改农场,海拔在1400米,村民们分到人均两亩茶地和半亩菜地。
村民们此前在老家没有种过茶叶,政府为他们买好茶树苗,请技术员教他们种茶,一村老小们热火朝天地种起了茶树。然而,2010年、2011年连续两年遭遇雪灾天气,四五十厘米的积雪覆盖树苗,很多茶树冻死了。补栽过后,又缺少种植和管理经验,茶园内杂草丛生。村民们对种茶失去信心,2011年把茶园整体承包给一家茶叶公司,收取每亩地300元一年的转租费用。一个人在茶地的人均年收入只有600元,与先前邛崃干部宣传的种茶人均年收入1万元相去甚远。村民告诉记者,一般茶叶三年就能采摘,但他们种的茶叶直到去年第七个年头才有少量产出,种茶叶以失败告终。
村民们又想种玉米和洋芋,但是南宝山土地贫瘠,雨水多,玉米刚抽穗就烂在雨水里。种紫色土豆,原来在夕格寨子里土豆丰收时一块土豆有成人的拳头那么大,而在邛崃收获的只有拇指大。原来在夕格村20斤土豆种可以收500斤土豆,在南宝山只能收不到100斤。村民们失去了种地的热情。
南宝山可利用空间狭窄,又不能养牛养马,正好应了杨永富当初的那句话:“下山有啥子好的,难道有了公路就能吃饱饭了?”每年冬虫夏草生长季节,杨永富又和妻子返回汶川的大山里挖虫草,一年收入能有五六千元。
更多的壮年劳动力只能到邛崃周边的建筑工地打零工。但是语言沟通、思维习惯与汉族包工头存在差异,他们并不受待见。33岁的王良军告诉记者,他刚开始做建筑小工,汉族包工头喊他“拿灰过来”,王良军不懂“灰”是什么,他连蒙带猜把一包干水泥拿给包工头,被劈头盖脸的臭骂“脑子不好使”,原来包工头让他拿调配好的水泥浆。
跟汉族人一边干活一边抽卷烟不同,羌族人做活时踏实,做累了会停下来,蹲着抽一杆烟。“被包工头看到了不高兴,就会训斥我们懒。”王良军说,“我们干体力活做得巴巴实实,但外头的老板不了解,训斥我们,我们受不得委屈,会回嘴,老板更不高兴了,说羌族人不服管,以后就不用我们了。”
打零工不可持续,木梯村民们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头三年由政府包吃,每个月政府会派车到村口发粮食、油和肉。后来改为发低保,从每月每人90元,到179元,2016年涨到309元,一个人一年接近4000元,成为一笔稳定的收入来源。
村支书陈永全觉得搬到邛崃八年了,还靠吃低保实在有点丢人,老家来的亲戚告诉他,他们山脚下的垮坡村种了李子和樱桃树,一家年收入能达到五六万,好的一年收入能到十多万。陈永全盘算着,好歹要比原来的日子过得好,不能输给老家的其他村寨。发展特色羌族文化旅游成为陈永全的“救命草”。
2013年,时任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到木梯村调研,拉着陈永全的手问有啥心愿。陈永全说,希望把寨子改造成传统的羌族特色房子,以后靠民俗文化旅游发展。黄新初拍板同意给木梯村做风貌改造。成都干部来了一批又一批开现场办公会,2014年下半年启动2000多万专项资金,给木梯村民修了崭新的羌族特色房子“羌碉”。2015年春节,木梯村搬进了新的羌寨,村民们把房子改做宾馆,接待游客,2016年收入100多万元,户均收入3万元左右。

没有游客的时候,羌人们坐在自家院子前闲聊。
但陈永全一直担忧,每户单搞“农家乐”不成气候,还会形成邻里间恶心竞争,希望政府帮助引进投资商,整体打造羌族特色文化旅游村。
“目前还没有形成品牌,希望能有一个文化广场,介绍我们羌族的文化特色,有一笔资金养起来一个固定的羌族文化表演团队,展示我们羌族文化特色。”陈永全说他的目标是每户一年收入能达到10万元,摘掉低保的帽子。
离陈永全的目标显然还有一段距离。5月12日的这个周末,木梯村来了不少观光客,住宿的客人并不多,有几个从成都来的年轻游客在羌寨里转了五分钟就出去了,一个游客说:“除了几个石头房子,没啥好看的,看不出啥羌族文化。”

木梯羌寨成为旅游景点,游客争相与羌寨大爷合影。
邛崃市文体局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木梯羌寨位于南宝山旅游带上,政府正逐步把南宝山打造成户外旅游和消夏避暑之地.“旅游开发有一个逐步的过程。”他说,南宝山的旅游正在起步阶段,“等到整个南宝山旅游发展起来,也会带动木梯羌寨旅游发展”。
已经调入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陈安强认为,木梯村的特色是独一无热的羌族文化宝库,村民们就是行走的羌族文化符号,政府要想办法充分释放他们的活力。
杨永顺则满面愁容地告诉记者,日子是比过去好一些了,但压力更大了。“以前在山里靠山吃山,自给自足,现在啥子都要钱。以前凭的是体力,现在拼脑力,我们又没有汉族人脑子灵活。”杨永顺把家人住的地方腾出来改装成接待客人的标准间,他和孩子们睡在临时搭的三四平米的阁楼上,他自嘲为“钻狗窝”。平时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们也不去住客房。
“我们身上有股味道,我怕我们住进去,客人再来住,会嫌弃。”杨永顺说。
20岁的陈文举也认为没有以前在山林里开心了,锅庄舞也跳得少了。“现在生活压力大了,没心思跳舞。在水泥地里跳舞,也找不到感觉。年轻人偶尔跳个舞,还会被大人说,跳啥子哟,没事干去找点事情干。”他说,“以前在山里虽然穷,但穷开心,现在满脑子都想着要怎么去挣钱。”
发展:从“文盲村”到“职高村”
尽管有抱怨,陈永明认为全村在教育上有翻天覆的改变。
今年60岁的陈永明在夕格村小学当了30年教师。村小学有一至三年级的三个班,据他统计,自他开始教书的1979年到2000年前后,村里的适龄儿童一大半没有跨入过学校的门,能坚持读完小学三年级的不到30%,能下山到乡小学读完小学的更是凤毛菱角,外界称夕格村“文盲村”。
即使义务教育免去学费,村民还是很少送自己的孩子下山读小学,因为穷交不起寄宿费。这种情况直到2000年后阿坝州实行“两免一补”政策才得到改观。
村干部有确保义务教育指标完成率任务,陈永全说过去在夕格村经常为这项任务发愁。家里穷实在读不起书,小孩也是放羊的劳动力,村干部只能动员他们去学校报名把名字登记上,实际上是没有来学校读书的。
在夕格村,30岁以上的村民,一大半是不会写自己名字的文盲。村支书陈永全的妻子杨翠花,今年47岁,她有兄弟姊妹八人,仅有二哥进过村小学念书,其他七人均没有读过一天书。
搬到邛崃南宝山后,政府对羌人的教育给予特别关照,免去所有学杂费并提供补助,所有的小孩都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并接着进入职高念书。

幼儿园内,有6个羌族儿童和汉族学生一起读书。
陈永全的大儿子陈文举今年20岁,初中毕业后在四川省交通管理学院读职高,在成都地铁公司做了一年安检员,现在回到家里做厨师,帮助管理农家乐。18岁的小儿子陈文学在读机电专业职高,目前在一家建筑机械公司实习,每月能拿到2500元工资,准备毕业后就留在该公司。
21岁的女孩杨庆利在四川矿产学院念电子商务大专,明年毕业,她计划毕业后回家帮父母管理农家乐,做导游接待游客。父母不认字,不会用手机收款,她想给游客提供更现代化的服务。“我们这一代比父母那一代读书多,自由选择的空间大。”
木梯村还有一个巨大的改变,生活富裕了可以自由选择婚姻。,过去的夕格村是汶川县有名的穷困村,不通路,外村的人不愿意嫁过来。下山相亲,女方看小伙子长得不错,一听是夕格村的就瞧不上。几百年来的习惯是本村人内部订娃娃亲,哪家生了女娃,另一家有男娃的家庭就来订亲。男娃比女娃多,就有人打光棍。陈永全介绍,地震前,夕格村有十多个大龄男青年找不到对象。搬到邛崃后,与当地汉族人通婚,那些光棍都娶上了媳妇。
村民杨彩华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当年杨彩华37岁,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男孩12岁读四年级,女孩9岁读一年级,日子艰苦。搬到邛崃后,经人介绍,她又嫁给一个南宝山镇的本地汉族人,丈夫人很实在,对她和孩子都好,两个孩子目前在读职高,前年又添了一个女娃。
杨彩华觉得搬到邛崃后日子好过了很多。“等两个孩子职高毕业找到工作,我就轻松了。如果不下山,日子很难过,娃娃很难读完小学。”
凋零:没有传人的释比
杨贵生最发愁的不是营生,而是没人愿意跟他学艺了。他经常望着静静躺在角落里的释比法器,心里苦闷:“祖师爷传下来的手艺,难道要在我手里失传,没有脸去见祖师爷呐。”
杨贵生14岁时跟着舅舅陈冰清学释比手艺,白天和大家一样做农活,晚上学释比文化。有很多东西要学,画彩画、划水、踩铧头、坐红锅、踏刀山,这些只是表面上的绝技,最重要的传承古羌语经文。羌族没有文字,正是通过释比把氏族历史、宗教典籍、法事技艺、天文知识、医药知识世代口口相传。在羌族人的祭祀、祈福、驱魔、婚嫁丧娶等活动中,释比通过唱诵经文,担当着羌人与鬼神、自然之间的交流媒介。
羌族文化研究者陈安强认为,释比文化能够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代代相传数千年是个奇迹。他曾花了半年时间和杨贵生一起整理羌族史诗《刮窝》(天路之歌),讲述羌族人创世纪及古代迁徙战争的历程。杨贵生能连续唱20个小时,容量达到15400行,长度超过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
过去在汶川,杨贵生是远近闻名的释比,四邻八乡的羌人在有祭祀、嫁娶、上梁下基脚等重要活动时,都会请杨贵生主持,每次给100元“份份钱”。

杨贵生展示2008年汶川县政府颁发给他的“古羌释比文化传承人”证书。
杨贵生记得最风光的一回是2006年,汶川县政府在萝卜寨举办羌族文化旅游节,开场表演羊皮鼓舞,杨贵生站在高高的祭台上敲响羊皮鼓,数百名群众舞蹈演员跟着鼓的韵律摆动。那一刻,他眯着眼睛,唱着古羌语经文,鼓点越敲越快,“神降临在我身上。我不是在表演,我是在与神对话”。
表演之前,杨贵生给舞蹈演员们上了一个月课,演员们毕恭毕敬尊称他“释比老人”,“相当于你们汉人里的教授。”杨贵生不无得意地说。2006年4月,汶川县政府还给杨贵生颁发了释比文化传承人的证书,他和阿坝州州长、汶川县县长握手,一起吃过饭。
搬迁到邛崃后,风光不再,杨贵生成了一个抽着旱烟、晒太阳打瞌睡的普通老头。很少有人请他做祭祀、驱邪、看病,只有每年一次的羌历年他会被请出来主持祭祀大典,“比过去也潦草很多了”。
“这里的人不信神,我在这里的空气里也感应不到神。”杨贵生说,过去在夕格村,村民们每到节庆日,要祭拜水井神、树神、土地神、羊神、家神等等。老寨子村口的那棵古树有上千年历史,四个壮汉合抱才抱得拢树干,树荫下放有一口古井。陈文举记得,当他还是小孩子时,大年初一早上,他会和父亲到古井旁上香烛祭拜水井神和树神。这些仪式在邛崃都省略了,“在这里,我们很少再感应到自然和神灵,心静不下来了。”
2009年,杨贵生被邀请到香港参加慈善表演,他印象中的香港楼房很高,巷子很深很窄,见不到阳光,空间狭小,“空气中也闻不到神的味道”。
在夕格村,杨贵生还要承担医生的角色。羌族人相信生病了是有邪魔附体,请释比老人“划水水”念咒语,就能驱邪驱魔。但搬出大山来到邛崃后,没什么人再找杨贵生看病,病魔也纷至沓来。据陈永全介绍,在邛崃的八年间,整个村子有12人去世,其中六个是青壮年,患肝癌、喉癌、脑癌等病。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有近20人患胆结石、肠炎等到邛崃的医院动了手术。而以前在夕格村,十多年间只有两三个年轻人在医院做过手术。大多数时候病了就到山上采草药吃,或者请释比老人“划水水”。杨贵生自己也未能幸免,去年在医院检查出冠心病,每个月要服药。
杨贵生还有一件烦心事,2009年10月,阿坝州登记“非遗”传承人,汶川县有30名释比享受政府津贴,其中国家级每年补助1万元,省级每年补助5000。但2009年5月杨贵生的户籍也迁出汶川县,不能参加阿坝州的评比。“如果他还在汶川县,以他的地位肯定能享受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补助。”村支书陈永全说。
杨贵生找邛崃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对方告知,邛崃没有申请羌族文化“非遗”立项资格,因此没有这方面的经费。羌族文化学者陈安强多次向政府相关部门呼吁,给予杨贵生津贴补助,均没有成功。
财新记者近日向邛崃市文体局了解此事,一名官员告知,因为地域差异,以前没有申请到项目资金,目前邛崃市准备和省里探讨,想办法解决释比老人的津贴问题。
在夕格村,杨贵生有四个徒弟,但到木梯村,徒弟们都没有心思学了。杨贵生的大儿子杨永顺跟着父亲在夕格村学了两年释比经文,现在全忘光了。他告诉财新记者:“释比在汶川很受尊敬,也是一门生计。但在汉族人这里没有实际用处,我父亲都没有人请了,我们学了有啥子用哟?还不如老老实实打工挣钱。”
杨贵生几次找村支书陈永全,让他动员青年人学释比,陈永全摊摊手表示没办法。
陈安强认为释比是羌族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他们掌管着文化遗传密码。“这一代释比去世,没有传人,以后谁还能口述羌族历史,谁还能主持祭祀仪式?羌族文化会迅速消亡。”陈安强认为,释比本身没有能力应对现代化的冲击传承下来,但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他向政府建议传承释比学徒的三年计划:政府设立专项资金,给每一位愿意学习释比技艺的学徒每年二万元补助,为期三年,三年潜心学习就能培养出一名释比。
“国家是重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并拨了大笔经费,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国家拨了2000多万给他们修房子,更应该拿出一笔钱保护释比文化,几十万就够了。”陈安强强调。
留守:老羌寨最后一户遗民
八年过去了,汶川夕格村的羌人已经习惯了自己被称为邛崃木梯村人,故乡逐渐远去。但还是有一户人家放弃了木梯村现代化生活,回到被废弃的深山夕格村里。
杨贵生的哥哥杨水生今年77岁,也是一名受人尊敬的老释比。八年前,他随大部队下山,仅在邛崃住了两个月,他就和老伴返回夕格村。四年前,杨水生的二女儿杨翠云和丈夫王龙清也返回老寨子居住。一家四口在断水断电的老寨子过着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没有自来水,喝雪山融化的山泉水,溪水潺潺流过家门前;没有电,点油灯,吃完晚饭一家人围在火塘旁边聊天。平时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种菜、喂猪、放羊,自给自足。

杨水生的老伴经常望着群山发呆,她很想念在山下治病的丈夫。
杨水生是汶川远近闻名的释比羌医,享受政府每月补贴的1000元钱,有时候还会被请下山去给人治病。不幸的是,今年3月,杨水生在捡柴时摔断了脊椎,被人抬下山,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被送到邛崃木梯村的大儿子家休养。财新记者在木梯村见到杨水生老人,他半瘫痪在床,精神状态不佳,脸有些塌陷,那是年轻时被黑熊拍了一巴掌把鼻子削去了。老人家盼望着回到生活77年的夕格村,但他喃喃自语:“怕是回不去了,释比法器还放在老家。”
杨水生说,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搬来邛崃,九年前临走时,一家人去给母亲上坟,他故意没去。“我不会离开的,我要守着祖坟和神灵。”为了不影响村人的情绪,他跟随大部队下山,又很快搬回山里住。
“山下没有神庙,没有神灵,山里才有神。”他的语气很坚定。
杨水生从山里下来治病,老伴王珍芬和二女儿、女婿还住在夕格老寨子里。5月16日,财新记者专门去夕格老寨子拜访他们。开车抵达龙溪乡,在悬崖峭壁上爬了三个小时山路,进入龙潭坝,五座山峰耸立在眼前,这就是村民所说“五龙归位”的地方,高山草甸上铺满蒲公英,两匹棕色的马在草地悠然散步,一副田园牧歌的景象。

黄昏,王龙清放羊归来,他用羌语吆喝驱赶羊只归家。
正是黄昏,遇上放羊归来的王龙清,他赶着60头羊回羊圈,山谷里回荡着他悠扬的羌语吆喝声。一会儿,杨翠云也从深山里摘虫草回来。在4000米以上的阳顶山上,有珍贵的冬虫夏草,此时正是虫草采摘季节。杨翠云当天的收获只有一根虫草。雪还没有融化,虫草很难采,“能采到一根已经算不错啦,前面九天我都剃了光头”。

杨翠云在整理晒干的虫草,这是她1个月来的收获,26根虫草,平均一天采不到一根虫草。
采虫草是艰苦的,杨翠云告诉记者,早上天刚亮,她就背着馍馍出发,穿上胶鞋和毛裤,山上很冷,要爬四个小时山路,走到雪线以上才有虫草。找四个小时虫草,然后下山还要走四个小时,要赶在天黑前下山。去年,杨翠云在山里采虫草还遇到黑熊,“我吼它,它就跑了。”
75岁的王珍芬在家中已经把火塘烧旺,把早上做的饭菜热好,等着劳作回来的女儿女婿一起吃饭。晚饭吃的是野生的蕨菜和烟熏腊肉,蕨菜是杨翠花采药时从山上带回来的。

夕格羌寨夜晚没有电,杨水生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烤火聊天。
吃完饭后,一家人坐在火塘旁聊天。王珍芬说,“还是山里的生活好”,不过她也惦记在山下养病的杨水生。杨翠花也认为,“山里的生活自在”,但是住在邛崃的大儿子有两个娃娃,大的五岁,小的才一岁,儿子儿媳要忙着经营家中的农家乐,多次喊她下山去带孙子。
杨翠云和王龙清商量,等今年秋天把羊子都卖了,就返回邛崃照顾孙辈。王珍芬也想回邛崃照顾老伴。到那时,夕格村就成为真正的空寨子。
在木梯村,村民们闲聊时经常辩论:到底是夕格村好,还是木梯村好?有人认为夕格村好,生活自由自在,顺应自然,没有城市生活的压力大;有人认为木梯村好,比过去富裕很多了,干活也没有过去辛苦了。但谁都没想过要再返回夕格村生活。
释比杨贵生经常会回忆在山林里祭神的场景:密集的鼓点,神灵附身的时刻。但他知道山林再也回不去了。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找个徒弟,把他的羊皮鼓、猴头帽、古羌唱经传承下去。
村支书陈永全从来不问自己:当年力主搬下山是对是错。八年来,他从没有回老家夕格村探访,老家的亲戚告诉他,他妈妈的坟被野猪拱坏了,他也不在人前流泪,只是夜晚偷偷抹泪。
这个倔强的羌族汉子,在村民指责他时也会偷偷抹泪,只是从不辩解。八年前,他劝全村人下山,就是想过上富裕的生活,不再被人看不起。如今木梯村已经摘掉“文盲村”“光棍村”的帽子,他还想让这个平原上的羌人寨子变成“富裕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