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为流传的历史读物《明朝那些事儿》,详尽记述了
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被俘于瓦剌时,锦衣卫
袁彬
舍身相护,和他相依为命的故事。然而,《明事》却有意略过了朱祁镇复位后,袁彬被奸臣陷害,下狱拷打,性命几乎不保,多亏一个和他素不相识的油漆工匠杨埙上书,激起天下公愤,才迫使朱祁镇将袁彬从轻发落,改为免职流放的后续故事。
土木堡之战,数十万
大军溃败,
朱祁镇身边信臣,非死即逃。唯有一个锦衣校尉袁彬留了下来。
这时的袁彬,已接替父职做了十年的校尉而不得升迁,年纪也到了中年;其个人奋斗前途显然非常有限,绝对不属于大明帝国官场中春风得意的那类人。不论从哪方面,都是几十万北征大军中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可是
疾风知劲草,板荡见忠臣
,变幻莫测的历史进程将这个小人物推上了大舞台,他也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成为后世记述这段历史时,不可缺少的一份暖色。
朱祁镇之前信用的一个女真族太监喜宁,投靠瓦剌人首领也先,成了侵略者手下红人,尽告边关守备详情,给瓦剌军出谋划策,同时对朱祁镇各种迫害刁难,欺凌故主。
汉奸、太监:喜宁

袁彬顶着喜宁的压力,对朱祁镇不离不弃,将他照料得无微不至。
朱祁镇在寒夜难以入眠,是袁彬解开衣襟帮他暖脚;每逢随军到车马不能行的泥泞地,是袁彬背着朱祁镇前行;
朱祁镇遥望星空长吁短叹时,是袁彬时时宽慰,打消他寻死念头;
袁彬阻止朱祁镇自杀:

朱祁镇和瓦剌人的各种交涉,都由袁彬做为中间人一力承担,尽心竭力为他筹谋;
朱祁镇写给孙太后、代宗朱祁钰、众群臣的书信,都是请袁彬代为起草和执笔;
也先想招朱祁镇为妹婿,又是袁彬苦口婆心劝说,让朱祁镇婉拒此事,因此不致有“生为俘虏,却贪恋敌寇女色”之嫌,损伤自己声誉;
也先宴请朱祁镇,袁彬挡酒

他的竭诚无私和赤胆忠心,让朱祁镇对他依赖备至,如幼弟对长兄一般依赖,将他当做了自己的生活支柱。两人出入同行,寝则同床,几近形影不离。
喜宁因此怀恨在心,有次唆使也先,要将袁彬五马分尸。朱祁镇放下大明天子尊严,苦苦哀求,跪地哭诉,让也先饶了袁彬一命。还有一次袁彬受了风寒,朱祁镇急得用身子紧紧抱住他,发了一身大汗,竟然好了。苍天亦庇佑善人矣。
袁彬保护朱祁镇,怒斥喜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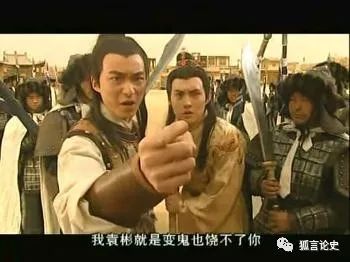
也先俘虏朱祁镇后,野心膨胀,更欲南侵大明,挟制朱祁镇攻宣府、攻大同,令他在关下叫门。幸好两关守将拒不开门。其后,喜宁领瓦剌军改道攻紫荆关,四日破关,杀守将孙祥,打通了直抵北京城之路。一路沿途不知多少黎民百姓,因此惨遭瓦剌军蹂躏。
又是袁彬定下计策,诱使喜宁充任替瓦剌勒索大明的使节,同时密信于谦,请于大人帮忙斩了这个奸佞小人,也为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和瓦剌军的败退,除掉了一个狡猾劲敌。
这样相依为命的日子持续了一年,朱祁镇回国了,不出意料地被囚入南宫。袁彬也理所当然地仅升一级,被授予锦衣卫百户,他的功劳和忠诚,在瓦剌一年的传奇经历无人在意,或刻意不被在意。就像通常那些偶尔跃入历史大潮的小人物一般,终究要回到碌碌众生中去。
几年后,夺门之变,朱祁镇复辟为帝,改元天顺,立刻对袁彬升官加爵,让他掌管锦衣卫,为都指挥,所请之事无不听从,各种厚赏。先赐给他原内阁辅臣商辂的居所,又特意为他别建宅院。还让自己母家的外戚出面,给袁彬续弦主婚,并时常召入宫中,谈论当年患难时事。
可惜,故事到这里发生了转折,不再是一个蒙难皇帝和护驾忠臣终得圆满的童话故事。
大明天顺一朝,朱祁镇经历瓦剌囚俘、南宫岁月,他不信群臣,不信宗亲,而只信厂卫,大肆以特务统治来威慑百官。
逯杲
和
门达
这两个参与夺门之变的锦衣卫,便成他最信任的耳目和鹰犬。
逯杲和门达秉承朱祁镇意旨,不断打击石亨一党,最终铲除了这个夺门之变大功臣、当时头号名将。
从此他们势倾朝野,文武大吏、富家高门多向他们进献妓乐货财,以求获免,连亲藩郡王也不例外。不肯行贿的人,逯杲和门达就将他们严刑逼供成狱。
其中最匪夷所思的一案,他们竟诬陷宁藩的弋阳郡王
朱奠壏
母子乱伦,事关皇族声誉,朱祁镇派驸马都尉薛桓和逯杲一起调查,找不到任何实据,宁王朱奠培也力证此事纯系诬告。
事情闹大了,朱祁镇怒责逯杲,逯杲惧罪,立刻坚持原见,称确有此事。朱祁镇“不得已”,为了保住这个得力鹰犬,竟然颠倒黑白,将错就错,处死朱奠壏与其母,焚二人尸骨。抬尸出来时,刚好天降雷雨,平地水深数尺,天下人皆认为是冤情激怒天地所致。
【天顺五年五月戊辰先是,锦衣卫指挥逯杲奏发江西弋阳王奠壏败伦事,既而有旨令体审,复以无是。事闻,上怒,即遣敕责问杲,杲惧得罪,仍以为实。上不得已,命王母子自尽,曰:无污我宗室。方舁尸出焚时,雷雨大作,平地水深数尺,父老无不惊愕,以为逯杲上罔朝廷,诬陷宗室,故有此异云。】——《明英宗睿皇帝实录》
【初,锦衣卫指挥逯杲听诇事者言,诬奠壏烝母。帝令奠培具实以闻,复遣驸马都尉薛桓与杲按问。奠培奏无是事,杲按亦无实。帝怒,责问杲。杲惧,仍以为实,遂赐奠壏母子自尽,焚其尸。是日雷雨大作,平地水深数尺,众咸冤之。】——《明史·列传第五·诸王·宁王系》
朱奠壏是宁王朱权之孙,明太祖朱元璋的曾孙,和朱祁镇血缘并不算远的堂叔。堂堂天潢贵胄,仅仅因为得罪了朱祁镇信用的佞幸,便落得个背负污名冤死,尸骨无存的下场。这就是朱祁镇复辟后的天顺朝,其特务统治之恐怖,可见一斑。
朱祁镇能制衡和最终铲除“夺门功臣”石亨、曹吉祥等,依赖的就是其大力扶植的锦衣卫。等到曹吉祥叔侄举兵造反时,杀了逯杲后;门达便成为朱祁镇维系其特务统治的最大臂助。他秉承朱祁镇意旨,广布旗校于四方,短短几年便制造多起冤案,按察使、参政、巡按这级地方大员被他罢免和下狱无数,竟已成当朝头号权臣。到最后,满朝文武就剩下袁彬和内阁首辅李贤两人,不肯对其顺从,因而成了门达的眼中钉而深恨之。
门达查访到袁彬的继室之父千户王钦骗人财物,便奏请朱祁镇,将袁彬定为此案主使,下狱,然后判决袁彬徒刑,需花钱自赎,还复原职。
(
《明史》误将写为王钦写为袁彬妾父,其实此人是朱祁镇舅舅孙显宗的姻亲,这门亲事还是朱祁镇拉郎配的……,所以如果说王钦有罪,主使人明明是皇帝朱祁镇自己,十足的黑色幽默
)
这一投石问路后,门达认定袁彬自持的护驾旧恩已不足道,便再接再励,依次给袁彬加上了受贿请托、收受逆党石亨曹钦等人贿赂,用官府木材建私宅、向督工的宦官索要砖瓦、夺人子女为妾等等莫须有罪名,严刑拷打,对袁彬严刑逼供,此时年近花甲的袁彬,被拷打得遍体鳞伤。
对此,朱祁镇只一句话,「随便你怎么整,人别弄死就好,给我活的就好。」
【时门达恃帝宠,势倾朝野。廷臣多下之,彬独不为屈。达诬以罪,请逮治。帝欲法行,语之曰:“任汝往治,但以活袁彬还我。”达遂锻炼成狱。】
天下人都知道袁彬是冤枉的,都在为皇帝当年的恩人落到如此下场而不平,可惜「内外咸冤之,莫或敢发也」。
这时,一个和袁彬素不相识的油漆工匠
杨埙
,另一个在帝国亿万生灵中犹如草芥的底层小人物,因此愤然不平,击登闻鼓冒死为袁彬诉冤,上疏更直斥大明天子本心:可还记得袁彬当日「保护圣躬,备尝艰苦」之功?
朱祁镇之前为表示自己如何知恩图报,将袁彬从百户提拔为锦衣卫主管缇帅时,把他护驾之功广而告之天下。因此袁彬在瓦剌之功,不止杨埙知,天下人人皆知。
袁彬是什么样的人,他犯没犯门达定的那些罪状,难道朱祁镇心里还不清楚么?原本
并不需要任何外人去上达天听,以诉其冤。
杨埙上书,
与其说是诉冤的,不如说是代表当时敢怒不敢言的天下臣民去抗议的。
「陷彬于死虽止一夫,但伤公论,人不自安」更是诛心之论。
袁彬一命于国家政事本是一件小事,可一个忍心如此对待自己大恩人的君主,心性实在太过可怕,足以令天下所有人不寒而栗。
袁彬一命于国家政事本是一件小事,可一个忍心如此对待自己大恩人的君主,心性实在太过可怕,足以令天下所有人不寒而栗。
【正统十四年,驾留沙漠,廷臣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乃能保护圣躬,备尝艰苦。及驾还复辟,授职酬劳,公论称快。今者无人奏劾,卒然付狱,考掠备至,罪定而后附律,法司虽知其枉,岂敢辨明。陷彬于死,虽止一夫,但伤公论,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审录,庶得明白,死者无憾,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草茅,身无禄秩,见此不平,昧死上言。】——杨埙《上袁彬事疏》
ps:
历朝历代在国都或陪都设有登闻鼓,由专人管理,一有冤民申诉,皇帝必须亲自受理,官员如有从中阻拦,一律重判。小民之冤,亦可因此上达天听。
明太祖朱元璋沿袭此制。所以杨埙即使只是一个毫无背景的漆工,也能仗义击鼓鸣冤。
直到清朝才特别规定,击鼓者不分是非,先先廷杖三十,以防所谓“无端刁民”的“恶意上访”。而且“必关军国大务,大贪大恶,奇冤异惨”才能击鼓,否则重罪严惩,登闻鼓制从此形同虚设。
朱祁镇不得已,却令门达审理此案。门达拷打杨埙,用尽酷刑,逼他自称是首辅李贤指使,欲借此案将李贤和袁彬定为一党,好将朝中异己一网打尽。
杨埙假意顺从,却在午门外众臣会审时翻供,当众揭发门达如何污蔑大臣,同时袁彬也历数门达纳贿情状。门达以为大势已去,气极无言,几乎垂头待死。
岂知正义终究还是没有伸张!
朱祁镇和朝廷法司最后的裁定,是袁彬叛处绞刑,输财赎死,贬去南京,之前朱祁镇特命修建的居所也被拆毁;杨埙诬告门达,本应处斩,从轻改禁锢。
【拷掠埙,教以引贤,埙即谬曰:“此李学士导我也。”达大喜,立奏闻,请法司会鞫埙午门外。帝遣中官裴当监视。达欲执贤并讯,当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讯,埙曰:“吾小人,何由见李学士,此门锦衣教我。”达色沮不能言,彬亦历数达纳贿状,法司畏达不敢闻,坐彬绞输赎,埙斩。帝命彬赎毕调南京锦衣,而禁锢埙。】
【达因是欲尽去异己者,乃缓埙死,使诬少保吏部尚书华盖大学士李贤指使。埙佯诺之。达遂以闻会三法司,鞫于午门前,埙乃直述,所言皆由己出,于贤无预。达计不行,而彬犹降黜,居第尽毁。】
——读史至此,竟有荒诞之感,实不知当年在瓦剌和朱祁镇相依为命的,究竟是袁彬,还是门达了。
仅仅是因为朱祁镇天性凉薄、忘恩负义么?怕不仅如此。
朱祁镇对袁彬,并非是简单的患难之交不能共富贵。朱祁镇如果真是无法面对瓦剌那段屈辱过往,直接把袁彬调往南京,安排一个闲职,送他一场富贵,没有任何人能说他不是。
朱祁镇复位后,一开始给了袁彬很多厚待,正是期望袁彬能和瓦剌时一样,和逯杲和门达这些人渣败类一样,做自己最得力的鹰犬爪牙,来控制朝政和整个帝国,而袁彬有着自己的道德底线,当年大军兵败,舍身忘死相护沦为囚虏的君主,已足可证明他的为人正直、品行无私。
诸如为富贵卖良心,诬人乱伦灭门焚尸这种丧心病狂的勾当,袁彬可能会去干么?否则当初在瓦剌就不可能死保落难的朱祁镇了:那时谁会觉得这人还能回国复位?
因此,对复辟后的天顺皇帝而言,从前相依为命的生死之交,已经远不如喜宁、逯杲、门达这等毫无下限的小人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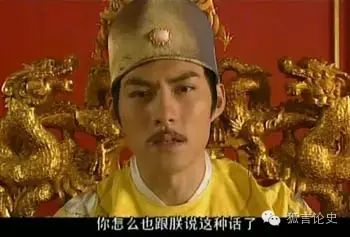
本来袁彬这样就挂个名养老,让门达们去当鹰犬也好。可几年以后,门达偏偏容不下袁彬了。朱祁镇必须二选一,是要保这个得力鹰犬还是要从前的恩人,所以就和几年前的弋阳王一案一样,他再次为了保爪牙,选择了牺牲天良。
所以,哪怕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着铁证如山众目睽睽,朱祁镇也一定要颠倒黑白,一定要甘犯众怒,一定要草菅人命,只为保住他的鹰犬们。
是以当袁彬一旦被门达嫉恨,便也只得被严刑拷打,然后仅留下一条命被赶走,以免后世讥评天子过于凉薄了。
这就是朱祁镇,最终就是这般回报这世上最忠心他的人,这般回报这世上最无私地帮助他和保护他的人。
所以从古到今,颇有些竭力洗白朱祁镇其实“是好人”的论者,努力将瓦剌这段岁月时,他和袁彬这段境遇渲染得如何有情有义,如何君臣情深;偏偏对两人故事最后的结局,要么一笔带过,要么一字不提,甚至有将朱祁镇特意嘱咐“饶袁彬一命”,也当做他顾念旧情的佐证。
哪怕三观和智商稍稍正常的人,也会觉得这是比“朱祁镇交待儿子明宪宗替于谦平反”,更可笑的笑话。朱祁镇这样的人渣,只怕连做人的基本良知都不具备,肯定不是好皇帝,居然却是“好人”?呵呵。
袁彬到了南京,闲住无事,开始回忆和整理当年和朱祁镇的点滴,将他们在瓦剌时的经历写成《北征事迹》,是后世研究这段重要历史的第一手史料。行文字里行间,并没有丝毫的怨愤,反而带着怜悯和温情。或许也只有沉浸于这种回忆中,他才能真切感觉到瓦剌时那个寒夜中搂着自己哭泣颤抖的那个少年人,并不是高举皇座九重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子。
直到朱祁镇死后,明宪宗朱见深即位。门达失去靠山,被众臣群起弹劾,被罢职流放,而袁彬得以平反昭雪,官复原职,重新掌管锦衣卫。袁彬还是一如既往地厚道与仁恕,特意去给门达送行,对这位差点致自己于死地的老同事,赠送大笔程仪。之前的锦衣卫缇帅,大都弄权索贿,声名狼藉,天下苦之。而在整个朱见深在位的二十三年里,袁彬治下的锦衣卫却异常安静,尽忠职守,大有长者之风。
【未几,英宗升遐。言者劾达罪,举埙事为证。达谪死南丹 ,彬复旧职,代达总卫事。】
年届九旬高龄的袁彬去世时,已经是朱祁镇的孙子在位时了。这时德高望重的他,是大明的光禄大夫、上柱国、左军都督,其母邹氏、其妻王氏都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两个儿子被特许世袭锦衣卫都指挥佥事。除了没有被封爵,前半生碌碌无为的小人物,一番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终究也算是位极武臣,寿终正寝。
而另一个小人物杨埙,也在袁彬冤案平反的当年被释放,成为天下知名、士人尊敬的义士。
朝廷想破格授予他官职,表彰他的义行,让他摆脱底层民众的境地,却竟然被他拒绝了,视官职名利如粪土,宁可以自己的漆工手艺糊口。
他的父亲曾遣人去日本习得该国的泥金画漆法,而天资敏悟的杨埙则潜心对其加以改进,创制了五色金钿并施法,所做漆器之物色,让倭人也自叹不及,被当时称赞为“其艺绝出古今”。
遂有士人特别为他撰写传记,称颂他「于袁彬无恩,于门达无隙,又非御史言官职责所在,却能以公论所激,挺身以突虎口,仗义维护国家栋梁、指斥权奸」,也因此得以流芳青史,传于后世。在大明王朝官方史书《明实录》的《英宗实录》一卷,记下了“义士杨埙”这个名字。
男儿汉大丈夫行事坦荡,对得起自己良心,对得起祖宗家国,则奸佞或负你,君王或负你,苍天大地不会负你,斑斑青史不会负你。因此,这终究是个好人终有好报的幸福故事。
【天顺间,锦衣卫指挥门达怙宠骄横,凡忤之者,辄嗾觇卒潜致其罪,逮捕拷掠,使无诘证,莫可反异。由是权倾一时,言者结舌。 其同僚袁彬质直不屈,乃附以重情,拷掠成狱。内外咸冤之,莫或敢发也。
京城有杨埙者,戍伍之余夫也。素不识彬,为之上疏,遂击登闻鼓以进,仍送卫狱。
达因是欲尽去异己者,乃缓埙死,使诬少保吏部尚书华盖大学士李贤指使。埙佯诺之。达遂以闻会三法司,鞫于午门前,埙乃直述,所言皆由己出,于贤无预。达计不行,而彬犹降黜,居第尽毁。
未几,英宗升遐。言者劾达罪,举埙事为证。达谪死南丹 ,彬复旧职,代达总卫事。成化初,修《英宗实录》,称“义士杨埙”云。
埙字景和,其先某处人。父为漆工。宣德间,尝遣人至倭国传泥金画漆之法以归,埙遂习之,而自出己见,以五色金钿并施,不止如旧法纯用金也,故物色各称,天真烂然,倭人见之,亦齚指称叹,以为不可及。盖其天资敏悟,于书法诗格不甚习,而往往造妙,故其艺亦绝出古今也。既不避权奸,为此义举,人亦莫敢以一艺目之。有欲授之以官者,不就,遂隐于艺以自高。
华亭张弼论曰:义者,无所为而为,合天下之公论者是也。使虽公论,行之以私,则其中已不义矣。若埙者,于彬无恩,于达无隙,又非言官,以图塞责也。特以公论所激,挺身以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于行义何如哉!】——明·张弼《义士杨景和埙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