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犀利视角——陈丹青的全新艺术观》全文共列28条“陈丹青语录”,简洁、有力,充满“常识”性与箴言意味,为了与编者的表达方式相协调,本人不对其整体进行论说式的批评,而是以同样感性但略带分析的方式逐条评说或提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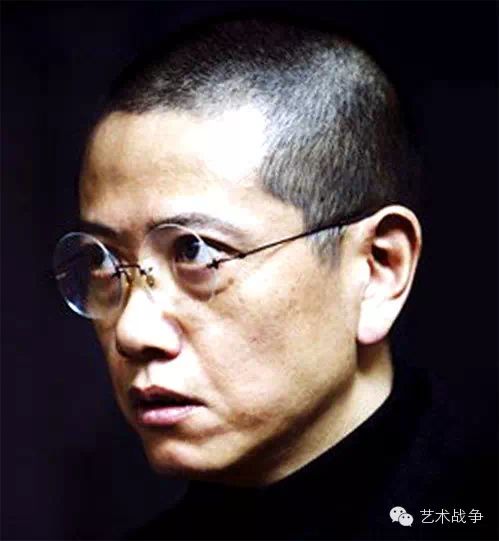
[按]今天在微信上看到很多艺术家在转一个题为“犀利视角——陈丹青的全新艺术观”的链接,上网查了一下,看到有包括**在内的多家艺术网站转载,来源均标“美术网”。对于陈丹青,本人一向敬而远之。原因是,多年来常在街头巷尾零星听过别人转述他的一些宏论,窃以为其中除了自相矛盾就是一些永远正确的废话。自觉才疏学浅,始终不敢妄加评论,今日读了《犀利视角——陈丹青的全新艺术观》,实在忍无可忍,故在此提出异议,还请大家批评指正。鉴于本人对陈丹青其人知之甚少,又疑虑网络传言的可靠性,为免去考据的麻烦,下面仅就《犀利视角——陈丹青的全新艺术观》(原文可由百度检索标题后查看)的文本本身提出质疑,与文外的陈丹青本人无关(有提到该姓名时只为修辞趣味,用时均加引号以排除人身针对)。《犀利视角——陈丹青的全新艺术观》全文共列28条“陈丹青语录”,简洁、有力,充满“常识”性与箴言意味,为了与编者的表达方式相协调,本人不对其整体进行论说式的批评,而是以同样感性但略带分析的方式逐条评说或提问。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一条]真的美术史是什么,是一声不响的大规模淘汰。
[宣宏宇的读后感]因缺上下文,不确定它在表达什么。烦劳了解其语境的朋友解读。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二条]文凭是为了混饭,跟艺术没什么关系。单位用人要文凭,因为单位的第一要义是平庸。文凭是平庸的保证,他们决不会要凡•高。
[宣宏宇的读后感]说“文凭是为了混饭,跟艺术没什么关系”大概可以有两个意思:其一,不应该设置艺术学校(学院),或者说不平庸的艺术家不应该进科班;其二,可以有艺术学校(学院),但没有必要发文凭,这当然也就意味着用人单位不需要考量文凭,甚至全社会都应该取消任何资格认证的制度。且不说以上设想是否合理,结合最后一句“文凭是平庸的保证,他们决不会要凡•高”,我想问:“为何凡•高需要文凭?或者,为像何凡•高这样的天才需要某种平庸的认证?”凡•高被其同时代的社会拒绝是事实,凡•高终究没有因为这种拒绝而被历史淹没也是事实,这些事实说明真正的天才不会因为平庸的要求而埋没,那么“陈丹青”你焦虑些什么哩?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三条]世界上的重要艺术家都不是研究生学历,也不是本科、美院附中,有的连高中都没上。梵•高就是个病人,毕加索也没有大学文凭。当今中国,需要文凭,为了就业,得到社会的认可,你就得拿个文凭。
[宣宏宇的读后感]此条大意同上条,但却更明目张胆地偷换了概念:前两句在谈特例(梵•高和毕加索),最后一句却在说大多数人(以混工作为目的的艺术生)。联系前后,其整体上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如果中国取消学历(文凭)制度,那么就会到处都是梵•高或毕加索;或者,中国学艺术的人都拒绝去上学才有可能像梵•高或毕加索那样成为大艺术家。那么,我想问的是:“为何西方各国不取消艺术院校?为何中国每年那么多落榜的艺术考生没有成群结队地成长为梵•高或毕加索?”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四条]你一要肯定自己的感受,感受是很可贵的东西。画出动人的画,凭的是感受,而不是技巧。我画的那个朝圣的小姑娘,那么苦、那么好看,但她自己却不知道——艺术就是这样,凭这一点点就打动人了。
[宣宏宇的读后感]我想请问:“什么叫‘自己的感受’?你‘陈丹青’的感受是怎么积累出来的?你要是连个形都画不准,你去试试怎么表现‘那个朝圣的小姑娘,那么苦、那么好看’!自己练过多少不说,却在对后来者大谈什么‘画出动人的画,凭的是感受,而不是技巧’,居心何在?”没有技巧哪来的感受?如果可以没有技巧就可以有感受,那你“陈丹青”就更是在说废话,那样的感受谁没有?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五条]偏爱、未知、骚动、半自觉、半生不熟,恐怕是绘画被带向突破的最佳状态。
[宣宏宇的读后感]又是一句永远正确的废话!但危险的是,这句话对那些尚未达到心、眼、手合一的艺术家来说,很可能成为一种不学无术的安慰剂。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六条]常识健全就是基础,素描不是基础,现在的素描教学是反常识的。什么都很重要,但你要说素描最重要,那就不对。一棵树,你能说哪根树枝,哪片树叶最重要吗?
[宣宏宇的读后感]如果,可以承认“常识”是一种为大多数所认可而非像“陈丹青”那样自诩为智者的少数人所占有的,那么,“陈丹青”你又何必焦虑不合常识的东西竟能大行其道呢?难道众人都低能就你一人“正常”?反过来看事情就很清楚了,“陈丹青”说的所谓“常识”不过是他个人的意志,而以“常识”(或常人、或大众、或人民等)的名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正是专制主义一贯的伎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创造,杰出的艺术作品往往都是反常识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反成见的,前卫艺术尤其如此。如果艺术创作要屈从于常识的话,前面说的梵•高和毕加索就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此外,说到素描,这一二十年以来,中国的美术院校早就不再是苏式教学一统天下的状态;还有,“素描最重要”一说是从哪里来的?个人认为之所以要在绘画入门时临摹、写生(无论素描还是其他)乃是因为其时我们对绘画还一无所知,只有先通过学习前人所做,通过包括像不像在内的一系列具体目标来开始我们的绘画体验。当然,这一起步的过程确实被很多人误解为所谓的“基础”,但却并非“陈丹青”所理解的那样,至少现在已经大不同了。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七条]我没有素描基础,不是照样画创作?中国传统绘画从来就不画素描,难道就是没基础了?想当年,我们一起画画的同学中,那些把大卫石膏像画得好得无与伦比的人,现在不知道哪里去了。
[宣宏宇的读后感]看到这一条,我有点不确定“陈丹青”究竟是在有意偷换概念,还是根本就缺乏起码的思维能力。“没有素描基础”和“没有受过某种特定的素描训练”完全是两回事。如前所述,素描(“陈丹青”所指其实是某种特定的“素描”方式)不一定要被视为一种基础,但这并不排除它可能成为某些画家的技法的一方面的基础,以“陈丹青”自己的作品来说,显然是具备这种“素描基础”的。作为艺术家,他如果因为厌倦了这种“基础”给他带来的束缚,那么他自己在创作中去努力破坏、消解,进而找到一种更自由的方式,那是无可厚非的,甚至那就是创造之所在(“陈丹青”前面所举的梵•高和毕加索以及其他很多杰出的艺术家正是这样做的,并且是终身这样的做的)。然而,要在其他并没有面临同样问题的艺术家面前,尤其是在许多年轻艺术家面前,把自己已经经历过的磨练隐藏起来去宣扬为所欲为,那就无异于在表演那个流传已久的笑话:“你看!我吃第七碗饭就很饱了,你不要再很麻烦地去吃那前六碗,直接吃第七碗就好了!”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八条]艺术家是天生的,学者也天生。“天生”的意思,不是指所谓“天才”,而是指他实在非要做这件事情,什么也拦他不住,于是一路做下来,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宣宏宇的读后感]又一句永远正确的废话,无懈可击却什么也没说。“非要做这件事情,什么也拦他不住”只是一个念头,一个愿望,一种冲动,关键的问题在于怎么做?对于每个做艺术的人来说,都有着成为大艺术家,或者说是为世人认可的梦想(梵•高亦是怀揣着这样的梦想死去的),但要做到这一点恰恰需要一点点去完善自己手上的活,而不是凭着所谓的“自己的感受”就可以“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陈丹青”在这里不谈如何达到目标,只喊“人定胜天”的口号,究竟是在解惑还是在催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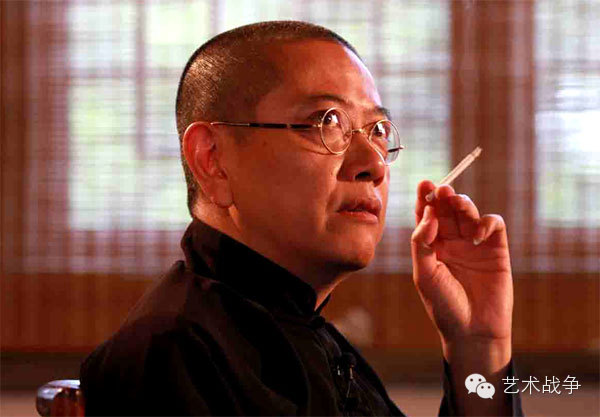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九条]中国连真正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的“公共知识分子”?进入公共事务时,偶尔有像我这样的傻子出来说几句真话大家就很愿意听,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
[宣宏宇的读后感]说话让大家很愿意听的人很多,凭什么就你“陈丹青”说是才是“真话”?还一正正经地谈“知识分子”?我看你“陈丹青”根本就一神棍!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十条]我从来没有传回任何关于成功的消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出国本身就是一种失败。
[宣宏宇的读后感]说起“中国人”的话题,我想起前段时间也是在微信上看到有人发的一个关于“陈丹青”言论的链接,内容大概是“陈丹青”捶胸顿足地唾骂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怎么能画了那么多年的油画,身为一名中国人不画国画而画其他简直就是不肖子孙云云。对此,我愕然!难道因为汽车、电脑、电话都是外国人发明的,中国人就不能用?那么还有多少东西是我们中国人不可以用的呢?难道这个到国外镀了一圈洋金边的“陈丹青”非要看到中国保持着刀耕火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才安心?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十一条]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然,那三分之一就是指活在神州大地上的中国人。我实在不忍享受“水浅”而“火不热”的生活,遂毅然出国,“受苦”去了——真不好意思,今年年初,我又回来了。我一回来,还在美国的不少中国同行就忧心忡忡诚心诚意追问我:适应么?习惯么?后悔么?那意思,就是怕我回来又“受苦”。
[宣宏宇的读后感]虽缺上下文,但可以看出这条讲的大概和上一条是一个话题,主要意图还是在表白自己是一个多么热爱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但表白是很廉价的,任何人都可以无条件地表白。对于那些言行不一的人,早有古话说过:“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因此,不必在此浪费时间,还是看下一条吧!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十二条]中国人大抵是惯于取巧而敷衍的,我自己也是如此。而我所见美国艺术家,一个个憨不可及,做事情极度投入、认真、死心眼儿、有韧性,即所谓持之以恒,精益求精是也。同人家比,中国人的大病、通病,是做事不踏实,做人不老实,要说踏实老实的憨人,中国不是没有,只是少,例外,吃亏,混不开。
[宣宏宇的读后感]关于这个话题,一直都有争吵,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大抵都是这样一个模式:一方摆事实,做分析,说明外国多好中国多差;另一方则主要进行道德谴责,骂对方“崇洋媚外”、“数典忘祖”之类,当然也有以事实为例证明中国亦有外国不可替代之美好等等。当然,无论哪一方,争到最后大多都会回到一个折衷点上来承认各有利弊,否则就要打起来了。在我看来,“中国人”、“外国人”之类的比较方式不但说明不了问题,而且还在助长一种忽略个体的概念化思维,进而滋生集权意识。“陈丹青”更圆滑的是,非常聪明地在说完外国多好中国多差之后,再加上一句“中国不是没有,只是少,例外”(虽然之前已不惜用“取巧而敷衍”把自己套在其中,但说到所谓的“少,例外”时还是在标榜自己吧?所谓金蝉脱壳说的就是这个吧!)以留余地。但更聪明的还在后头,看下一条。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十三条]放松政治钳制、美学观略略放宽、创作格局稍许多元,是做文化起码的前提。八十年代用过一个词,叫做“松绑”——不少语言真形象,一不留神,实情给说出来。
[宣宏宇的读后感]一个浅显的生存原则是:莫与众人为敌。你大放厥词,得罪了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人家把你抓起来,把你处决了,那后世你也许会成为烈士,流芳千古,虽死犹生;另一种情况下,你同样是大放厥词,但得罪的是众人(无论你的动机如何),大家不用动手,光用唾沫就把你淹死了,结果你除了小命玩完,还将成为千古罪人,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陈丹青”不仅深知这一点,而且很懂得如何趋利避害。于是,对“中国人”的批评转换成了对政治的批评,把责任推到少数人身上,十分安全。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十四条]您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很满意吗?您对野蛮拆迁很满意吗?您对目前的医疗系统很满意吗?假如您诚实地告诉我:是的,很满意!很开心!我立即向你低头认罪:我错了,我改,我脑子进水了,我对不起人民,我要重新做人,封我的嘴,然后向你们好好学习——这样行吧?
[宣宏宇的读后感]这一条里所举的“中国的大学教育”、“ 野蛮拆迁”,不都是全国人民每天在网上热议的话题么?我无法想像“陈丹青”如何竟可以用“低头认罪”之类的革命词汇,来将自己的人云亦云渲染成一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英勇壮举!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十五条]我真正的身份就是知青,我真正的文化程度就是高小毕业,中学都没上过。
[宣宏宇的读后感] “陈丹青”的意思是让我们再次取消大学,停止中学,让青少年们继续去“广阔天地炼红心”?如果不是,那究竟想要说什么呢?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十六条]受过小学教育而能做成一些事情的人,太多了;受了大学教育而一事无成的人,也太多了。“学历”与“成就”应是正比,不是这样的。
[宣宏宇的读后感]后面一句完全无错,因为它既无法被证实,亦无法被证伪。将其还原为一个逻辑陈述大致相当于这句话:“天下的乌鸦不一定是黑的。”所以后一句可以当作废话,前边一句却值得稍加思索。什么叫“太多”?什么叫“做成事”?在什么情况下“做成事”?做成了些什么事?如果这两个“太多”都是合理的话,你“陈丹青”还批“中国人”,还批“政治”,还列举社会问题做什么?这两个“太多”基本上呈现了“学历”与“成就”之间是一个反比,但“陈丹青”为何要说“应是正比,不是这样的”?老江湖啊!佩服!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十七条]真率是很高的要求。真率也是品德。
[宣宏宇的读后感]神秘主义——神棍的杀手锏! “真率”是什么?什么是“真率”?谁会认为自己不“真率”呢?你会么?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十八条]“丹青:你怎么也叫陈丹青?”接着签了我的名。但随即我就后悔了:凭什么人家不能也叫“陈丹青”?我该这样写:“丹青:我也名叫陈丹青。”
[宣宏宇的读后感]又一次让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丹青”:你干吗不去演琼瑶剧呢?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十九条]无论绘画还是写作,我尽量不说假话。我这个人口无遮拦,不知道哪天又会说什么。
[宣宏宇的读后感]我想,没有任何一个绘画或写作的人会宣称自己的工作是在说假话。另外,话真不真和话对不对是两回事,在我看来,后面一个问题才更重要。并且,话真不真在大多数时候是无法讨论的,而话对不对则是可以争辩的。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二十条]“科以人传科尤重,人以科传人可知。”解释起来,好比你是钱学森,又是博士,这博士学位因为你就分量很重;可要是你没啥名堂,却拿个博士学位混一辈子,你这家伙是个什么料,可想而知——我向来讨厌名校学生自视高人一等的那张脸。
[宣宏宇的读后感]是的,但你“陈丹青”不能因为有拿着博士学位的混混就否认学位存在的意义,更不能因为某种“讨厌”就无视现实。本人考硕士5年才上,考博两次均败,至今无果,但自以为其间亦学习了许多东西(比如说由于考硕4次英语不过,导致我反复学英语,以至于英语越来越好,可以直接阅读许多尚未被译介的东西,才不至于被你这种假洋鬼子随便就忽悠了),明白了很多事情。如果你要斥责我在向不合理的规则臣服,很可悲,那么我的回答是,我的原则是尽可能多地检典自己,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去点滴地促进规则的完善,因为我同意波普尔(Karl Popper)的渐进社会工程论,而无法苟同于“陈丹青”式的革命情结。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二十一条]我为什么喜欢鲁迅?他骂人、斗争,不买账,一辈子叫板,但是孝顺、善良、心软。西方一些知识分子、艺术家也是,很惊世骇俗,但私下很纯朴、真实。中国这样的人不多,要么惊世骇俗,人不可爱;要么人可爱,却没有骨头、锋芒。
[宣宏宇的读后感]“中国这样的人”又“不多”了!我们都没骨头,没锋芒,不可爱,就你“陈丹青”既“惊世骇俗”又“可爱”(叫你“万人迷”满足不?),但请你不要把自己和鲁迅相提并论好吧?不要跟我辩解说什么你没有把自己和鲁迅相提并论,你只不过说了你喜欢鲁迅而已,试想,如果你没把自己想像成和鲁迅一样的人而是把自己看作阿Q,你对鲁迅还喜欢得起来么?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二十二条] “好”必须牺牲很多东西,如果反抗,就得把“好”作为代价。中国人的人格不丰富,太单面。
[宣宏宇的读后感]不知所云。有劳了解上下文的朋友解读。不过后边一句好幽默,“人格不丰富”?中国人要都像你“陈丹青”似的双重人格、多重人格、人格分裂才好么?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二十三条]我不知道自己懂不懂矿工或农民,但我一定弄不懂当官的、谈生意的、玩儿金融的,还有毫无表情的科学家,不,一点都不懂——这就是我和现实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难以和现实理顺关系,而且不想理顺。
[宣宏宇的读后感]科学家都毫无表情?不知大家以为然否?“陈丹青”你说你“弄不懂”“谈生意的”,我想问你你的画卖过没?你的现实不用理,已经很顺了,至少比你“不知道自己懂不懂”的那些“矿工或农民”要顺得多,如果连这点你都不敢承认,那我只能是无语了。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二十四条]将当今教育体制种种表面文章与严格措施删繁就简,不过四句话:将小孩当大人管,将大人当小孩管;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宣宏宇的读后感]我也想不明白,怎么全中国那么十几亿人就不理解“陈丹青”你那么简单明了的办法并照着去做呢?非要执迷不悟地在复杂的生活和工作中“受苦”?要是让“陈丹青”当皇帝该多好!一声吆喝,人类千百年来的理想社会就实现了!多省事!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二十五条]我一点不关心中国学生的英语如何。我看见大家的中文一塌糊涂。我们千千万万的“好萝卜”如今是英语也不好,中文也不好。
[宣宏宇的读后感] “丹青”:刚才已经和你说过一次我考学和学英语的经历,现在你又提起英语,我就学着你的样再显摆显摆吧!听说高考要取消英语考试了,我好高兴,因为我的英语现在越来越好了,以后能像我英语那么好的人也会越来越少,我可以越来越像你一样有优越感了!说到中文嘛,二十年前还经常能看到的那些扫盲标语怎么现在不见了?如果你愣要对中国这些年来的进步视而不见(或者说就是看不惯),非要说“中国学生”的中文“如今”不好(即没有过去好),那我也只能表示无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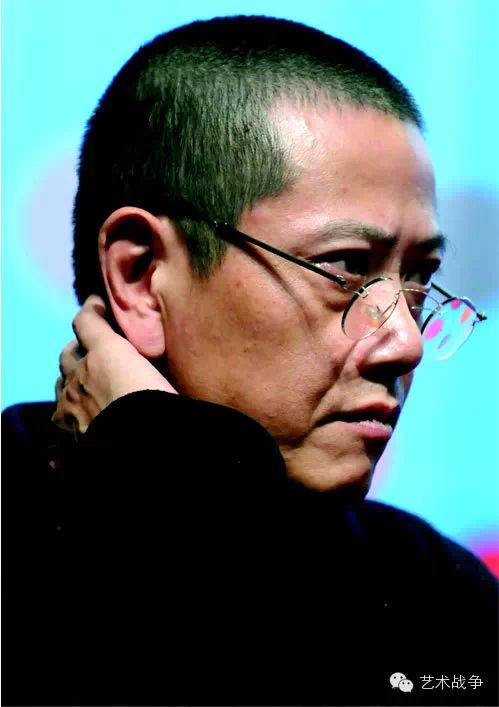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二十六条]真正有效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我根本就怀疑“培养”这句话。凡•高谁培养他?齐白石谁培养他?
[宣宏宇的读后感]如果“陈丹青”你说的“自我教育”就是今天学校里正在提倡但还没有做到的“自主学习”,那么你又废话了,这个道理其实没人不懂,但问题是能在大多的程度上做到?如何去做到?你要不是觉得我们都需要被你培养,你又何必成天到处高谈阔论?如果你说的“自我教育”其实就是自我催眠的话,我想凡•高应该是从来没有干过这个事的。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二十七条]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双方”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不求定论,有如禅家的公案,修行的细节。
[宣宏宇的读后感] “陈丹青”你能不能不要再这样赤裸裸地标榜自己,这种话你叫学生来说也比你自己在这里说要让我们的感官更容易接受一点!你上边说的这些,哪本教育学的教科书里没有?就你做了,别人都没做?就你做的好,别人做的都不好?
[“陈丹青”的犀利视角第二十八条]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徐悲鸿任北平艺专校长。搁现在,第一条入党,第二条凑够行政级别,然后呢,领导看顺眼了或把领导捋顺了。于是一层层报批、讨论、谈话、任命,转成副部级、部级之类……这样的“入世”,有利益、没担当。今日大大小小教育官员除了一层层向上负责,对青年、对学问、对教育、对社会,谁有大担当?
[宣宏宇的读后感]又拿民国来说事了(很时尚)!我最近看了一部叫《神秘博士》的电视连续剧,里边的那个DOCTOR有个叫Tardis的东西,建议“陈丹青”你没忙着说话的时候去想办法弄一个来,带着我们穿越到一百年前去扭转乾坤好么?如果不行的话我想问你,在现行体制无法进行立竿见影的改变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都不要做任何事了呢?或者,“陈丹青”你来发动一场革命?
终于说完了!好累!这让我想起了索伦森(Roy Sorensen)的那个倒背圆周率的老头,还好编辑没有列出280条或者2800条,不然我的人生也要被耗尽了。如[按]中所说,以上所有感想不针对《犀利视角——陈丹青的全新艺术观》所指的那个具体的叫“陈丹青”的人,之所以在这里再次强调这一点,不仅是为了避免被误解为人身攻击,而且还为了明确说话意图。按照论辩在基本要求,如果要对陈丹青其人的观点进行整体评说,那必须建立在对其著述及相关信息的调查研究之上,虽然这会比较花精力,但也不是说不能做,只不过我想说的重点不在于此,所以我不去考证,甚至将《犀利视角——陈丹青的全新艺术观》的真实性责任保留在编辑那里。我关注的是该文本身的传播结果及其反映出来的问题。
作为一个传播现象,陈丹青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惊世骇俗”的效果。记得好几年前陈丹青到云南艺术学院讲演,报告厅被挤得水泄不通,厅外十几米开外也是人山人海,当时我还以为是来了韩国的歌星。当然,就像在我在第二十五的感想中说应该看到进步那样,在大多学术讲座需要强迫学生听讲的情形下,能够将学术活动(不论其内容)做到这样的效果自有其积极的价值,但很大的问题是,当某个人被奉为偶像,尤其是这个人还很享受这种感觉的时候(具体表现就是变本加厉的去重复,去强化那些便于讨好的说法),事情就会走向反面。《犀利视角——陈丹青的全新艺术观》就是这种明星效应的表现之一。
如前所述,我不清楚这28条“犀利视角”究竟是摘录于陈丹青的长文还是记录的他的只言片语,但无论如何,面对这样一种缺失了上下文语境的断章取义,最糟糕的还不是我们是否会误解了陈丹青其人及其本意,而是读者很容易把这些表述奉为信条,其结果就是强调权威、迷失个体,完全不会出现 “犀利视角”里宣称的那种情形:“……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双方”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不求定论,有如禅家的公案,修行的细节。”拟定这样的教条是否符合陈丹青其人的本意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此类《葵花宝典》式的至理名言的层出不穷,反映出我们崇尚领袖和英雄,推卸个体责任的思维惰性。另一方面,从内容上讲,“陈丹青”的所谓反教条,反体制,倡导精神自由和艺术感觉的鼓吹,实际上支持了一种不学无术的态度,而这正契合了思维惰性的需求,这也正是它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回到艺术问题,我还是认为艺术是做出来的,不是设想出来的,更不是鼓吹出来的。前几天在微信上看到一个关于宫崎峻“拒绝技术”的链接,有感而发(仅因标题有感,内容我没看)写了一句话:他本身就是一种技术,此技术拒绝彼技术而已。艺术的思想是做出来的,当艺术家全身心地沉醉于某种技术中时,艺术才飘逸而出,同时也生成了深刻的思想。大多数想法是在做的过程中形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没做的人会没想法的原因。钻研不了艺术的人张口闭口都是谈思想谈观念谈情感表现,最后再上升到神秘主义的高度。这些东西任何人都能张口就来,很廉价。其实,“艺术是做出来的”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未必很多人不懂,只不过练成一种技术(就绘画而言,写实在今天只是众多技术中的一种,并且它本身亦有许多不同的策重)的过程总是痛苦的,尤其是在形成自己的技术(或曰风格)之后仍要不断克服则是终身的痛苦,而大师们恰恰就是能够在这些为常人视作痛苦的过程中感受快乐的人。要是已经做到一定程度的人对着后生晚辈只谈思想谈观念谈情感表现,甚至对基本的训练大加贬斥,那他若不是不负责任的话,就只能说是愚蠢了!
更进一步,在单纯的创造过程中只有技术没有艺术,艺术是欣赏过程的产物。然而,对人的实践来说并不存在单纯的创造过程,因为任何艺术家总是会在其创造生涯,甚至在最微妙的一个环节中(或其前后)不断地反观自己的作品与行为(即欣赏活动),因而实际的创造过程总是“单纯创造”与欣赏交替前行的。尽管这样似乎会因为颇带量子化视角的假定而显得有点造作,但这稍嫌别扭的视角却有助于让我们去区分艺术家的两种工作状态:其一是在某段时间内忘乎所以地下意识工作,然后在另一段时间里停下来观看,思考或干点其他什么事,这种方式即所谓“交替”;其二是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保持意识的强力控制,这按通常的观点可以说成是“思想-技术-艺术”三位一体的完美统一,但在我看来这种方式是毫无创造性的,甚至于是很难在实际中做到的。那么问题又回到了“交替”上。我以为,有效的创造过程一定是“单纯创造”状态大于欣赏状态的。如果一位艺术家过多地从工作中抽身出来评判其成果,那么一定会破坏其创作的感觉经验,尤其是破坏这种经验的连续性,即破坏其技术生长的生命线。于是,当艺术家越努力地向其作品中倾注所谓的艺术时,这些作品便离艺术越远。因为他所认为的个体思想、观念及情感都不过是来自历史、当下潮流及自身积习的抽象概念(而不是“陈丹青”想像的那种具有真如历史性的“天生”),而“技术”恰是艺术家赖以艺服概念化的唯一途径,在下意识地沉醉于技术过程中,概念化的传统重新鲜活起来,当下潮统成为一个参考系而非指南,个体的积习也变得可以争辨。以上这些其实早就为Jackson Pollock的“无意识”绘画强烈地提示过,也是解构理论的值价所在。
所以,从事艺术一定是一个从引入外来约束到设置自我约束并不断克服这些约束的过程,绝不是“陈丹青”所说的那种放任自流。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仅仅在“陈丹青”身上存在,甚至“陈丹青”根本就是我们思维惰性的一个产物,他的逻辑漏洞就是我们规避追问所留下的空白,他的自我膨胀就是我们掩饰不自信的表现,他乐此不彼地扮演英雄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崇尚权威的导演……
仅就艺术而言,我不会像“陈丹青”那样去焦虑一个天才是否会被“万恶”的教育制度或者其他什么不合理的现实埋没掉,因为天才之所以为天才就在于通过克服种种“不应该”才成就自己的。然而,对于那种普遍蔓延于各种社会问题之中的惰性意识,我则不那么乐观,但我亦不会像“陈丹青”那样自命为先知,试图去以上帝的角度拯救大众,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原则还是之前感想里写过的那句话:尽可能地多检典自己,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去点滴地促进规则的完善。
作者:宣宏宇
原题:《读“陈丹青”的“艺术观”有感》
------------------------
((“艺术收藏区域群”(微信号:99938888),现有几十个城市的艺术收藏区域群。))

(((B2B模式艺术电商,连接10万艺术品经营商,连接几十万艺术收藏家,连接10万艺术家。
“ART MALL 艺博会”(微信号:303000333)
连接几十万艺术收藏家,ART MALL“艺术大卖场”规划覆盖几十个城市,每个城市几万平方,画廊、艺术商店、文创
商店
、艺术家具、艺术拍卖公司等免租金入驻
。
“
ART MALL 艺术产业论坛
”(微信号:99909099)
连接10万艺术品经营商
,常设艺术产业创投论坛。
为古玩城、艺术区、文创园区提供招商服务,为空置的厂房、商业地产、别墅区提供文创转型招商服务。
“B2B线上服务”(微信号:330300001)为艺术展览、艺术拍卖、艺博会、文创活动提供线上推广服务。
“B2B小型会展”(微信号:330300007)为艺术品、文创行业提供小型会展招商、场地、推广等综合服务。
“B2B书画换工作室”(微信号:1015222225)艺术家用书画作品来置换艺术区工作室的使用权。
“B2B艺术银行”(微信号:1013777773)为国企、集团公司、上市公司、连锁酒店、会所、茶馆等提供批量艺术品租赁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