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圣容教授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Eugene Higgins数学讲座教授、台湾清华大学荣誉讲座教授,曾获选美国杰出女数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2年,作为数理组唯一一位女性候选人,在外界一片看好她当选的呼声中,张教授顺利当选第29届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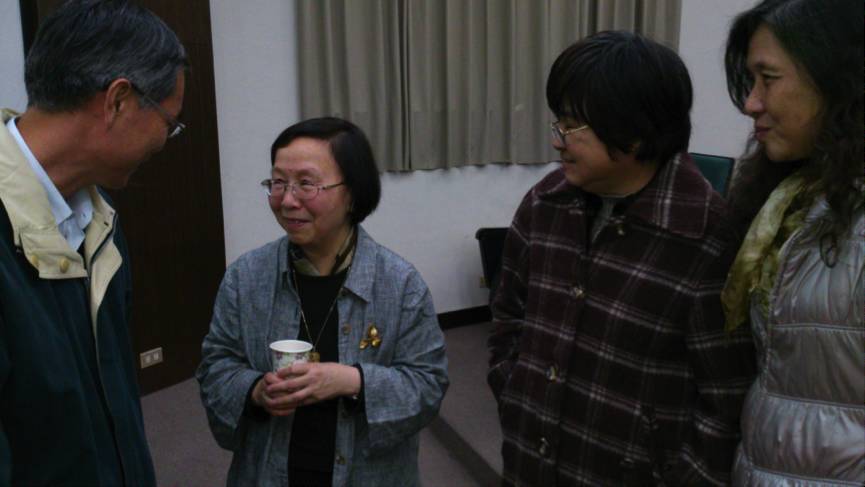
张圣容在淡江大学演讲后与学者相谈甚欢,其中包括本文作者胡守仁教授(右二)。
受访人:张圣容教授(以下简称张),普林斯顿大学Eugene Higgins数学讲座教授、台湾清华大学荣誉讲座教授。
访问人:胡守仁教授(以下简称胡),台湾淡江大学数学系教授。
胡:先谈一谈你的求学过程。
张:我在台湾长大,小学在台南,五、六年级搬到台北,随后进入北二女(现在的中山女高),然后保送进入台大数学系,1970年毕业后赴加州伯克利攻读博士学位,1974年取得博士学位。
胡:为什么会选择研读数学?
张:我们那一届很多人都是第一志愿进入台大数学系。你觉得你的因素是什么。
胡:那时候觉得自己数学比较好一点。
张:就我个人而言,大概有有双重因素,一方面是在中学时觉得数学比较容易,也学得比较好,另外一方面也是实际现实的考虑,生活现实的考虑。其实那时候我对中文,特别是中国文学也很有兴趣。可是在理科和文科之间,觉得念理科将来找工作比较容易。那时候理科的人才比较少,我们所知道的文科出路也不多,总觉得理科的天地比较宽,工作机会比较多,比较容易自立,这是一方面的考虑。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激励,我后来才觉得,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杨振宁在清华大学成立几周年的一个演讲中说,如果他是年轻人,就会选读数学。他说数学呈放射性发展,很有前途。我想这也是影响的一个原因。我觉得你和我都算是运气好的,高中时对数学知道的不多,进到数学系后觉得还喜欢。也有人进到以后不喜欢呢。
胡:你在做研究生以后怎样选择你的领域,开展你的研究工作呢?
张:实际上在台湾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将来是念分析或几何的。我觉得读数学基本上有两型,一个是比较代数化,比较抽象思考,还有一个比较分析型的,比较几何,比较是看图的。我很早就知道我代数不行,不是那一路的。要嘛要念分析,要嘛念几何。所以到了伯克利,起先跟的一个老师是比较偏几何的,可是他做的偏向拓朴,是和上同调(cohomology)相关的东西,过了一下,我觉得我没有太多感觉,才换成分析。所以经过了一阵子的摸索。不过那时候在伯克利,不需要马上选老师,第二年再选都可以,我就选了Sarason做指导教授,念古典分析。
胡:所以你一开始做的分析是古典的。
张:对,是单复变分析(one complex variable)。我常跟人家讲笑话,美国有一个大学炸弹客(Unabomber),他是数学家,曾在伯克利当过讲师。我常说我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懂他的数学的人。我们做的是“单位圆上的有界解析函数”(bounded analytic function on unit disk),这个大学炸弹客之所以在伯克利当讲师,是因为他是我老师的博士后研究员。我跟他是同一师脉的。
胡:但你现在做的东西跟以前做的似乎有相当大的差异。
张:其实也就是分析,我念的是单复变古典分析理论。可是我在毕业的时候,1973~1974年时,分析方面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费夫曼(Charles Fefferman)和斯坦因(Elias Stein)的古典实分析研究进展。而我念的复变数中有一个很有名的问题——日蚀问题(Corona Problem),是分析大师卡尔松(Lennart Carleson)用很复杂的复变分析方法做的。费夫曼、斯坦因的工作,有一部分受到卡尔松工作的启发,但他们的方法可以简化日蚀问题的某些步骤。我那时候就体会到实变的工具更具弹性。复变很严谨,可是比较古老,题目都做到底了。而实变是活的,所以我在毕业时就知道我要往实变的方向走。毕业以后我就逐渐由复变转向实变,做古典调和理论的问题。再过了四、五年,建平(作者注:杨建平教授是张圣容教授的先生)问我一些题目,是比较几何的问题,但最后归结到分析。所以我逐渐开始去了解他的题目,我们之间就有了一些讨论。我们虽然做研究生时就认识了,但正式讨论数学,差不多是毕业十年之后开始。
胡:所以你们之前并没有数学上的合作。
张:他有时候会告诉我他做了什么,我也会告诉他我在做什么,但只是听一听。真的开始合作研究差不多是1980、1981年。逐渐他告诉我他要什么,我也去了解几何的东西,我们才开始合作。
胡:所以你由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是一件相当自然的事情?
张:渐渐,渐渐转的。
胡:那所需要的工具、知识怎么补足?
张:那是慢慢的边学边用。
胡:现在很多学生常常觉得自己的工具不够,或知识不足,不能开展研究。对此你的看法如何?
张:这方面,尤其在我到了普林斯顿之后,发觉有不同的哲学。我们以前念书都说要扎实,要把工具学好,你有一个工具以后你可以做东西。到了普林斯顿以后,我发觉他们的哲学是这样的,就像读一本数学书,有时候你不一定要从第一章开始看,当然在大学时要先建立一定的基础,可是你要学一个东西,你要插入。先学深一点的东西,你要哪一章,先进去看。不懂再回头补,就是这种跳跃式的。所以像我们系里开课,很多时候都是直接开专题课程,需要的东西你再回来补。
胡:并不是说我需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
张:不是这样,不过我觉得跟人家合作很好,跟人家合作就是学的一个方法。有的时候,他的东西你不懂,你的东西他不懂,你们的题目有一个共同的方向。你想办法去学他的东西,他想办法学你的东西。是一个互相的配合。
胡:在研究的过程中会遇上高潮及低潮,你是如何面对的?
张:当然啦,大部分的时候是低潮。其实我觉得做数学研究很难,就是这个原因。实际上有突破,有发展的时候很少,大部分都在耕耘。这个当然也看人,有的人比较快,我则是比较慢,慢慢磨出来的,最后成熟。
有时候是放下,放下的题目很多,成功的题目不多。有时候是先放一下,过一阵子再回来看。有时候有合作者就不一样,你自己一个人做,容易卡住就放下了。如果有合作者,你的低潮不见得是他的低潮,彼此间有个互补,有个压力。比如说我和我年轻的学生或博士后做题目,我知道他一定得出论文,有的东西我想要放了,也还是会想办法多看看,绕一绕,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进展。即使这样,放下来的题目要比真的有进展、发表的题目多得多。
胡: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心情是如何转换,如何调适自己的心情?
张:现在的年轻人我不清楚,我们以前的教育太重视你一定要关在房里好好用功。其实你讲的所谓的调适,到山顶上散步、去听音乐会,并不表示没有在想数学。如果心里有牵挂的话,总是会在想的。散步的时候可以想,跟朋友聊天也可以想。实际上还是一种调节,有时候先放一下还是好的。不要一直钻牛角尖的想。

张圣容(感谢摄影师Mariana Cook授权)
胡:你认为做好研究,除了知识、工具以外最重要的是什么?
张:最重要的到最后是个眼局问题。一个东西你深入了解,你要看准方向以及各方面之间的关联性。选题的方向很重要,你觉得哪个题目重要,这就已经是做研究的一半了。
胡:你怎么知道哪个题目重要,或者说哪个问题可以下手?
张:这当然是很难的事,就是摸索和感觉吧。所以我说多读、多看都是有帮助的,多去听演讲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数学上我们最赏识的就是原创性,这个原创性就是一种眼光问题。一个东西你有独到的见解,或是你看出这个题目和那个题目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这种很有功力的数学家,一直在做同一个方向,把那一个方向的工具发展得越来越好。也有这样一种做法,可是数学界到最后我们更期盼一种新的眼光,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一个题目。
胡:选题的眼光和一个人全面的教育有关系?
张:一个人的眼局,还有生活方式会表现在选题方向上,如果这个人的兴趣很广,有时候他选的题目反而比较活。我看到现在国外杰出的年轻人,窜升很快的明星,到最后是一个眼局问题。数学好,做人做事很成熟,对选题目有眼光都扮演一定的角色,也就是说你这个人的格局比较高。到最后教育是一个全面的,当然数学是本,但到最后你的表现能力、应对能力、选题的方向、对人对事的态度等,都扮演着某种的角色。教育要是全面的教育才能培养一流的人才。
我有时候觉得中国或台湾培养的顶尖人才,在各个方面的表现仍不够成熟。我们的教育太狭窄。我平生很遗憾的就是物理没有学好,这是我的损失,是我教育上的大洞。我看到我们学校很多来自前苏联的数学家,他们大学的时候比较不分科,数学、物理、工程就算同一领域,所以他们的学问比较广,到最后影响到他选题的方向,他学偏微分方程(PDE),因为有物理的背景,他看的PDE就不一样。代数几何他也能有物理的概念,他比较通,把数学看成科学的一支,互用的,像我们这样则是比较单线的发展。
我所谓的选题的眼局,你的背景都算在内的,你的视野都影响你的方向。数学的教育要比较广,至少大学部要如此。你要钻研的话以后有的是机会,有很多时间来专精一个领域,大学教育还是要广。作为现代的数学家我觉得统计、几率都是必修课,和微积分一样重要。
胡:无论如何,对研究生或刚开始从事研究工作的人而言,选题其实是最困难的事。
张:刚开始总是如此,尤其是博士论文,通常都是老师点选,可是日子久了,应该要有自己的方向,自己的感觉,自己觉得什么题目重要,什么不重要。
胡:所以你认为数学还是有重要的和不重要的题目分别?
张:当然有,我是觉得有。有的比较像例行公事,有的只是整理的工作,有些是比较开创性的工作,这是有所不同的。
胡:现在来看,你觉得数学上哪一些是比较重要的题目?
张:重要不重要,我年纪也大了说不准。我的感觉是现在的数学跟以前我们在在念研究所时学的数学是不一样的,现在最主要受计算机和大型计算的影响。我们以前读书时,特征值问题(eigenvalue problem)λ1、λ2需要一个个的算,然后变分(variation)、极值问题(extremal problem),现在动不动就是渐近状态(asymptotic behavior),λk、k趋近于无限大,λk怎么样的分配。因为有了计算机的引导,进入了几率的观念。数据一大,就有分布、几率的影响。所以现在的数学,不论是分析、代数或代数几何,常常有比较大的框架,比较大的数据,需要做整体的分析。比较不局部性。
胡:那么以后的数学发展,也是像这样一个方向。
张:对,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都应该懂点几率,无论你的学科是什么。数学其实不能够区分成很多支,都是相关的。可是大数据的分析是很重要的方向,不管你用什么工具。

张圣容院士受邀到淡江大学演讲的情形
胡:想请你谈一下做为女性数学家,你有什么特别的遭遇和感觉?
张:感觉很强烈、很孤单,尤其在普林斯顿、哈佛这些常春藤联盟的学校,因为女性数学家人数实在太少,你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其实我看了很多台湾出去的女学生,或者我周遭的女学生、博士后,我觉得女性从事研究工作,到最后很多都是不能面对、处理这种孤单的感觉。做数学本来就是关起门来工作,比较孤单、寂寞,要能自己面对自己。而女性因为同行中人数很少,就变得更加孤单,跟人家交朋友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还有类似我们这种背景,出国在外的外国人,到了美国本来就还有一个文化适应的问题,朋友圈又再缩小,所以到最后我看到有些中间出问题或者半路离开的例子,都跟孤单有关,都是朋友太少。像我的情形,建平是数学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两个人可以合作,所以孤单比较少,即使这样,我还是有这种感觉,像我们系里30多位教授,大概就只有一、两位女教授。
胡:这个是因为她们做得没有这样好,还是没有这样的机会,或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张:像我们系里讲师层级的老师,20、30人中大约有4、5个女性。而且每年雇用新的讲师都会有年轻的女教授。可是到了终生长聘的层级,好像可以选的人就不多。不是说资格不够,还有一个就是家庭的因素。男教授你雇用他,传统上太太都是愿意迁就跟着先生换。譬如说,先生有机会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工作,通常太太都愿意跟随,自己或者换一份工作,或者休息一段时间,这种事常常发生。女教授就不会,如果他的先生也是专业人士,谁迁就谁?男方迁就女方是很少的,即使在美国也是这样。我们普林斯顿的校长是位女性,她在孩子3、4岁时就离婚了,两个孩子是她一手带大。女性事业的路是比较艰难的,因为各种社会的因素。我不觉得是能力和天性的问题。传统上,研究工作是男性的职业,女性开始时是极少数的,我们是新进入这个行当的,路比较艰难。
美国因为女教授很少,对于歧视的问题很敏感,其实我个人的观察,我并不觉得有歧视,数学界的人还蛮开明的,对这个问题都很敏感,所以歧视的问题在公开的状况是没有的。可是这个制度本身对女性不利,终生长聘的制度在设立时,就没有女性的参与,没有以女性的职业考虑,以前都是男性。制度在设立时就是以事业为主的考虑,男性本位。比如说终生长聘制度中,你读完博士学位,大约27、28岁,然后做博士后,再做助理教授,顺利的话,等到要升等时,已经34、5。大部分的女性到这个时候一定会考虑婚姻的问题,孩子的问题。所以长聘的制度对女性很不利,你一生的事业有三、五十年,为什么终生长聘在前6年就要决定呢?这是因为传统是这样的,可是这样的制度对女性很不公平。
胡:那你是怎样度过这个艰难的历程?
张:第一当然是建平帮忙,先生的合作。第二,相对而言我一直很幸运,博士读了四年,26岁时就拿到了,终生长聘也蛮顺利, 31、2岁就拿到长聘,我是拿到长聘之后才生小孩的。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等到拿到长聘才生小孩啊。这件事有个时间的期限,我就看到很多周遭的女性朋友到最后错过生小孩的时间。或者那时候刚好生病,或者升等没有那么顺利,等上个几年,甚至婚姻出了问题,结果就没有小孩。这个生小孩的生理期限、婚姻的问题,对女性是很大的压力。我是说这个事业的关键时刻跟你生小孩的时间基本上是冲突的,所以说这个制度对女性很不利。这是我的观察,这个观察局限在学术界,工业界的情形我不清楚。
胡:生小孩之后你还是可以做出这么好的数学,你是如何安排处理这一切的?
张:压力很大,有一段时间,我的研究还是慢了下来。还有就是我父母一直帮我忙,他们二人轮流住在我家,帮我照顾儿子到九岁,女儿差不多到六岁。所以我得到父母很大的帮助。记得我女儿出生后,我觉得好忙,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我常常忘了吃中饭,中午常常没有时间吃饭。一早就忙,工作、备课、演讲,和学生讨论等,到了下午四、五点我觉得怎么有点头昏,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吃中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有两年的时间,就是觉得日以继夜的忙,每天一回到家,马上接手照顾小孩,常觉得喘不过气来,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人生最忙的一段时间。
胡:那这样的工作是建平和你一起分担呢?还是你负担大部份的工作?
张:我相信他分担的要比其他的传统的中国男士多,绝对的。可是呢,我还是觉得我做得比他多。我不知道是传统的原因还是母性,对孩子的照顾好像一种天性,就是会花比较多的时间。不过,他也许并不这样觉得,我相信他做得已经很多了,这一方面,我十分感激。
胡:那么你们在普林斯顿收进来的女性研究生占的比例有多少?
张:很少,我们一年大约收15名博士生,给的入学许可约二、三十人,我们一般有六、七成的接受率,低的时候也有四成。一届里面12~15名学生,有两个女性就很不错了。所以她们一进来就很孤单,人数很少。
胡:那在大学本科呢?
张:也不多,我们大学本科要到大三、大四才需要选择主修,每一年大约四十个学生中,有个四、五个女孩子。
胡:比起我们在台大的时候,差不多。
张:我们那一届特别幸运。我们班上很多女生后来继续做研究工作,跟我们女生人数比较多有关。我觉得有个互相扶持的力量,而且一开始就不孤单。我作为女数学家,孤单的感觉是到国外念书后才发生的。而且我们班的女生都还蛮喜欢念数学的。到最后有个互相扶持的力量,互相砥砺的力量。到了伯克利才发现原来女孩子读数学的这么少,别人也用一种比较特别的眼光看你。
胡:那你会鼓励女孩字念数学吗?
张:我以前一直是鼓励的,现在因为我看到很多例子,我有时候觉得也不见得是最好的选择。要看人的个性,如果她喜欢念,她从中得到乐趣的话,我当然是鼓励的。可是我觉得这条路满孤单的,尤其是到国外去进修,发展事业,如果在自己的国家也许还比较不一样。美国女孩子很少念数学的念到博士,尤其在比较尖端的大学里,大多是外国女学生在念,我觉得奋斗是双重的,生活上的,还有你要进入一个都是男性的行业,很孤单的。是不是最好的选择,有时候我质疑。并不是说不适合女孩子念,而是说路途是很遥远的。你自己要很喜欢,很多时候要保持一种平衡,不要太一心一意,不要变得很孤立。
胡:那你是如何保持这个平衡的?
张:就普通的观点来看,人家大概也觉得我很孤立,可是我给我自己出路。像我喜欢看电影,我就订了Netflix(美国在线影片出租公司),常在家里选好的电影看;我喜欢听音乐,也去参加音乐会;而我喜欢旅行,我跟建平有机会到哪里去,就在开完会后多留几天,到附近游玩。我觉得要一个平衡,不要太苦自己。要觉得有乐趣,你才会继续奋斗。人生要有一个平衡,你要觉得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不过即使这样,我女儿也觉得她小的时候我花好多时间在工作上。
胡:她的感觉可能是比较真实的。
张:她说为什么一个人一天到晚要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对着黑板,她觉得人生还有其他的事,更有趣。
胡:那他们小的时候,星期六、日不上学,你也做数学吗?
张:有的时候做数学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就放不下了,是自动的。不是我要怎么样。不过基本的态度是你要做自己感到有乐趣的事,要让生活愉快,我觉得很重要。
胡:你最近几年担任系主任的职务,女性的身份会否影响你执行你的工作?
张:做系主任碰到很多困难,我觉得这跟女性并没有什么关系。至少我跟同事之间的人事问题,不会因为我是女性让我处理事情变得困难。我们的校长是女性,也影响到学校的气氛。虽然这三年系里发生很多事情,我发挥了全力处理,但我不觉得我身为女性是个障碍。

张圣容院士获颁台湾清华大学荣誉讲座教授。
胡:你对台湾数学界近几年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张:我前几年当普林斯顿数学系系主任,虽然每年都回来,但多半是开会,停留时间不长。我对台湾数学界知道的不多,这次停留两个月是比较长的时间,希望有机会多了解一些,能够和同仁、较年轻的博士后及研究生谈谈。我听说现在的学生出国的很少,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
胡:那你对学生出国留学的看法如何?
张:台湾毕竟地方不大,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到外面去看看别人总是需要的,年轻人的眼界要宽一点,要去看世界。无论如何,以读书或博士后的方式总要到国外去待一阵子。不一定是美国,也可以是欧洲,这是个眼局的的问题,永远呆在台湾是不行的。旅行、各种方式到国外看看总是需要的。到国外去访问一年、研修等都是必要的。台湾的年轻数学家做得不错的也不少,但我所知道的年轻人很多也在四十岁以上了。再年轻的数学家我知道的不多。
张:另外,我感觉台湾在设备各方面都是一流的,设施、教室和邀请访问人员的经费都相对充裕。我听到的薪水相当低,我不知道和生活指数的比较如何,光看数字是很低。不只如此,在国外博士后和教授的薪资大约差三倍,就是说慢慢升等上去后薪水差很远。在台湾我的感觉是差距不大,最多两倍吧,恐怕还不到。你要鼓励这些研究人员前进,薪水要适度调整。
胡:我们现在也有弹性薪资,给研究表现优异的人员。
胡:学生特别是高中生常常问要如何念数学,你有什么建议?
张:数学虽然算是科学的一支,但更接近艺术或音乐,它极具原创性,可以有很多方法来学习及掌握。对我而言,我发现学数学就像学弹一首曲子或唱一首歌。你先学一小段基本的旋律,试着掌握它,然后再加上另一小段,再掌握它,期待慢慢的终究掌握了整个作品。熟记公式也是基本的功夫,不过如果你了解公式的意义,就容易记得了。
胡:学生还常问主修数学以后能做什么?
张:以数学为主修恐怕是最有弹性的专业了。在普林斯顿,据我了解约有一半的学生在大学毕业后念研究所,有些继续念数学,有些转财经、信息,还有进入各个应用科学的领域。另外一半进入职场,很多进入财经、金融的行业,有些进入如google、yahoo之类的公司,还有人去念法律。台湾的情形我就不太清楚了。
胡:感谢你的分享。
张:谢谢你的访问,和你相谈十分愉快。
张圣容教授简历
1970年 台湾大学数学系毕业
1974年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
1988年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教授
1998年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
2008年 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2009年 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2012年 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本文采访于2013年1月8日,地点为台湾大学天文数学馆727室。《赛先生》蒙张圣容教授授权发表。
投稿、授权等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您可回复"年份+月份"(如201510),获取指定年月文章,或返回主页点击子菜单获取或搜索往期文章。
赛先生为知识分子公司旗下机构。国际著名科学家文小刚、刘克峰担任《赛先生》主编。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赛先生”。
微信号:iscientists

▲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点击“阅读原文”,加入科学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