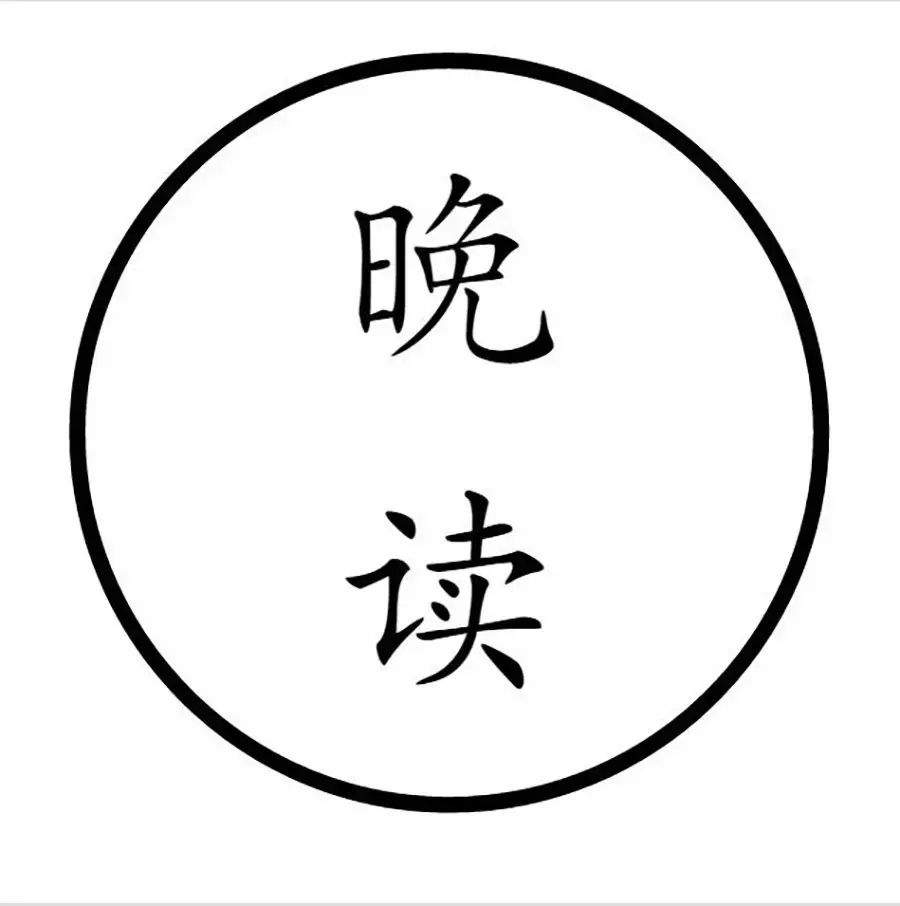作为“21世纪公共卫生领域最伟大的进步”,仿制药自问世起,人们对它便是“爱恨交织”。
以电影《我不是药神》为例,主角为帮助买不起昂贵进口抗癌药的白血病患者,从印度大规模走私低价仿制药卖给他们。影片中患者对于新药的渴求真实而迫切。
其成本约等于原研药的零头,仿制药的出现,意味着更多的患者能够更快、以更低廉的价格吃得上药 —— 这对许多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至关重要。尤其在当下,全球老龄化加速,医疗负担加剧,医疗保健支出在GDP的占比再创新高(注:2023年,全球医疗支出占全球GDP的10%,美国17.3%,中国7.2%)。
以美国为例,美国人每日服用的处方药数量高达1.31亿份,其中仿制药占据90%的比例。而在这些仿制药中,40%来自印度。也因此,仿制药出现之后,监管机构肩负着确保仿制药“等效”的重任,以确保使用者的健康的安全。尽管美国以严格监管著称,但面对仿制药,也暴露出诸多监管不力之处。
为之付出代价的则是患者本人。2023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将一家印度药厂生产的两款眼药水下架,称其与发生在美国18个州的81起细菌感染病例有关联,感染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14人失明。
凯瑟琳·埃班(Katherine Eban)是美国资深的调查记者,她历时十年(2008-2018)对仿制药的产业链进行调查,采访了举报人、调查员、医务人员,揭开仿制药生产链条的隐秘,写就《仿制药的真相》一书。
书中详细描述了印度仿制药生产灰色地带。在印度的生产车间,生产环境一塌糊涂,为了追求最快的生产速度和利润最大化,清洁和无菌无从谈起,工人缺乏规范操作指引,药物杂质问题层出不穷。而在药物申请、定期检测等诸多环节,都存在数据造假的问题。工人们也能够提前接到检查通知,充分准备以应对。
然而,种种操作之下,患者直面了巨大风险,这些药物从印度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患者们到手的药物可能含有有毒杂质、未经许可的成分、危险的颗粒物。
由于供应链条复杂,人们也很难知道这些仿制药在哪里生产、由谁生产,以及哪一种药物效果最佳。
在美国,一位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的患者服用仿制版防止器官排异药物后,因为急性器官排异症状再次入院;另一位患心脏病的患者服用了仿制版β受体阻滞剂(用于控制心率不齐,在首次心脏病发作后保护心脏)后,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呼吸急促和心律不齐增加了许多。
2018年7月,欧洲监管机构发现,在降血压药物Diovan的仿制版缬沙坦(valsartan)的一种广泛使用有效成分中发现了一种曾用于液体火箭燃料的致癌毒物。成千上万的患者进行投诉的同时,美国的药剂师们甚至拟出了一份对外保密的药物黑名单,上面主要是在印度生产的仿制药。
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派往海外的调查员被制药公司玩弄于鼓掌之上,他们读不懂当地文字,看不懂生产记录,翻译都是被制药公司的销售人员,这些公司把调查员领到假冒的“展示”公司里,里面看上去事事合规,但真实的生产并不在其中。
然而,政府机构不得不在足量的药物、成本和安全有效性之间做更多的权衡。《仿制药的真相》一书提及,一旦调查员查得更严格,审批员对于申请审得更严格,FDA不批准足量药物,整个医疗体系可能就会崩溃,出现全国范围的药荒危机。
也因此,调查员贝克发现,在2012年至2018年期间,FDA不顾明确的执法权和法律的明文规定,选择削弱视察力度,淡化调查员的发现。
他说,“那些公司生产了不达标的产品也不用担心后果,因为现在已经是赢家通吃的局面了,而输家就是患者。”
相关链接:都在喷集采药,救命级高质量仿制药公司一定要了解!【收藏】
以下是《仿制药的真相》节选(部分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