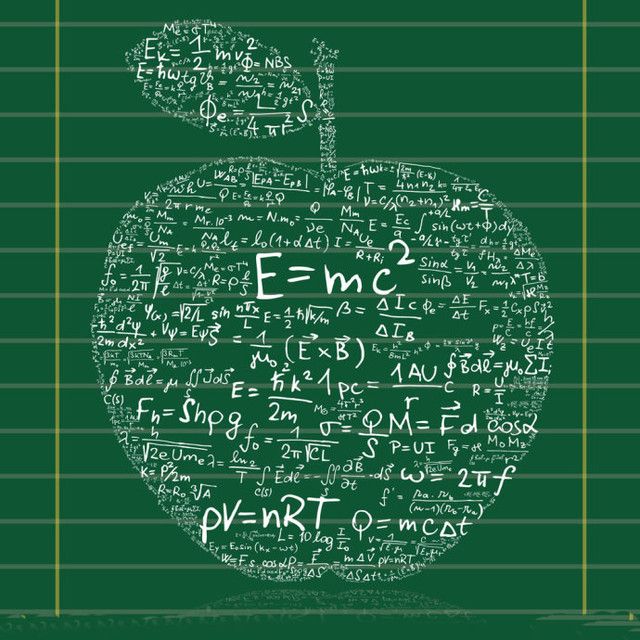本文转自中国科学院大学新闻网
2003年,38岁的卢柯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改革开放后当选年龄最小的院士,这个纪录至今仍未被打破。
在常人眼里,今年52岁的卢柯一直在“惊悚地成长”——16岁上大学,30岁当博导,32岁担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36岁出任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所长,38岁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40岁当选德国科学院院士,41岁成为美国《科学》杂志的首位中国评审编辑,48岁成为中国“万人计划”的首批杰出人才6位人选之一。卢柯的人生就像安了加速器,每一步都走得比同龄人更快更受瞩目。

熟悉卢柯的人都知道,他除了锻炼身体没别的爱好,一心扑在工作上:几乎每个晚上都有工作,每周只休息半天,离开金属所不是回家就是去机场——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交流和会议,其他地方几乎不去。他把自己定位成职业科学家,“不做科研,还能做什么?”
他效率非常高,几乎是用半天的时间就能把一天的活儿干完。他一直在加速理解什么是科研,加速实践自己的科研想法。他的理由是:“越早经历,越早能修正自己的错误,死之前做有价值事情的时间就越多。”
为什么能这么快呢?卢柯认为客观上是自己运气好,主观上方法和努力很重要。学习有学习的方法,做科研有做科研的方法。跌跟头爬起来也有爬起来的方法。他的方法是“讲求效率,缺什么就学什么,不被动等待。”
16岁,卢柯考入南京理工大学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志愿是父母填报的,他根本不知道材料是什么。大四做毕业设计实验时,他能动手做了,才觉得有意思。“感兴趣了,毕业分配又不想回甘肃,那就考研吧。”可考研很费劲,他高考分数超甘肃录取线60多分,但全系120多人,他入学成绩倒数第二,高考英语也只有30多分。
那就从头学起,他玩命学英语,把专业最经典的英文原版教材——《位错引论》,花了一年时间翻译成中文看。一年后,他考研总成绩是系里考中科院的学生中最高的。
读研时上课少,卢柯很多知识都自学。做实验需要物理学知识,他就捧着《非晶态物理学》自学,把书都翻烂了。到德国读博士后,他发现自己的热力学知识不够,就找书从头开始看。学完后,他还用热力学方法对自己的研究做了一个系统计算,这个计算让他发了一篇论文。
现在,他的学生做实验碰到热力学知识来问卢柯,他都能迅速地给出解答。学生诧异:“老师你怎么对热力学这么熟悉?”他就说,“热力学是我自己学的,所以印象极其深刻。你缺什么,就要自己去补什么。”

卢柯课题组合影
实验做完了,理论上解释不通也要去学习。2011年,卢柯开创了梯度纳米结构材料研究领域。研究之前,他只知道自己有点思路上跟别人不一样,他期待这一点能带来什么变化。实验结果让他惊讶,他一度无法解释金属中原本不相容的“高强度和高塑性”为何能在纳米尺度下兼得。他向人请教转换思路,从力学性能本质出发去分析,最终才弄明白。
卢柯总结自学的经验:“自己先琢磨,琢磨不透就去找人问。你就说,这个是什么,我看不懂,你给我讲一下嘛。我去问,你觉得我笨又有什么,我就这样。”最近,他又开始自学界面方面的教课书了。
研究生毕业后,卢柯才确定了自己的兴趣——纳米材料。他想探究纳米尺度的材料能带来什么。他觉得确定的时间有点晚了。
2016年5月19日,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的科学前沿进展讲座上,他把自己的求学体会转送给在场的300多名国科大本科生:“去找兴趣,越早找到越好。国科大的科学前沿讲座涉及各个领域,是找兴趣的好机会。”
“这一轮精品讲座扫下来,你对什么感兴趣,你到底喜欢什么,应该会有点思路。至少你能了解到老师们的兴趣。有时候,改变你兴趣的,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人。你跟了一个导师,这辈子就可能‘捂’进去这个领域了,能‘捂’进去是好事儿。”
“捂”进纳米材料领域后,卢柯一直专注于对材料“制备-结构-性能”关系的思考,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2000年至今,卢柯课题组先后研究出“纳米孪晶结构”“梯度纳米结构”“纳米层片结构”等几种新型纳米结构,研究水平国际领先,为开发高综合性能纳米金属材料开辟了新途径。
不是没有过挫折和痛苦,卢柯的实验也曾好多次做不下去。他说,“做不下去时,就跳出来,放到更大的视野下去看看。”
1998年,卢柯在参加学术会议的路上偶遇一位国际大牛,他兴奋地说起自己在做的表面纳米化研究。大牛一瓢冷水泼下来,“你去看某某人的文章,有人早研究过了,nothing new。”
备受打击的卢柯并没有叫停实验。他读完文章后,仔细分析别人做了什么,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他和学生花了很长时间做样品。从1997年—2005年,第一代样品做出来,卢柯觉得“完了,就到这儿为止了!”样品坑坑洼洼,粗糙度太大,根本看不见表面纳米层对力学性能的效果。
“要放弃吗?”
“要放弃,这是技术问题,但大目标不变。”
“万一错了呢?”
“有可能错,那你也得承受。科研有风险,这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
“跟谁斗?”
“跟自己斗!”
卢柯扔掉第一代样品,扔掉了之前的原理,换思路带领学生又做了五年,还是什么都没做出来。不过,这回他认定自己的思路是对的,不放弃。

2016年5月19日,卢柯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前沿进展讲座现场
一年后,“两头粗中间细,界面光洁,强度和塑性都很高”的梯度纳米结构样品就做出来了。2011年,这项成果被发表在《Science》,起初大家都不相信能实现,后来又都跟风做。2015年,美国材料学会秋季大会上,还开设了专门研讨 “梯度纳米结构材料”的分会。
同时期,卢柯课题组还开展其他多项研究。2003年,他们发现利用表面纳米化技术将铁表层的晶粒细化到纳米尺度,其氮化温度显著降低。表面纳米化技术成功应用到了宝钢集团冷轧厂的拉矫辊上,大幅提高了拉矫辊的使用周期。
像这样能在短时间内投入使用的材料和技术是少数,“99%的新材料都停在死谷里,等待着走出去。”材料研发过程的复杂性、长周期、大尺度跨越、低成本要求,卡死了很多新材料走向实际应用,也让卢柯和很多从业者感到不幸,“大部分人在死之前,是看不到他研究的材料能用上的。”
经常会有人质疑:中国的制造业不行,是因为材料不行。卢柯觉得很冤枉,“美国、日本制造业发达,不仅是材料好,是整个系统都好。我们材料可以做得很好,但其他环节中只要有一个出问题,就不行。”
新材料使用前要经过4个阶段:发现新材料—发现优异性能—材料研究与发展—材料应用。在最关键的“材料研究与发展”阶段,又要经历“材料—部件—系统”3个维度的转变。每个维度都有不同领域的人在做,很容易产生断层现象。
这种断层是不幸的源头之一。“做材料的只关心材料能不能做出来,具有什么组织结构,什么性能等;做部件的只关心技术能否实现,成本低不低,批量生产可不可靠等;到系统时,又只关心系统的设计、稳定性、制造、功能、成本等。”卢柯说。
卢柯能把控的是要求自己和学生:“既要有技巧把材料做好,又要看到部件和系统对材料的需求。既要创新,又要在漫长研发周期中,学会坚守。”
“坚守什么? 坚守对基础知识的探索,坚守精益求精。不求甚解,是我们落后的原因。”卢柯反复告诫自己的研究生。
“与其说我们和国外的差距是材料技术上的差距,不如说是差在我们对材料本身的理解上。你都不知道这种制备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构,这样的结构能有什么样的性能,你怎么能控制材料?” 在5月19日的讲座上,卢柯与本科生分享自己科研体会:“我们经常做的是把国外的东西拿来解剖,然后照猫画虎地做。人家是按照自己的知识体系建立起来的,我们画出的永远是猫。虽然现在引进技术,能让我们快速地走到一个阶段,但是我们很难突破,我们完全是在学习别人。”
卢柯认为:“要想有所突破,你就要从根上做,最基础的开始做。”计算模拟能简化材料设计,但是材料科学的基本规律,还有很多未知的。他说,“千万不要因为模拟计算量增大,就减少基础研究的实验工作量”。
他强调,“坚守似乎不是创新,但是它是把你的创新变得有价值,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卢柯经常拿网球来举例问学生:“知道业余选手的我和网球天王费德勒的差别在哪儿吗?”“我是‘大概齐’玩一玩就行,自己打好一个球就很高兴,后面打得稀里哗啦也无所谓。老费的每一个动作、每个环节都是严格训练出来的,他必须按照职业要求来打,无论身体多疲惫,动作都要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