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高正良(同济大学转化医学高等研究院、医学院和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特聘教授)
8月24日,Cell杂志上发表以西南医学中心徐剑教授和复旦大学周峰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的文章 “In Situ capture of chromatin interactions by biotinylated dCAS9”,首次利用了“biotinylated dCAS9”的方法建立了高分辨率,位点特异原位DNA-蛋白质以及其他元件的互作网络(下图)(详见此前BioArt的报道:Cell:中美科学家携手打开解析基因组非编码序列的潘多拉之盒丨特别推荐) 。该工作是表观和基因转录调控领域的重大技术进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困扰领域几十年的技术瓶颈问题,第一次让领域专家看到解决这个技术瓶颈的希望;假以时日,必将触发新的技术改进、普及化和科学进展,甚至表观和基因转录调控领域的爆发式进展(在这个技术的应用中,本文将只关注反式因子研究这一块,也借回忆一些个人经历,展现这个问题的历史与重要性,希望能够触发青年学子对于科学和职业的一些有益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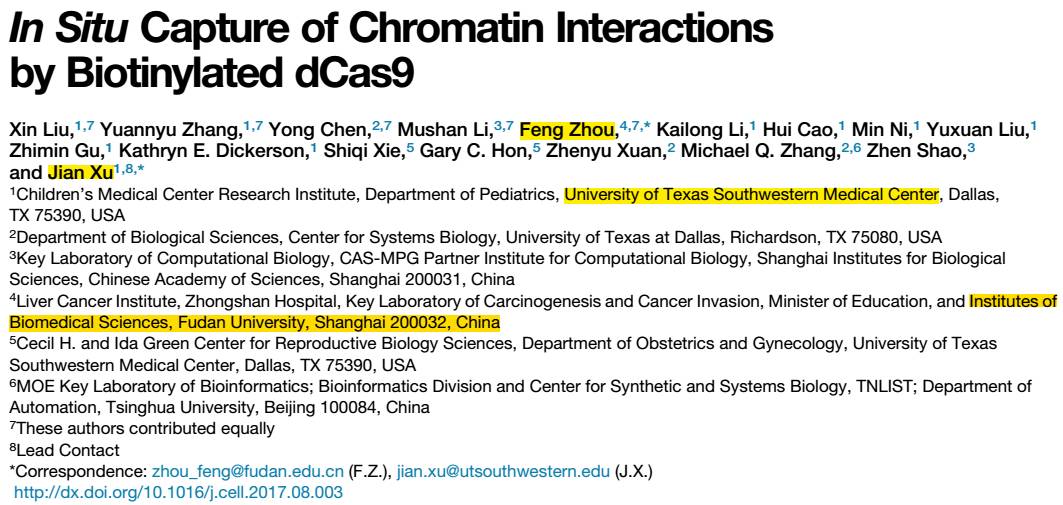
自从上世纪后半叶以来,人们日益认识到基因是生物的遗传基础,而基因表达则是生物表型的内在物质基础与机理。基因表达的调控,尤其是表观和转录调控更是首当其冲, 日渐成为现代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基础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基因表达的调控包含诸多维度比如信号转导,转录前(包括染色质构象和表观调控等),转录调控,转录后调控(剪切、编辑、转运等等),翻译和翻译后调控。其中多个步骤都是围绕着基因序列(DNA序列—传统的认为是顺式作用因子Cis)和其结合因子包括蛋白和非蛋白因子(传统地认为反式作用因子Trans)而发生。因此发现和解析这些DNA序列及结合因子并阐明它们的相互作用关系与机理是基因表达调控的核心内容;发展适当的技术,开展相关的研究则是核心的核心,关键的关键。如果暂时把高级构象和染色质生物学(近年研究前沿,值得几篇科普和前瞻性评论,这个领域不少华人学者表现耀眼,比如生物物理所的新秀李国红研究员等)搁置在一边,简单粗暴的分一下,基因的表观和转录调控有两个层面,顺式因子和反式因子,技术方法学也可以简单粗暴地分为以研究顺式因子或反式因子为主的两类方法学。
对于已知或候选反式因子(表观和转录因子)和顺式因子的研究手段较成熟,比如经典的EMSA,报告基因,ChIP等。给定反式因子,如何解析可能的结合和互作的未知顺式因子,尤其是在native 状态,unbiased 的组学水平上,曾经也是巨大挑战。但是这个难题在世纪之初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当时博士来自哈佛Tom Maniatis ( 美国科学院院士,2012年与 Donald D. Brown共同获得拉斯克基础医学特殊贡献奖,《分子克隆》的主编,第一个构建基因组DNA文库,第一个构建cDNA文库,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室(陈志坚、付向东、吴瑛、吴强等老师都来自这个实验室)的任兵老师(清华新秀颉伟教授的博后合作导师)正在MIT Richard Young院士(当时应该还不是院士)实验室做博士后,是第一个完成全组学水平转录因子CHIP分析的人(Ren et al., 2000),之后有一大批的华人学者比如阮一骏、赵可吉等等都成为相关方向的翘楚。任兵老师很快去了UCSD,成为领域的灵魂人物(也是冷泉港课程的负责人),The Young实验室更是在这个技术之后迅速成为年轻一代表观和转录研究者的梦想之地。

2012年拉斯克医学特殊贡献奖得主Donald Brown和Tom Maniatis
但是在另外一个方向上 ,即给定顺式序列,如何研究在native状态下与之相互作用的未知反式因子,几十年来一直是横亘在研究者面前的holy grail的技术问题,困扰着领域,也充满了鬼魅的诱惑,俘获一个又一个激情幼稚的心,我自己就是曾经的不怕牺牲、无知无畏的一个。
05年博士毕业前夕,遍访美国科学学院院士、HHMI、Top Universities和conference presenters 的网站,决定聚焦刚刚起步的系统和合成生物学,靶向治疗的抗性发生、预测与解决,日新月异的非编码RNA和表观调控领域,研究很薄弱的剪接调控,垃圾DNA、转座子、基因转换等(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DNA现象,但是却非常poorly 研究的,比如conversion and convection—可以看看Ting Wu的网站,很少有CNS,甚至所谓的好文章,曾经主要以Genetics 为主打,但是令人敬重的学者)。在旧金山与任兵老师的偶遇部分改变了我的聚焦方向:任兵老师不仅学术好,做人更好(颇有晋商之感哈);当他知道我是自费出来开会见世面,寻找职业发展机会,免费请我吃了2天饭。就是在这两天共餐过程中他“不经意”的点拨,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是否应该不考虑转录调控领域。旧金山会议回来后不久在Woods Hole 会议上遇见哈佛大学的马秋富教授,是神经发育转录调控方面的权威,开始更清晰认识到转录调控并不是一个over-crowded的方向,仍然是一个poor studied的领域,有很多重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后续的阅读思考中遇到的第一个重大bug问题就是很震惊(幼稚)发现了在native状态研究给定顺式序列的未知反式因子方法学的真空状态。尽管在非native 状态,有些方法,比如yeast/mammal cell one-hybrid、oligo array 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解析潜在地能够结合和调控给定顺式序列的反式因子,但是对于如烟的基因组的重要基因和位点,居然缺乏一个有效的可以研究其未知结合和调控因子的方法,这个发现足以让任何一个有科学激情的幼稚头脑亢奋,就像我当年一样:基因工程编辑一个特异性的顺式序列作为hook就可以了,这么简单,怎么会被人疏忽呢? 很困惑、很亢奋。当时潜在地可以作为hook的已经很多了,比如loxP、FRT、GAL4、MS2等,也可以考虑三链结构等(后来还可以用TALEN及Cas9等),还可以考虑做concatemers, 用BAC或者YAC一类的……想了很多可能,信心膨胀,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接下来的博后选择和职业的轨迹。
博后最后面试的是西南医学中心 Jenny Hsieh博士(博士导师RNAi 诺奖Andrew Fire,博后导师Fred Gage)的实验室,seminar之后,Jenny当即给了offer。第二天在Jenny的办公室从上午谈到下午,有关实验室规划、基金潜力、课题和我可能的职业发展与规划…基本决定不会选择去西南医学中心了,Jenny突然拿起粉笔,一边在黑板上画一边说,你觉得这个课题有没有挑战性和潜力……Jenny还没画完,我就脱口而出,that’s my idea! Jenny 转过头: what do you mean? It is my idea!……在Fred Gage院士(SALK,以JHU 宋红军为代表的一大批华人学者都与这个实验室有渊源,也是成体神经再生领域最大的一个pedigree)实验室Jenny尝试过这个技术,当时暗想她步骤里有多个不必须的地方,觉得自己的方案会更好。这个共鸣让我对Jenny实验室兴趣大增,决定回去仔细考虑…最后毅然决定加入…博后起始了多个课题,这个课题比较靠前,也是最快放弃掉的:在具体执行设计中,意识到这在当时是mission impossible;原因很简单,信噪比和质谱的敏感性,以前之所以亢奋是因为没有做好基本数学。
在一个双倍体细胞里,我们大多数人研究和感兴趣的顺式序列通常都只有两条,而与它们结合的反式因子(转录因子)通常不会超过4-8个分子。转录因子常是以同源或者异源二聚体作用,对于给定的顺式序列,结合、没有结合或者是单倍体方式结合,那能够拉下来的反式因子的数量一般应该在2-4个分子,多可达8个,少可至2,甚至1(想想imprinting)。 而在哺乳动物细胞中,反式因子常常是成千上万甚至是千万个分子。也就是说,要在这浩瀚的一团漆黑的汪洋里从成千上万甚至千千万万个一模一样的微小生物里抓住仅有1-8条口含微小标签的微小生物,这将需要如何高效精准,恐怕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也难以企及…
更悲催的是上述的挑战只是其中一个难关,事实上这个挑战本可以激发无数自信心爆棚的分子生物学技术男的征服欲,至少当年我就是这样,觉得会有一系列的巧妙的办法或技巧来解决或规避这个问题。而第二个挑战:质谱的分辨率和敏感性,成了压死绝大多数自信心爆棚的分子生物学技术男的稻草。当时的估计是至少需要1010-12个分子才可能完成这个实验,相当于103-6(1千-100万)盘细胞,意味着即便能够成功,这个技术上也没有事实上的用处……
所以多年来无数人想到过,Jenny想到了,我也想到了,MITBBS生物版在11-13年间还有过一次还是两次较为深入的讨论(我在这个讨论中泼了不少冷水,也许应该向某些人道歉了),无数的激情四射自信心爆棚的分子生物学高手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期间,最值得提到的是2009年的研究,据说是经历了多年审稿的折磨,来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David Kingston的实验室在Cell上报道了这个技术的雏形(Dejardin and Kingston, 2009)。这篇文章并没有在领域里引起波澜,原因很简单,是针对有很多个copies的端粒,但仍然用了20升HeLa细胞,大约3X10 9个细胞。对于单个基因序列而言,他们估计至少需要几百升细胞才有可能,显然这个技术对于哺乳动物细胞的蛋白编码基因的调控序列而言,基本等同于没有!
相信对于很多Hardcore 转录调控的研究者,这个技术问题会像魔鬼一样一直萦绕在心。2010-2011年,我开始思考和准备自己独立后的方向,决定选择当时人迹罕至的干细胞静息激活调控,聚焦表观和转录调控图谱,所以一边发展ChIP-Seq,自学生物信息分析,一边又开始琢磨这个技术。那时来自表观大牛Jerry Workman博士实验室的李兵已经在西南医学中心做PI几年了,成为我的球友和铁哥们,给我泼了很多冷水也给了不少建议,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这个技术问题是表观转录实验室共同的心魔;后来几年也多次同朋友们讨论,但是一直都觉得时机还不成熟……
突然就是8月24日的深夜,看到Cell文章的新闻,非常兴奋,亢奋的无法入睡,由衷的为这个技术,为徐剑、周峰和所有的作者高兴…在微信和大学教授群里盛赞这个突破。第二天从GJ那里获得全文,同朋友交换了一些意见,也从GJ和徐剑那里得知这个工作的艰辛,由衷的敬佩徐剑、周峰和所有作者的胆识、努力、勤奋、毅力和不放弃!
仔细阅读全文,技术瓶颈还是相当高的,挑战仍然在信噪比和质谱敏感性。质谱背景处理上要求比较高,需要技巧;每次试验需要0.25-1X109个细胞。这个细胞量对于工具细胞不能说太难,但对于绝大部分功能细胞,最需要这个技术体系的研究系统,是极大的瓶颈,对于微量材料比如早期发育的问题更是无法想象。显然这只是一个开始,徐剑、周峰和合作者们让大家看到了希望,我们有理由相信真正practical的技术就在拐角了,这个工作会掀起大家新的研究热情,技术一定会得到改进完善,推广应用,给转录调控领域带来新的机遇!最后,再次衷心感谢和祝贺徐剑、周峰和所有的作者,great efforts!
作者简介:高正良教授为上海市特聘教授,同济大学医学院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介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目前正负责筹建同济大学丽丰再生医学研究院。高正良教授主要从事神经和脂肪干细胞命运决定和表观转录图谱及临床应用、干细胞组织工程、器官重建、疾病和肿瘤模型等研究,相关成果主要发表在Nature Neuroscience、Nature Chemical Biology、J Neuroscience、Cell Death Dis.等杂志上。
参考文献:
1、Dejardin, J., and Kingston, R.E. (2009). Purification of proteins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genomic Loci. Cell 136, 175-186.
2、Ren, B., Robert, F., Wyrick, J.J., Aparicio, O., Jennings, E.G., Simon, I., Zeitlinger, J., Schreiber, J., Hannett, N., Kanin, E., et al. (2000). Genome-wide location and function of DNA binding proteins. Science (New York, NY) 290, 2306-2309.

温馨提示:日前,BioArt正式推出姊妹微信公众号“BioArt植物”。“BioArt植物”依托于“BioArt”, 致力于报道和评论植物科学领域最新研究进展。同时,“BioArt植物”会及时分享植物科学领域的重要会议信息。“BioArt植物”还设有招聘专栏,为PI免费发布招聘广告。扫描或长按下方二维码可关注“BioArt植物”,了解植物科学领域最新研究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