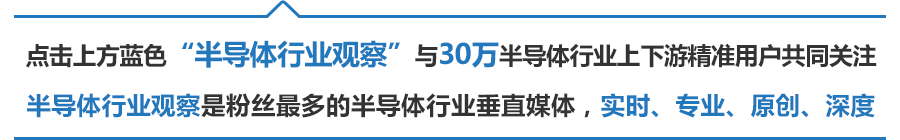第二部分:汽车的故事
![]()
让我们认识一下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汽车的人。
![]()
这个人就是康熙皇帝,他当时可能就是穿着这身衣服“开车”的。康熙皇帝在1672年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汽车——那年他18岁,送他这辆车的就是全世界第一位汽车制造者。
![]()
这个人就是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一位佛兰芒耶稣会传教士。很显然,他还没来得及把手放好,画师就已经完成了画像。南怀仁在中国度过了一生。1670年,他在一场历法推算的二人对决中胜出,于是成为大清帝国的首席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那场比赛的失败者是要被“凌迟处死”的。新官上任以后,南怀仁开始了他的发明创造,他的发明成果之一就是世界上的第一辆汽车,那是他送给皇帝当玩物的。这车很气派。
![]()
车身的大小并不足以承载驾车人,但是南怀仁解决了车的动力问题,即通过烧水产生蒸汽,让蒸汽集中作用于一个转盘,使其快速旋转,从而带动轮轴装置使车的后轮滚动。这就是南怀仁发明的全世界第一辆自行驱动车。
南怀仁的汽车都属于世界一流水平,直到1769年——那一年,法国发明家尼古拉·约瑟夫·居纽(Nicolas-Joseph Cugnot)终于想出该如何改进南怀仁的汽车:他发明了第一辆可以搭乘驾驶员的汽车。
![]()
这位时髦的小伙子叫François Isaac de Rivaz,于1807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内燃机以及一辆由内燃机驱动的小车。
![]()
![]()
蒸汽机是在引擎外部点火,加热引擎内部的蒸汽,从而带动其运转。所以它是一种“外”燃机。“内”燃机省去了蒸汽,通过在引擎内部燃烧燃料来产生能量。
直到1886年,第一辆具有实用价值的汽车才真正诞生,它是由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Karl Benz)和他的妻子贝尔塔·本茨(Bertha Benz)——如果是我,我也会爱上她——一起发明的(另外这位工程师的胡子也不赖)。
![]()
他们的汽车被认为是全世界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汽车——奔驰一号(Benz Patent-Motorwagen)。
![]()
“奔驰一号”当时耗资1000美元(约合今天的26248美元),有三个车轮,由一台非常原始的现代内燃机提供动力。
几年后,在世界的另一端——美国密歇根州,一个在农场长大、名叫亨利·福特的小伙子到托马斯·爱迪生的公司应聘工作,因为他觉得接管自家的农场会“无聊到老二不举”(原话)。爱迪生的公司当时正在为美国各个城市安装发电系统。这让福特接触到了公司用于发电的蒸汽发动机,并成为了这方面的一把好手。空闲时,福特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小车间里摆弄当时还属于新鲜事物的内燃机。
1896年,福特32岁,他制作出了一辆由一台简单的内燃机驱动的汽车,他把这辆车命名为“福特四轮车”(Ford Quadricycle)。
![]()
之后,福特越来越痴迷于制造自行驱动车。1899年,他辞去了工作,并成立了“底特律汽车公司”(Detroit Automobile Company),但以失败告终。随后他又在1901年又成立了“亨利福特公司”(Henry Ford company)。不过因为与公司投资者发生纠纷,福特很快又离开了公司,于是投资者将公司改名为“凯迪拉克汽车公司”(Cadillac Automobile Company)。1903年,福特和一个名叫亚历山大·马尔科姆森(Alexander Malcomson)的人合伙建立了 “福特&马尔科姆森有限公司”(Ford &Malcomson, Ltd.),后来更名为“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马尔科姆森简直气死了。
福特和他的新公司一上来就瞄准汽油车,但是在当时,汽油车还远非主流。汽车在当时属于新兴技术,在二十世纪初,美国40%的车是蒸汽驱动的,38%的车由电力驱动,汽油车只占美国汽车市场的22%。
这些数字是很说明问题的。以蒸汽为主要动力的外部燃烧技术是三种方式中最早出现、也是人们掌握得最好的技术,是早期最常见的汽车驱动方式。它的“表弟”——酷炫的内燃机是通过燃烧汽油产生动力,因为去掉了中间步骤,所以燃料燃烧效率更高。然而,崛起最快的汽车类型还是电动汽车,这并不令人意外——那是1900年前后,所有最酷、最新的技术都是依托于电力。
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世纪之交的35年时间里,托马斯·爱迪生、尼古拉·特斯拉、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乔治·威斯汀豪斯等发明家共同推动了一场电力革命,这场革命让整个世界从平凡无奇变成了充满“奇迹”。第一个奇迹发生在上世纪中叶,通过采用远程电力,电报使相距非常遥远的人们能够建立联系。1866年,第一份横跨大西洋的电报成功发送,从此欧洲和美国之间实现了神奇的“即时”通信。这场变革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达到了顶峰。1876年,贝尔进行了全世界第一次电话呼叫。紧接着,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录音和回放在1877年宣告成功。19世纪80年代初,灯泡的发明照亮了城市的大街小巷。1896年,第一张电网将电力大面积输送到人们的家中。同样是在1896年,第一部早期电影在纽约上映。1900年,第一次人声无线传输在巴西完成——无线电就此诞生。与此同时,无须依赖马匹的神奇汽车开始出现在马路上,而仅仅几年之后的1903年,莱特兄弟又实现了人类的第一次载人飞行。真难以想象在当时的人看来那是个多么疯狂而非凡的年代。
如果你生活在1900年,你很可能会把现代技术等同于电力,就像我们今天将现代技术等同于电脑、智能手机和互联网一样。爱迪生和特斯拉就是那个年代的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用一个燃烧生热的引擎来推动交通工具——这个点子可以一直追溯到最早的火车头,也就是将近100年前,这对于1900年的人而言已经很“现代”了,就像黑白无声电影对我们而言。到了1900年,你已经不必再去面对如何生成能源这种问题,燃烧的火焰只存在于远在他地的发电机中,而消费者只需要与安静、清洁、方便的神奇管家——电力打交道。
关于外部蒸汽燃烧、内部汽油燃烧和电力三种驱动方式中哪一种会成为未来的主流,1900年的人如果打赌的话就很可能把宝押在电力上。而在那时候,电力车不仅在绝对数量上超过汽油车,连世界最著名的发明家——包括爱迪生和特斯拉——都将精力放在了打造一个电力车的未来上。在上世纪初,《纽约时报》认为电力车是“最理想”的车辆,因为它比汽油车更安静、更清洁、更经济。
但是理想并没能成为早期汽车业的推动力——规模才是。在当时,汽车基本就是华而不实、供富人消遣的玩具。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理想才一步一步化为现实——第一步就是如何制造出快速、牢固、最重要的是买得起的汽车。世界各地的资金和人才都汇集到了汽车技术领域。1908年,亨利·福特及其成立五年的公司推出了使汽车业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的经典车型:T型车(Model T)。
![]()
在T型车之前,电力车和汽油车都存在很大问题。电力车续航里程短,充电时间长。汽油车噪音大,启动难,喷出的黑烟让人觉得仿佛回到了1802年。
但是福特是一位了不起的实业家,他发明了采用流水线安装来替代人工造车,从而将成本大幅降低,生产出了美国第一辆供普通大众使用的汽车。1912年,工程师查尔斯·凯特灵(Charles Kettering)发明了电动汽车启动器,免去了费力且危险的手动启动,而且新发明的消音器极大地减小了汽油引擎的噪音。仿佛一夜之间,汽油车那些糟糕的地方都变好了——而且变得比电力车便宜得多。福特T型车横扫美国。到1914年,美国新车中99%为汽油车。到1920年,电力车彻底退出了商业生产。
这并不是必然的结果。汽车市场的未来霸主依旧虚位以待,而福特只是比对手智高一筹而已。燃烧燃料的方式属于过去,而电力代表着未来——尽管如此,福特在汽车制造方面创造了一种被证实可行的、能够盈利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对于电力汽车而言尚不存在,而且很快,电力车制造商已很难扭转局面,情势变得极为艰难。因此他们选择退出。
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最原始的本地有线电话早已成为历史,如今的通讯图景已经变成这样:一个身在印度德里的人从口袋里拿出一部智能手机,用手指点一点,便能立即和远在圣保罗的朋友视频聊天。画质粗糙、断断续续的黑白无声电影已经变成如今精美逼真的皮克斯动画。在实验室里混合化学物质变成了在大型强子对撞机里分裂原子。莱特兄弟那段时长12秒、离地120英尺高的飞行已经演变为定期前往国际空间站、距地表250英里的太空之旅。
本来我很想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上面这个段落,“原始的汽油车已经变成了【我们无法想象得到的东西】”,无奈的是,我只能写成“原始的汽油车变成了更先进的汽油车。”
如上所述,如果你活在1900年,你很可能会觉得交流电感应电动车电机特别棒、特别未来主义,而内燃机仅仅只是在100年前发明的早期火车蒸汽发动机的基础上改进而来,虽然也不错,但不是很有未来感。遗憾的是我们并非活在1900年,现在是2015年,所以当我们看到所有汽车搭载的都是现代内燃机,看到活塞因为气缸内部高温气体的爆燃而上下翻飞时——
![]()
——你会觉得它们简直“古老得骇人听闻”。小插曲:
通过以一种外行人的方式描述汽车引擎的工作方式,Tim让爱车人士对车更加疯狂——蓝框内容
欢迎阅读 “Tim以一种外行人的方式描述汽车引擎的工作方式让爱车人士对车更加疯狂” 蓝框内容。我们是这样安排的:
上面动画里是一台四冲程四缸发动机。四根粗管代表的是四个气缸,活塞在气缸里上下移动。活塞向上或向下移动一次,被称为一个冲程,燃料燃烧以四冲程为一个周期,循环实现:
1)进气冲程:活塞向下移动,上方可以看到有蓝色的东西进入。这些东西是被吸进气缸的空气,其中混合了少量的汽油,那是由喷油器在最合适的时间喷射进去的。
2)压缩冲程:此时,活塞上移,蓝色物质变成了橙色。刚才进气口的阀门在此时已关闭。随着活塞向上移动,气/油混合物无处可逃,因此混合气被紧紧压缩。
3)能量冲程:在介绍这个阶段时,我感觉自己就像那些超级爱车人士,提到车时两眼放光。此时,活塞下行,上方的橙色物质最终变成了灰色。上一个压缩冲程已经将空气和汽油紧紧压缩,当混合气被压缩至最小时,气缸顶部的火花塞跳火点燃混合气,随之产生一次小小的爆炸。爆炸产生的压力推动活塞下行。这个冲程便是汽车引擎的动力来源。
4)排气冲程:在这个冲程里,活塞上移将灰色物质排出气缸。灰色物质就是尾气——也就是烟,因为你刚刚在气缸里点燃了一堆篝火——接着尾气会跑出汽车的尾气管。这种烟的成分主要是无毒气体加上微量的一氧化碳以及其他有毒物质。尾气中的二氧化碳也是在爆炸过程中产生的,汽油中长年不见天日的碳元素在地下埋藏了3亿年后终于得以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
四个活塞热火朝天地来回运动,一起奋力推动一个叫曲轴的东西——就是与活塞下方相连接的金属棍儿——正是曲轴的转动最终带动了汽车轮轴的转动。我想是这样。
回到正题。我承认汽车引擎很酷。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对它们那么着迷。但是当我看到以下两张图放在一起时——
1815年的火车发动机:
![]()
2015年的汽车发动机:
![]()
——它们是如此相似,根本不像隔了200年之久。
“气缸里的热爆炸推动活塞往复运动,带动金属杆转动车轮,并将燃烧产生的废气翻腾着排出一根管子”这听起来像是一种过时的技术,而我们今天还在使用这种技术,这真的很奇怪。无论现在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已经习惯了它,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历史并退后一大步来看,有些事情突然会显得完全没有道理。汽车发动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所以,我们要问的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既然电动汽车是更先进的技术,既然它们因为安静、清洁、技术尖端而被视为理想的交通工具,那么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世界放弃了电动汽车呢?在1900年,无论是电力或汽油车都无法实现大规模应用,因为两者都还有几个关键技术难题有待破解。汽油车所需的关键技术突破首先实现了——但是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愿意永久地满足于这种较为原始的技术、这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让我们的城市雾霾笼罩、还会改变大气组成的技术?既然二十世纪的发明能让我们在66年中实现从莱特兄弟的12秒飞行到登上月球这样的飞跃,那么发展一下电池技术,增加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降低成本并缩短充电时间是绝对有可能的吧。对全世界如此重要的一种汽车动力技术为什么就这样停止了创新和发展呢?
化石燃料时代这个大背景下的其他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比如对下面这个问题,你也会感到同样的迷惑不解,“美国第一座发电站——即爱迪生在曼哈顿建的珍珠街发电站(Pearl Street Station)——于1882年第一次点火,该发电站采用的是煤电技术——我们几十年前就知道燃煤发电不是最佳的也不是长久可持续的方法,为什么到了如今的2015年,燃煤仍然是人类生产电力的主要方式?”
“某项技术为什么会停滞不前?”这个问题的不合理之处就在于,人们误解了进步的产生方式。我们不应该问技术进步有时候为什么会止步不前,而是应该问:
技术为什么会进步?
第一个问题的错误在于人们直觉地认为技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而然地进步。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技术不会自己进步。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我现在的时代华纳数字视频录像机(Time Warner DVR)的用户界面和2004年那台一样惨不忍睹。在默认情况下,技术是静止的,只有当什么东西推动它前进时,它才会进步。
当我们思考进化这个问题时,我们常常会犯相同的直觉式认知错误。自然选择并不会使事物变得“更好”——它只是优化了生态,使其在所处的任何环境中都能最好地生存下来。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如掠食者变异后跑得更快、某一类食物变得稀缺、冰河时代即将到来等等,这意味着之前适应环境的物种不再适应。环境变化改变了自然选择的条件,对物种本身便产生了一种压力,随着时间流逝,物种的基因会对这种压力做出反应,改变其基因来适应新的环境。
对于技术而言,它的自然环境是一个完全自由、开放的市场。但有一点不同的是,生物世界就像那永恒不变的美国西大荒(Wild West),而人类社会中还有另一个因素在起作用——一种像上帝一样的力量,它的名字叫政府。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弄清楚是什么因素促使技术进步和改变,我们必须研究两种压力来源:一种是此消彼长、不断对环境中所有生物施加新的压力的自然市场条件,另一种就是那个可以人为改变环境、创造压力的“上帝”。两者都必须好好研究,我们首先来看看政府这个因素:
1)以政府行为为诱因的环境变化所导致的压力
政府这个上帝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中,其性质和力量各不相同。在朝鲜,这个上帝就是圣经中描述的宇宙中全知全能的统治者,它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自然市场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唯有上帝创造、保持的那个环境。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帝是一个富有而强有力的母亲,市场就躺在她温暖的怀抱中,安全而充满机会。在中非,上帝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它接受了一份新工作,也就是为最有钱的家庭打工——那可是在社会阶层上很大的进步。
在美国,上帝有点身份认同危机,总是在自豪感与自我厌恶之间徘徊纠结。它想创造一个最好的国家,但是却像是一个人站在街角大吼大叫,跟自己争吵未来到底该怎么走。如果美国政府(或与之类似的政府)想要扮演上帝并改变美国的自然市场环境,以便在某些方面施加一定的压力,那它主要会使用三种工具:财政拨款、监管和税收。
财政拨款:如果想通过政府财政拨款实现重大进步,那么拨款数目必须足够大,而在一个开放的民主国家,这个国家想要做的事情必须足够重要,以至于所有人都投赞成票才行——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当失去全球影响力的恐惧使美国政府肾上腺素上升时,美国政府把一个活人送上了月球。同样的,巨额的美国军费支出也是因为有足够多的选民支持,因此才获得如此庞大的资金,并在几个行业的技术进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分裂的民主国家往往会因为利益集团的冲突和政治口水战而瘫痪,根本无法推动一场真正的技术变革。
监管:民主政府的另一个力量来自于它可以制定规则,包括法律、限制令、配额等等。对于推动小的改变,这些是有效的——安全带和安全气囊就是政府监管的结果。但对于汽车业而言,我挠破头皮也想不出一项因为政府监管而产生的重大技术飞跃。
税法:政府经常通过税法来将自己的经济压力转移至自由市场。还是一样的,虽然这种方式可以将某些事物向某个方向稍稍推一下,但它往往不会催生席卷式的进步。
当然,美国对于这个问题争议很大,对于政府推进事物发展的能力,财政自由主义者的看法往往比财政保守主义者乐观很多。但我想两方都会同意的一点是,要想靠政府的力量推动重大技术进步,这种情况在苏联或现代中国更有可能发生,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在开放民主国家中诞生的了不起的创新往往来自民间的压力,来自那个充满生机的自由市场——
2)来自自然市场力量的压力
在自然界中,为了让自己既能成功捕食,又能远离掠食者的魔爪,动物们会优化自身条件——它们会加快自己的行进速度,不让任何人追上。当地面上的食物变得稀缺时,各种生物会感知到饥饿的压力,渐渐地,它们的基因会再次优化,发展出擅长攀爬的身体结构或长脖子甚至翅膀。一个物种从奔跑进化成具有飞翔的能力,并不意味着它变得更好——它仅仅是更适应当下的环境而已。在生物界,优化的定义很简单,因为最终目标很简单:生物的核心需求永远是一样的——生存和繁衍。所以优化在自然界的定义也一样:调整自我,尽最大可能保全自己并繁衍后代。
为了理解优化在市场中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市场上各个角色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当然,人也是生物,保全自我永远是第一目标——如果你饿了、冷了或是病了,满足温饱自然是核心目标。但是对于那些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的人而言,他们的行动动力之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深层渴望?“追求自身利益”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然,这跟文化有关。在某些文化中,人们极度害怕失败,以至于这种害怕超过了对荣耀或巨额财富的渴望,主要的内在动力变成了维持现状、得过且过。在其他一些文化中,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可能是宗教救赎、社区或家庭服务、悠闲的生活方式或精神启蒙。
就技术进步而言,此类动机恐怕是无法让人达成目标的,因为搞发明创新对这些人的自身优化并没有什么帮助。那么,如果想实现科技进步,人们的内心究竟应该抱有怎样的渴望呢?
我认为完美的配方是一杯“双层鸡尾酒”:
第一个成分:贪婪。在一个完美、公平、开放的市场上,贪婪是一种强大的活力源泉。资本主义理论上是这样运作的:谁创造的现实价值越多,谁赚的钱就越多。所以,处在竞争环境中的公司会尽可能创造更好的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以优化自身,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样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对个体而言,贪婪是他们达成各种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些目的包括一掷千金的生活方式、个人自由、安全感、被人崇拜、权力、性,但是,他们想要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只要他们内心熊熊燃烧的欲望之火让他们确实想要某种东西,他们追求自我优化的动力就会推动技术进步。不过,贪婪是一把双刃剑——要想发挥其有利作用,必须将其限制在一个高度自律、由精英领导的自由市场中。如果做不到,贪婪会变成阻碍进步的敌人,因为市场体系越容易出现腐败,贪婪的上层就越能通过操纵市场体系来确保自己永远是赢家。
第二个成分:雄心壮志。贪婪可以催生扎实的进步,但是为了使进步实现飞跃,第二个成分往往是关键所在:干出一番伟业的勃勃野心。同样的,这种野心背后的真正原因也是因人而异的。有时是由于个人主义驱使——想名扬四海、青史留名、百年后被人铭记为伟人。对于另一些人而言,野心是受一种近乎疯狂的自信和乐观主义所驱使,这使人有勇气做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些是饥渴的底层弱者所渴求的。
一个已经充满贪婪赢家的成熟行业就像是一片拥挤雨林中高度最高的树冠层。他们只会在必要的时候向上生长,他们争夺阳光,相互推搡只为那一分一厘的利得和胜利,绝大部分仅仅只是为了保留自己在树冠中的立足之地。贪婪要的只是阳光——它不在乎当它得到阳光的时候,它有多么高处不胜寒。
而在下面,那些饥渴的底层弱者不惜生命地争取阳光,每周花100个小时研究怎么才能获得阳光。当突破来临时,处在底层的人会冲破树冠层,尽情舒展枝叶,享受美好的蓝天。这时,原来处于顶端位置的树突然被挡住了。于是贪婪被更加强大的生存欲望所取代,他们努力攀爬争抢,使得创新这台机器在此时进入了高速运转状态。环境发生了改变——常态被打破了——在这个因为底层人的破坏而形成的新世界里,公司必须通过创新实现优化。有些公司重回树冠,有些则失败了——这整个过程的最后结果是,技术蹒跚前行。我们都见证过这样的事例:2007年,当苹果公司一路飙升、突破移动手机产业的树冠层时,它逼迫其它所有公司不得不生产智能手机,否则就是死路一条。三星成功地重见阳光,而诺基亚却没有。
记住这一切,让我们再回到汽车业和最开始的问题:
为什么汽车技术森林在过去一百年中没有向上生长?
我想到了两个主要原因:
1)进入门槛高得不可理喻——因此没有饥饿的底层人士带来飞跃式进步。
可以试想一下,还有什么事比创立一家汽车公司更麻烦、更艰难。
首先,在你卖出一件产品之前,你必须投入天文数字的资金来购买工厂、确定如何设计一辆车及其所有零部件,然后还要造出一辆原型车,用它来筹集更多资金、大幅扩大工厂规模、招来数千员工,再花上几百万美元做市场营销,让所有人知道有你们这么一家公司。你大概得非常非常有钱又非常非常有风险承受能力才行,因为基本没人会傻到去投资一家刚起步的汽车公司。
第二,为了实现盈利,你必须达到很高的销量。汽车的制造成本太高,销售利润太薄,所以一年只卖出区区几辆的话是没法维持生存的。因此,要想办车企,你不仅得设计出一款非常棒的车,而且还得是很多人都想买的那种。
第三,汽油车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优化——如果你想像默默无闻的底层弱者那样奋力突破树冠层,你必须造出一辆比现在市面上所有产品都要好得多的汽车。对汽车而言,这大概意味着在汽车的核心——引擎以及“突突突”地一直困扰所有人的尾气排放上提出解决方案。但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做过这件事,这就意味着你不仅要创造历史上第一家成功的初创汽车公司,而且你的公司还必须是有史以来第一家成功制造你所设计的那类车的初创公司。此外,因为你是第一家这方面的公司,你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用于创新研发,并承担整个行业的创新成本。你还得扛上客户培养的营销成本,告诉全世界人民为什么他们需要这种新型汽车——这是一种一次性支出,一旦成功了,其它公司就会搭上你的顺风车,利用你砸了无数钞票所建立起来的客户需求来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