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我一直想写写徐梵澄先生,却不知从何落笔,惶恐之中,只留下一地碎片……

一
2011年底,为立人图书馆推荐《梵澄先生》
(扬之水、陆灏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一书,推荐语云:“关于徐梵澄先生,无论其人还是其学,我并无作评的资格。近代中国,如康有为自号圣人,熊十力、梁漱溟等皆具圣人气象,不过我心中的圣人,却是梵澄。康之为圣,在伪;熊、梁之为圣,在狂;梵澄之为圣,则在澄明……”
美国人MarisL.Whitaker 曾在印度担任徐梵澄助手半年
(1970年)
,二十年后,她给詹志芳
(徐梵澄邻居,经常照顾其生活)
写信,说徐先生是她一生之中最为惦念的人:“遇到了他,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他是我衡量自己的标准。我希望人们都能与徐先生这样的人生活一段时间,这样他们就能认识到许多事情是有可能存在的。”
(孙波《徐梵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页)
二
1978年,去国三十余年的徐梵澄从印度归来。翌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彼时所长为任继愈。入所之前,徐梵澄提出三项要求:第一,不参加政治学习;第二,不带研究生;第三,不接受任何采访。皆被应允。
想起1953年底,汪篯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两封信,南下广州,请其师陈寅恪北返,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长谈,亲自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最终未被应允,中古研究所所长则由陈垣担任。
风骨相同,遭遇则异,时势使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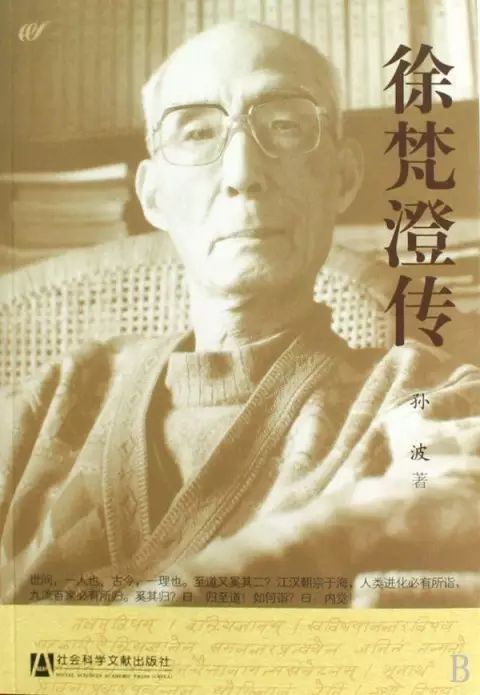
三
读徐梵澄,屡屡想起瞿同祖。二人相差一岁
(徐梵澄生于1909年,瞿同祖生于1910年)
,都是湖南长沙人,都曾长年游学异邦,巧合的是,都是1945年出国。不过,瞿同祖于1965年归国,徐梵澄则等到了1978年。这一区别,直接决定了他们晚年的学术命运。
瞿同祖谈回国后的经历:
虚度岁月,根本谈不上研究。刚回来时,在北京住了一年,安排不了工作;然后去了湖南,在那儿什么都没做,也安排不了;后又回到北京,住在宾馆里。那时条件不允许,也不允许做研究,根本谈不上研究了,北京还有图书馆,在湖南没有资料,那段时间可惜了。
1978年我工作调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打算再写本书。于是每天坚持坐公共汽车去王府井和美术馆之间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每天上午去,把要的材料摘录抄写回来,下午就不去了,因为到点就闭馆了,人家要吃饭了,我也要吃饭了,就回来了。但试了一两年就办不到了,68岁的人了,实在不行了,毅力也差了,实在是疏懒了。这样干了两年,到70岁实在不行了。我儿子倒是安慰我:条件那么差,年纪那么大了,受条件限制了。不过我觉得是个遗憾,到近代史所应该是做出点成绩的,但除了论文,别的没干出来。当时主要想研究的是清律。
瞿同祖一生共四本专著
(《中国封建社会》《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汉代社会结构》《清代地方政府》)
,皆为青壮年时期所撰。他回国那年55岁,正值一个历史学者的黄金年龄,然而自此岁月蹉跎,学问荒废。晚年与妻子合译《艾登回忆录》,编译《史迪威资料》等,只能说聊胜于无。
徐梵澄则幸运多了。最动乱的“文革”十年,他豹隐印度,一面修行,一面治学。归国之后,其心性直入圣人之虚静。故而晚年撰述自如,《老子臆解》、《陆王学述》等,皆可藏之名山。
仔细想来,却不宜将二位先生的命运之歧异简单归结于运气。他们何时返国,皆属自由抉择,这则关乎对个体的预期与对时代的预判。这两点,恰恰呈现了徐梵澄的高瞻远瞩。一个人,如果会通了中、西、印三大文明
(冯象称徐梵澄“是会通了中、印、西三大文明的罕见其匹的大学者,又是得了鲁迅先生亲炙的哲人和文章家”,见《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版,第147页)
,百年世事,则如眼底浮云。
四
据扬之水《读书》十年日记,1992年1月17日午后,扬之水访徐梵澄,谈去年最后一期《读书》,徐梵澄说李慎之一文甚好。李文为纪念某人,扬之日记,将此人名字隐去。徐梵澄言,某人一贯阿世,陆续为蒋介石政府捧场,为四人帮捧场,后来写书检讨。“那更不必,要就不做,做了,又何必去检讨?总是不甘寂寞罢了。”
(《十年(一九九一-一九九三)》,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40页)——
案,某人即冯友兰,李慎之文为《怀念冯友兰》。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辞世。日记所言检讨之书,应是《三松堂自序》。

五
徐梵澄与贺麟、冯至,相识于留学德国期间,互为挚友,终身莫逆。扬之水日记当中,徐梵澄常常谈及贺麟。他对贺麟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评语,叫“风云守道”,有风云之气,但仍守道;他自己只是守道而已。“守道”不难理解,他们都是知识人与哲人,道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风云”何解呢,可观这段对话:
徐:贺麟是有风云之气的。
扬:那么先生也是有的了?
徐:我可没有,我只有浩然之气。
扬:那鲁迅先生有。
徐:对,那是大大的风云之气。
——拉上了鲁迅,“风云”便不单是经世与事功,而接近于“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圣王气象。
徐梵澄还对比自己与贺麟:贺不甘寂寞,而我,甘于寂寞。这正是风云之气与浩然之气的差异。
1992年,贺麟逝后,扬之水访徐梵澄,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他沉吟半晌,摇头拒绝,说有一事对不起贺麟。据其回忆,1940年,贺麟与蒋介石结缘,他是推手之一。本来蒋复璁先找他,欲引荐给陈布雷,他坚辞,说你可以去找贺麟。后来贺麟被蒋介石接见,并拿到资金,成立了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
徐梵澄实在不必为此耿耿,假如贺麟像他一样,淡泊而有浩然之气,权力者的召唤则不足让他心动;反之,像贺麟这样不甘寂寞而有风云之气,即令不由徐梵澄推荐,他登龙门,却是迟早之事。
六
1996年初,陆灏“临时奉命为新创刊的文汇特刊编一个随笔副刊‘圆明园’,写信向先生组稿,希望他能继续写一点当年为《申报·自由谈》写的那类杂文,并建议把当年的文章结集出版”。
徐梵澄回信:
愚尝及见印度独立前一辈革命志士,鼓动风云,变化莫测。及至印度独立以后,有一雄辩之老革命党人,欲登坛有所言,尼赫鲁当时为首揆,止之。三问不可,遂寝其事。此无他,不必再闻其语也。日月出矣,爝火不息;刻舟求剑,其可得乎?时过一甲子,而足下犹以“自由谈”为言,陈年日历,何所用之?若谓陈言犹不无可采者,此则依乎所言是否尚有真理……
这便是智者。
1928年起,徐梵澄亲炙于鲁迅先生门下,对时势的判断,正得先生三分真传。鲁迅曾劝他:“捐生喋血,固亦大地之快,足使沉滞的人间,活跃一下,但使旁观者于悒,却是大缺点。……此外,作和尚也不行,我常劝青年稍自足于春华,盖为此也。”
徐梵澄的通透,可观其论史:“……黄石老人为什么与张良一约再约?不了解国民党统治下盯梢的险恶,就不能解当日的秦网如织,约在凌晨,是因为天尚未明,自然安全,约在五天以后,则因事过三天,不起波澜,大抵已是安全,五天,便更保险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