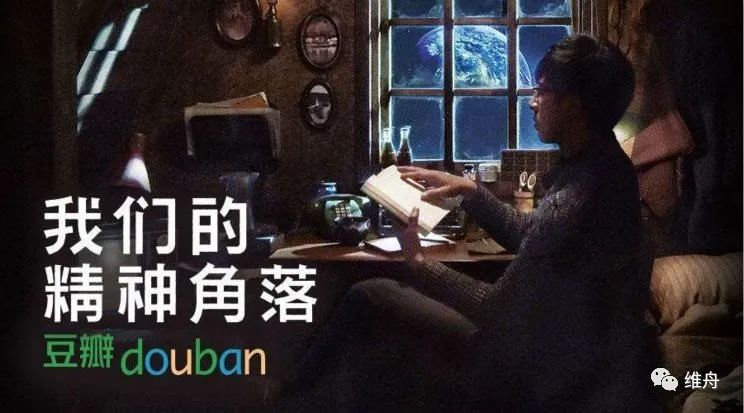
1
豆瓣自问世以来,已经十五年了。在盛衰无常的中国互联网界,这已算得长寿。五年多前,我曾写过一篇《从数据看豆瓣兴衰》,认为
豆瓣的成功之处,不在于比同行“跑得快”,而在于“死得慢”
。
当时,艾媒咨询发布的《2015年中国手机APP市场研究报告》指出,移动应用的生命周期平均只有10个月时间,85%的用户会在1个月内将其下载的应用程序从手机删掉,曾经强势出场的脸萌、围住神经猫、疯狂猜图等手机APP早已不再更新。这一点在近年的大浪淘沙之下,只会更为明显,有几家网络媒体能活过(且不说盛行不衰)十年?
一度曾是国内熟人社交媒体领军者的人人网,在经历多年业绩下滑、用户流失后,开发了直播、游戏、团购等功能试图挽救颓势,宣称“13年后重新登陆人人网,你会看到你青春的截止日期”,但用户上网看到的却是满屏的直播和彩票广告,更生反感。不得已,2018年,人人网将社交平台业务相关资产以2000万美元现金出售给多牛传媒。2019年底人人网再度上线,但2个多亿的老用户能否顺利回归却是最大的疑问。
在这一点上,豆瓣一直抵抗住了诱惑。它这十五年或许可以粗略划分为前后两阶段:2012年七周年之前是高速成长期,百度指数显示它在这一年的4月30日这周达到了此后再也没能达到的巅峰,2011年完成的C轮5000万美元融资也让它推出大批新功能;而最近的八年,虽然严格来说豆瓣并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但不同平台的分流、市场的管制和干预日益加大,使得它始终在不断挣扎调适中。
变化正是从那时开始的:2011年1月21日微信问世,公众号平台2012年8月23日上线,到2013年8月5日升级到5.0版,将公众号分为订阅号和服务号,凭借着腾讯的实力,内容创作大量分流。2013年3月,知乎正式面向公众注册开放。随即到来的,是2013-14年从美剧下架开始的视频网站整改。2014年可谓“移动化”元年,而豆瓣迟迟都未能推出自己真正的移动端产品,费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调适过来。
在市场上很少听到豆瓣融资的消息,给人的印象是豆瓣从未找到自己大规模变现的商业盈利模式,不清楚它靠什么赚钱,甚至怀疑它从未商业化过——它正式商业化晚至2017年。至少,它确实广告不多:豆瓣的销售总监告诉我,2019年豆瓣的广告收入不过2亿;2012年豆瓣日均PV 1.6亿,和微博相差无几,但微博2019年度的总营收则是125亿,其中广告和销售108亿,占比高达88%。这一点我的个人经验可以验证:业内一家数字媒体年投放额上百亿的广告集团,2019年在微博合作的投放量是1.5亿,但在豆瓣仅有不到200万。
微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太贪婪地追求广告变现,才使得媒体环境那么混杂。这里,还可以对比一下抖音和快手:虽然两者收入基本一致,但结构完全不同。抖音是广告模式,快手则是打赏模式,不依赖广告,也因此对广告的支持非常消极。快手市场更下沉,业务模式更偏重普通创作者,在流量分发上,不倾向于头部用户,甚至和谢娜等签约之后,还要求她停更,以免占据太多资源;抖音是相对更偏重高端点的市场,主推爆款。
相比起来,豆瓣则是既不怎么依赖广告,更少依赖打赏。在这一点上,豆瓣确实显得有几分清高,很多人喜欢的也正是它的不功利——包括我。以至于很多人都说,如果豆瓣活不下去,他愿意付费帮它活下去。

2
那时所谓的“死”,是指在市场上生存不下去。长久以来,豆瓣用户常常焦虑的一点,就是豆瓣会不会哪一天死掉,以至于我们这个仅存的精神角落,也死无葬身之地。但大体上,由于它不紧不慢、不温不火,看似踉踉跄跄、有气无力却又总是死不了的抗打击能力,这并不算是一个迫在眉睫要考虑的问题。
直到最近半年来,这个问题变得空前现实。2019年10月,豆瓣被封站两周,直至10月20日才恢复。这一天被许多人提议为“豆瓣复活节”,尽管有几分激愤,但整个的情绪是“紧密团结在豆瓣周围”的。那一天的狂欢气氛中,我还说了两句可能让人很扫兴的话:
复活是复活了,但在那之后,就一天天地“风刀霜剑严相逼”。这几乎是每个豆瓣用户都能切身体验到的,就我个人而言,去年9月第一次被禁言3天,今年1月24日除夕又被禁言7天,放出来才讲了5天,再被禁言15天,等到2月20日总算熬出头,才讲了1天,竟然再次被禁言15天!当时脱口而出:“我真去他妈的!”朋友说:“真没想到,连你都会爆粗。”
不仅是我,温和如邓安庆,也被禁言3天,这可说是象征性事件,意味着无论你多温和,都难例外。2月22日,豆瓣大赦,宣称此前一轮引发众怒的大范围禁言是bug所致,我也和很多人一样,收到一封邮件:“非常抱歉,由于系统bug,导致你的豆瓣帐号被禁言。目前该bug已修复,你的豆瓣帐号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我不相信这样的解释,也不需要这样的施舍,在长达整整29天仅有6天可以开口的极差体验之后,我已经完全不像前两次那么急着想出狱了。我决定继续自我禁言到3月7日15天期满。我深切体会到了《肖申克的救赎》里,老黑人瑞德的处境:他年少入狱,每过数年被提审,他都回答自己已完全改过自新,想出去重新做人,但却一再被拒;到最后再次被问及时,他答:改过自新?狗屁不通的词。我他妈不在乎(I don't give a shit)。
那段时间,日记功能停用、书影音条目不能添加或修改、广播下面的评论经常无法显示、广播动辄被贴上“与事实不符或谣言”的标签,真是“
建成‘都ban’指日可待
”(来自@Artful Dodger)。看到有人说:“我这几天看豆瓣的时候,发现有些原来每天发好多次广播的号突然沉寂了,后来才想明白大概是都陆续被禁言了。”2月23日,@PhoebeBuffey说:“我关注的粉丝超过10000的友邻,没有一个未被禁言过的。”
在中国的网上,每天都经历着“象征性死亡”——一些账号不知说了什么就被封杀了,另一些东西如果不存下来,很快也消失不见了。这让人产生了一种随时准备好后事的心态。现在,这样的状况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现在豆瓣上。
它曾经被很多人相信是国内最尊重用户的网站,也有人继续这么相信,但在这一轮“
豆瓣腾退
”之后,我是已经不相信了。显然,它看起来担心的不是用户流失这一死法——那至少是慢性病的死法,不是猝死。
2006年,豆瓣创始人阿北曾在接受天涯采访时说,如果强推商业广告,用户因为体验差而离开,对网站的损失要比收入更大。换言之,豆瓣曾为了顾及用户体验而选择少赚钱,但现在它选择的却是违背商业公司信条的双输:既不赚钱,还让用户体验极差。
的确,谁都知道豆瓣有它的难处,知道它的脆弱,很可能随时倒下,但给人的印象是:
它因为害怕他杀,就选择了自杀
。如果有一天它死了,或许它是他杀的,但很可能也是自杀。

3
作为一个精神角落,一个很多人最喜欢的树洞,豆瓣原先之所以在市场上活下来,靠的就是超强的用户粘性,但
现在它自己破坏了这种粘性,做到了竞争对手和豆瓣用户自己都做不到的事:
治好了他们的豆瓣依赖症
。
豆瓣是一个club,不是一个clan,不像在宗族制度下,哪怕是被逐的孤臣孽子,都仍然忠诚不舍。就像许烺光说的,在现代社会里,“许多俱乐部的生命十分短暂,因为它们是为某种特殊目的建立的”,加入一个club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但也因此更依赖每个人的主动认同,当他想离开时,没有人可以阻止他离开。
在这一轮肃杀之后,很多人都出走了,2月22日大赦日变成了离别日。8万关注(在豆瓣已经非常高)的王大根,在2月两度被禁言7天(其间间隔16天)后,发了最后一条广播,“现在的豆瓣对于我来说已经是最难说话的地方了”,“那我不说了,我什么都不说了”。另一位梅花牛,也因春节以来两次被禁言7天和3天,选择离开,因为“最近豆瓣变了。一个相处了十多年的朋友,突然戴上红袖章,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用户则变成了豆瓣的‘行货’”,这让他觉得非常没意思。6万关注的小杭,只丢下一句话:“散了吧,13年的号不要了,20年的名字也不要了。”
相比起来,我一个月里被禁言了3次,中间的间隔更短——所以,如何证明我更爱豆瓣?就是在这样一轮轮禁言之后,我居然仍未离开。但在被强制戒毒之后,内心已经不再依恋了。就像我的朋友田方萌说的,“
关久了,人就会产生另一种生活模式
。我在家里呆了一个月,昨天第一次出门,连怎么坐地铁都要想一想。”
在日记功能被停用一段时间之后,邓安庆说:“我已经不怀念日志了,有没有我都无所谓了。”去年船组八组闹到豆瓣广播被封,当时我简直气炸,现在好像也无所谓了。对很多人来说,
它现在变成了一个标注的工具,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它丧失了原有的社交属性
。我还会在豆瓣,因为就像波拉尼奥说的那样,“在这样的社会政治形势下,自杀很荒谬而且多余。最好是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诗人。”但对我而言,豆瓣已经不再是一个社区了,更不是唯一的社区了。
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之后,豆瓣就这样一点点死掉了。就像@阿修说的,“那个把我们聚在一起的豆瓣早已不在,我们只不过是尸体上的残余细胞,或余悲,或放歌都成,我看就不要再担心这、担心那了。”人慢慢地都走了,凋零到最后,或许即便还在,登上去还能看,但人不在了,这是最悲哀的死亡。
豆友@lowdive的一番话说得很好:这些年他拒绝了很多新平台的邀约,只专心在豆瓣创作,当然谁都知道豆瓣的难处,但希望豆瓣在面对压力时,“一定要勇敢保护你的用户们。他们去到其他平台,即使从零开始,也总会慢慢得到应有的关注;而豆瓣永封了这些用户,也就永远的失去了这些曾经在豆瓣不计回报的创作者们。”
豆瓣以前广告上的那句slogan“有人驱逐我,就会有人欢迎我”,俨然它是提供最后庇护的精神角落,我从未想到这句话可以反过来理解。现在,当豆瓣驱逐我,我也被迫复活了微信公众号,开始用以前一直抗拒使用的微博,甚至还开了百家号,它们也许不见得更宽松,但毕竟多个发声渠道总是好的。
这也许是豆瓣给我的最后的礼物:
通过强制断奶,迫使你离开它,独立于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