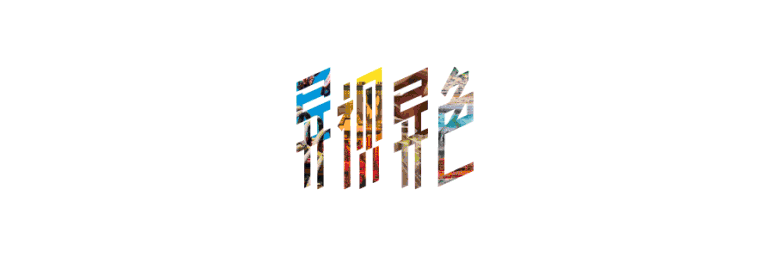
赵大明

连续几天凌晨,我都会从噩梦里惊醒。梦中我抱着相机趴在前线士兵的战壕里,端相机的手抖得像个骰子,根本拍摄不了一张清晰的照片;炮弹在战壕里炸开,落地之前会有像吹口哨的声响;越来越多的士兵包围了阵地,灰头土脸的我慌张地爬起来,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姿势,用蹩脚的英语说:“Don't shoot me! I am reporter”……
对死亡的恐惧让我在梦里惊醒过来,发现身在北京朋友的家里。他笑我:“你都战地摄影这么牛逼了,还不是得在我家打地铺?” 回想刚才梦中举手投降的样子,我不应该像电影里的那种视死如归的英雄嘛?不,更多得像一只失态的狗熊。
 难民营 本文所有图片由作者拍摄
难民营 本文所有图片由作者拍摄
去年12月,我听说缅甸北部有难民小学,便辞掉工作想去拍点什么。最开始是一位支教老师告诉我那里的孩子上课都能听到枪声,我觉得他肯定是想把我骗过去拍照。了解一些情况后,他介绍了一位当地做生意的中国人,我便用一天的时间赶到了云南边境。
车站旁边很多摩托车大哥在吆喝,“迈扎央,30元,30元!” 摩托车大哥看着我一身外地人的装扮,凑过来问要不要走小路去缅甸赌博。我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势摇头,去小卖部买了两包烟。为了掩饰我忐忑不安的内心,即使不会也只能抽着装装样子,等待线人接我走小路赶往难民小学。两颗烟的时间,做生意的中国线人出现。相互寒暄之后,我坐上他的摩托车驶向边境线。
 难民小学
难民小学
难民小学在山顶的一片空地上,是用帆布和树枝搭起来的帐篷。除了60多个孩子,唯一能证明学校身份的,只有两块黑板和木头搭成的简易桌椅。老师是一名小学毕业的小伙子,他无奈地说,“在整个缅北边境线,8到16岁失学的孩子有近2000多名,很多十二三岁了都写不出自己的名字。还有些孩子外出打工或者嫁人,能读完小学就已经算学历很高的了。”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我不会相信有这样的地方。而真正在那儿时,我发现这和噩梦没有区别。这种生活叫做 “借土养命” —— 只是用借来的土地生存。我以前认为做一个中国人没什么了不起,但此时此刻,自豪感和走运的感觉同时生出。这就是战争,离我这么近,又如此荒谬。
 玩枪的孩子们
玩枪的孩子们
前线阵地是一处高山,与难民小学直线距离只有3千米。调皮的男孩们用树枝制成木头枪,分成两队在丛林里玩游击队的游戏。那个时候,孩子们的表情和暗号像极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在全民皆兵的缅北,孩子们都见过真枪实弹,参加战争只是年龄问题。我遇到一位十岁的孤儿,父亲战死、母亲改嫁,他已经被军队收养。“现在孩子抬不动枪,所以在学校学习,等长大了就可以扛起枪去战场”,代课老师无奈地说。很多孩子的练习册上都会有一些关于战争的涂鸦。
 李晓英
李晓英
难民营就在小学旁边,非常大一片,全是几根木棍搭起来的帐篷。一位老人冲着我说,“家里的粮食都没有来得及带走,就匆忙逃离到中国境内。现在真正的是四海为家,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 —— 就是苦了这些孩子”。李晓英今年31岁,两年前走小路回缅甸,想去家里取2个水桶,结果在边境线踩到地雷。当时救护车赶不到,丈夫用摩托车把她送到医院急救,截去了左腿下肢。缅甸的政府一直没给一个说法,家人只能自费去医院,花费了家里积蓄5万多元。她说:“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变成一个残疾人,也从没想到战争距离自己这么近”。炸断腿之后的她再也没有回去过缅甸的家,也再也没有买过一双新鞋子。甚至在腿刚被炸断的一段时间,她一度想自杀,但是看了看自己的3个孩子,她说她要选择了活下去。
 瞭望塔
瞭望塔
由于线人的关系,我们走小路赶到了前线阵地的一处营地。这里是山头空地,周围好多战壕。非常隐蔽,却没有电,只能靠太阳能使电灯泡,就连手机都不行。带着两箱啤酒和一条烟过去,向导告诉我千万不要随便走动 —— 为了防止敌人偷袭,附近埋了很多地雷。这是一支五人小分队,有人只能说几句简单的中国话,但性格却和我们很相像。递上烟,在小板凳上喝几口酒,便打开了圈子,借着翻译聊下去。
我留着蘑菇头,满脸笑呵呵的,很害怕哪句话说错了就被一枪放倒。但他们完全没有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的状态,反倒是老乡一样亲切,也没有士兵杀人的气场。他们很欢迎外地人来,因为这里除了站岗什么事情都没有,太无聊了。
年龄最大的老兵金卡利51岁,一直在吐槽好久没回家了。他养了3只老母鸡,等鸡长大了就可以吃肉。金卡利开玩笑说:“来前线已经7个月了,没有见到过长头发的人(女人),唯一看到和我们不一样的就是这些老母鸡。”
 检查武器
检查武器
金卡利向我介绍武器,一蛇皮袋子的手榴弹在屋子里拎出来,每个手榴弹上都写了数字5、7、10 —— 写的几就是几秒爆炸。每个士兵标配是4个弹夹、120发子弹和8个手榴弹,还有更多武器被埋在地下准备打大仗的时候使用,只有班长和队长知道埋在哪里。
缅北有一个说法:“连鬼都怕他们当兵的”。打扫战场的时候,不管敌人死没死,他们都会在脑袋上补上一枪,美国大片里装死的桥段根本不好使。
 守望者
守望者
夜幕将临,阿超坐在营地前的大树下抽闷烟,我走过去想和他聊聊。阿超喜欢在木头搭成的瞭望塔上唱歌,用的是克钦族语言,撒娇地语气唱着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为了让弟弟妹妹读书,他只能选择参军。他还像个高中生一样孩子气,一脸羞涩地看着我。
 金卡利
金卡利
傍晚时分,营地周围出奇的安静,51岁的金卡利班长抱着枪躺在床上, 我就躺在他旁边的木板床上,老爷子看我睡不着就安慰我说:“小伙子,你放心睡,我们这里距离敌人阵地还有3公里呢,营地周围我埋了好多地雷,你放心睡就好啦。”虽然抱着枪,但他安慰我的语气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爷爷。
那一夜,我没敢合眼,脑袋里浮现的全是电影里深夜偷袭营地的画面。我才25岁, 还有大好的青春年华呢。看着老爷子抱着枪睡去,应该会梦到抱着自己的老婆睡觉,醒来却是冰冷冷的枪。
 坟墓
坟墓
第二天早上离开的时候,营地队员笑呵呵地欢送我们下山。他们不想让家人知道现在前线阵地的情况,可他们知道如果自己牺牲,可以得到不等的赔偿留给家人 (大概400到3500人民币),那样家人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一个人的死去换来全家人的好生活,这他妈的不是沾满血的馒头吗?营地的一旁就是士兵坟墓,插着简易十字架。“深山坟场里尸体的腐烂味道会引来狗熊,把尸体挖出来吃骨头”。这句听得我后背直发凉。
 受难耶稣
受难耶稣
下山的路上,我碰到一位赶去教堂做礼拜的士兵。他背着吉他,左手拿着圣经,右手扛着枪,匆匆赶路。没来得及举起相机,士兵就消失在从林里。沿路往深山走,我发现一处荒废的村子,向导说这儿已经荒废了6年多。稻草人在庭院里静静地呆着,等着主人归来。我走进其中一所民宅,墙上挂满了耶稣像,也许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的住处,而满地狼藉已经证明宗教没有阻止战争的蔓延。
看到这么多战争的荒谬之后 ,我匆忙催促向导赶路到拉咱 —— 克钦独立军的首府。一路颠簸的山路上,我抽了好多烟。向导和几个当地朋友约去 ktv 唱歌,我也赶过去凑热闹。包厢里,一位30多岁的大姐带着4个士兵,陶醉地唱着恩恩爱爱,些许的市井气让我意识到终于回归到了正常人的生活。喝完3瓶啤酒后,大姐过来敬酒,她告诉我她是中国人,来缅甸是做玉石生意的,同行的4位士兵都是保护她去买玉的。和玉石姐盛情喝了3瓶之后 ,我意识到我快断片了。玉石姐摸着我大腿趴在我耳边说:“这里太吵了,我们两个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喝酒”。我只记得玉石大姐的口红特别醒目,是血红的颜色。恍惚中,4位士兵大哥虎视眈眈地看着我,我竟然还看到了他们每个人腰里的手枪,我心里想,“此地不宜久留,老子要撤,否则得挂在这里。” 借着上厕所的理由,我麻溜地滚回酒店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赶回中国边境。在回昆明的大巴车上,有一位乘客大哥看我长得特别黑,估计以为我是缅甸人,递给我一颗中华烟,凑过来问,“你知道哪里能买到缅甸媳妇吗?我是过来买媳妇的。” 我故作深沉地抽了一口烟,没有说话。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不会吸烟,只是把它吸进嘴里吐出来。
现在回想起去缅北的经历,真的算堵上了一切。朋友笑话我说.:“人家都拿着相机去泡妹子,你他妈的拿着相机去拼命。” 的确,最后我他妈发现,原来什么都改变不了。对于当地人,我只是一个过客,也只能是一个过客。而这趟旅行唯一让我舒口气的地方,是在回到中国之后。我找到昆明的一个公益组织,在他们的帮助下,李晓英七月份装上了义肢。
下拉进入缅甸北部的炮火世界 (请勿效仿作者行为):


 医院里的伤兵
医院里的伤兵
 前线士兵
前线士兵
 死神的袖子
死神的袖子
 怀中的猫
怀中的猫
 玩枪的孩子们
玩枪的孩子们
 孩子们的涂鸦
孩子们的涂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