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
——《从前慢》.木心
我最后一次焦急地等待邮递员,大概是在前年的夏天。不是等待买买买的快件,而是等待一张来自尼泊尔的明信片。
明信片最终不知遗失在辗转走向我的哪条路上,我日日去问单位收发员,有没有我的信件,他很奇怪又见怪不怪地说:“这年头,还有人写信吗?”
嗯,的确。不知何年何月起,邮局里所投递的信函除了广告就是各种中奖或参赛的邀请函。再没有人会认真写一封信去投递,去等待对方展信阅读;如同再也没有人会有耐心去等待,等待云中谁寄锦书来。
让我想起之前曾经嘱咐我一位同学,去我去不了的地方时,要记得寄明信片给我。所以他在剑桥给我买了明信片,转机戴高乐机场又买一张,然后回到国内,珍重至极的用信封装好给我邮了过来。我当时笑了又笑,为收到两张崭新的明信片。如今想起来,他一定是未卜先知,怕那些明信片,会走失在历经千山万水的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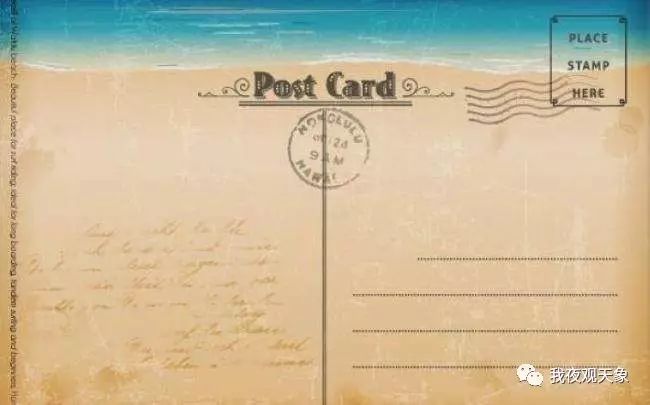
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封信件是我哥写给我的,夹在大人的信封里,薄薄的一页。信封上的收信人并不是我,想来这并不能算是正式的信件。那时候,我才是七八岁的光景,哥哥在信中楞充大人的口吻,教育我好好学习,听爸妈的话,没事要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等等等等。我回信说了啥不怎么记得了,想来无外乎是表决心、立壮志之类的豪言壮语吧。前几年在我哥家收拾东西,翻出一封我高中时期写给他的信,既有青春期小姑娘的迷茫与幻想,又有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让我看了很是脸红,赶紧叠成小豆腐块给偷了回来。
如今我哥在我面前,总是对我谆谆教导,想来应该是从小通过鸿雁往来养成的习惯。以至于我每每听到他给我讲人生道理的时候,眼前会自动幻化出信笺,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会慢慢在其上洇成一封书信模样,上面是他多年练书法成就的字体,铁划银钩,矫若惊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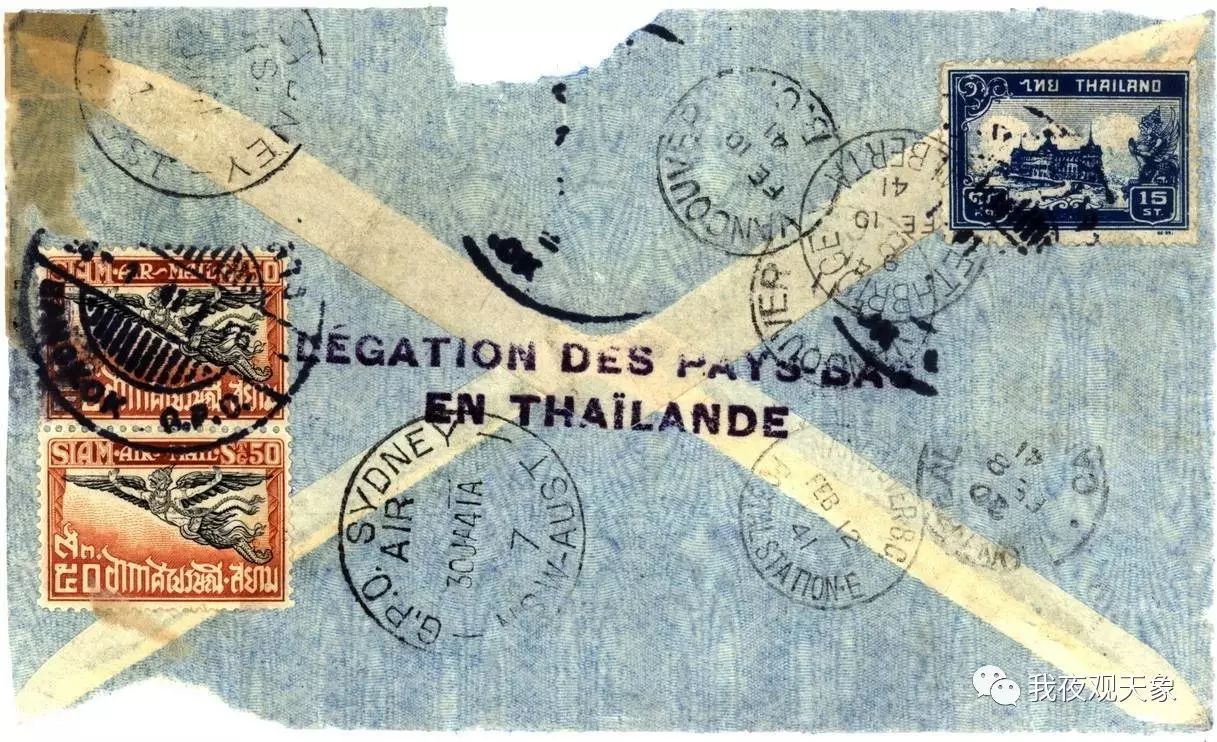
高中时期经历一次与好朋友的分别,她去了遥远的北方,从此我们俩把思念诉诸笔端。她给我讲诉新环境、新朋友、新际遇,我给她汇报老同学的新状况、老县城的新变化。整整一个高中到后来的大学时期,我们俩都对对方了如指掌,收到了仰慕者的小字条、上学途中遇到了心仪的男孩子、考试有了小小的进步、北方飘起了第一片雪花、春天的第一次郊游......
偶尔会有小小的不快,也会在信件里倾诉,等下一次收到回信被询问心情是否已经好转的时候,却早已把沮丧抛诸脑后。往往要回想半天,我上周为了啥事不开心来着?
好可惜信件不似“伊妹儿”一样可以备份,所以要在脑海中细细的回忆,回忆上一封信写过了什么内容。
好庆幸信件不似“伊妹儿”一样可以备份,所以每一次的回忆,都会带来嘴角上扬的弧度。
她的字端庄秀美,如同她的人儿一样,秀秀气气。每一封信,都如同她在我的面前,将趣事乐事美事,对我一桩桩娓娓道来。
我有一位朋友,与曾经的男友是初中同学。她踏入高中校门,男孩子应征入伍,从新兵连的时候开始给女孩写信一直到退伍归来,积下了厚厚的信件。他诉说着部队里的一切,她讲诉着校园里的种种。当她进入大学校园的时候,他正好退伍归来。一切似乎顺理成章,她(他)们也从纯纯的革命友谊发展为朦胧的青春恋情。
一切美好的恋情都以为会有一个天长地久的结果。只可惜,人世间,很多美好的愿望并不一定能天遂人愿。
男孩子有个习惯,会事先写好一迭信封,粘好邮票,每每完成一封信,直接填入信封。可是,也是这个习惯出卖了他,女孩子有一次发现,书桌上厚厚的一迭信封里,居然有一部分填写的是另一个女孩的地址和姓名。都说女人的直觉最准,当然也最可怕,那一瞬间,她知道,他的心,有一半已经不属于自己了。当她决然离开的时候,自己早已泣不成声。
厚厚的信件,全部被付之一炬。黛玉焚稿时的泣血,也不过如此吧。一切,起于信件,最后也毁于信件。只可惜了当年那美好的情感。
多年后,她也曾遗憾的告诉我,如果早知道有一天,与他会天人永隔,或许当年不会那么绝决地烧掉所有的信笺。那样的话,再次展信阅读,看到他那虬劲的字迹时,或许,能想起的,依然是美好。
我在高中时期,一直收到姑父给我写的信。
姑姑和姑父在遥远的内蒙,很遗憾,我除了幼时见过姑父,长大后,一直未曾再见。高中时期的我,说不上很叛逆,但是总有一些与父母怄气或者闹别扭的时候。姑父给我的信并不夹在给爸爸的信件里,而是很正式的寄到学校,让我十分有自己已经长大成人被重视的感觉。
姑父在信件开头亲切地叫我“我的小公主”,让我时至今日都觉得被宠爱,在信的结尾庄重地落上他的名字,让少年的我觉得自己被平等对待。他给我讲塞外风情,讲草原民俗,也给我讲人生道理,波折起伏。他告诉我他和姑姑每到一地,都会给我买一件小礼物,要等到我出嫁的时候,一并郑重地交给我。
只可惜,他英年早逝,我终是没能等到收取所有礼物的那一刻。
姑父的字写得疏朗大气,如同他的眉眼。我总在想,除了父母给我的教导之外,姑父在我的高中时期,给我的教育更重要。如同他给我取的名字一样,教会我要有一颗坦荡阳光的内心,才能面对人生中所有的风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