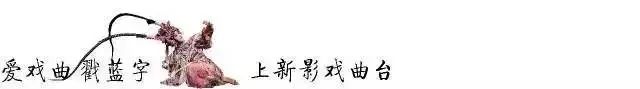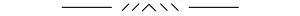王亚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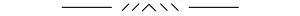
北京演艺集团艺委会副主任、一级作曲
蒲剧《樱桃花开》以自然平实、连贯流畅的风格,烘托出主要演员丰满的人物形象,英花自立自强的顽强性格令人敬佩。从创作的角度看,音乐的序曲应符合戏剧的风格和主题,在舞蹈动作上加入戏曲锣鼓点。序幕应更加简洁,不要过多渲染寿宴的喜庆氛围。舞美的设置很美,樱桃花代表了顽强自立的主人公英花,也映射了剧情的发展,但在不同场次中樱桃花应根据情节有浓有淡,有多有少,以符合情节的推进。再有,豆豆的年龄过小,与故事情节不符。第六场在主要矛盾已经抛出的情况下,女主角还在犹豫显得有些多余。人物关系上,英花冰清玉洁,爱上性格自私的梁冰,这种情感基础还不够充分。第七场英花与有良结合显得突兀,他们的感情应该在第四场有所铺垫,以符合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感情的推进。

王英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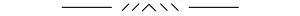
现代生活与革命题材的舞台呈现是不一样的。革命题材可以很自然地运用锣鼓经等程式,而现代生活题材则不然。蒲剧《樱桃花开》充分体现了导演对传统程式的驾驭能力。序幕一场,导演把流动的舞台处理得有条不紊;第二场中梁冰与英花的表演把传统的程式加以现代化。表演上,几位演员唱功不凡,英花的行腔吐字很到位,李父、李母、豆豆等角色都很有戏。尤其是四位“手机控”的婆姨,在剧中起到了调味剂的作用,让一出悲情大戏多了几分幽默与诙谐。第六场的设置有些拖沓,英花带公婆改嫁的态度在前几场已经表明,不需要再用一场的时间来表现左右为难的情绪;其次,英花是一个有骨气、有主意的女人,与梁冰及有良的感情过于草率。

张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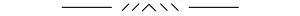
山西省各级领导对戏曲发展的重视,为蒲剧《樱桃花开》的成功演出注入了强心剂。该剧的服装很新颖,富有时代性,样式夸张却恰到好处,让人耳目一新。演员的表演十分精彩,主演声情并茂,唱腔穿透力强,恰到好处地抓住了人物的心理。饰演豆豆的小演员只有十岁,却很会演戏,一声“妈妈”,让人潸然泪下。戏曲的程式化不留痕迹地融入到现代戏作品中,如剧中偷拍、刷朋友圈和在樱桃园中打理樱桃,这些形体动作以戏曲的程式为基础,又富有现代感。四个婆姨的过场戏起到了陪衬主演和调节场次的作用。最后,衷心地祝愿蒲剧《樱桃花开》在不断打磨中更加完美,成为山西戏曲的一部精品。

陈友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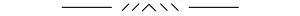
时事戏的难点在于内容的虚构和情节真实的调剂上,既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又要真正打动观众。《樱桃花开》主要是以情动人,主创人员敏锐地抓住“孝”的主题。中国人以“忠孝治天下”,“孝”的主题和英花对幸福的追求,紧密结合在一起,使英花作为一个现代女性,在剧中的形象十分完满。编剧、导演巧妙的构思,使场次的转换不留痕迹,情节紧凑。演员们十分投入的表演充分体现了王国维对戏曲的定义:“以歌舞演故事”,做到了“有声必歌,无动不舞”,给人一种审美的享受。除此之外,个别情节设置过于仓促,如最后一场,英花和有良的情感交集,需要在之前设置一些铺垫。

孔培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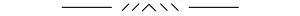
蒲剧《樱桃花开》有两点最为突出:其一,情节动人。剧本刻画了一个失去丈夫的农村女性,在自己命运陷入悲剧和绝望的境地时,没有选择逃离,而是坚持着一种近乎不可能实现的执念:带着公婆出嫁,让这个普通的女性身上闪现着动人的人性光辉。
其二,舞台唯美。导演调动一切技术手段实现了舞台二度呈现时的美感。剧中灯光被赋予了表达情感的功能,每一次切换都在讲述情节,蓝、红两种色彩的转换,正是悲喜的交替。舞美设计紧扣主题,镜框式的舞台大背景,既调节了樱花视觉的散乱,也代表着命运对主人公的束缚。音乐上,山西民歌主题曲虽然不断地变形,但浓烈的乡音乡情给观众带来了心理共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过场戏中的四个婆姨,她们推动着剧情发展的同时,也是村民的化身、舆论的化身、观众的化身。
全剧略嫌不足之处在于,英花带着公婆出嫁这一主要矛盾线条清晰,人物性格明确;而在英花对梁冰与有良爱情选择这一剧情线条上,英华的选择始终是被动的,看不到她明确的主动选择,因此,这一层面的人物性格塑造显得模糊。

王静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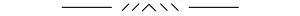
该剧情感细腻,唱腔优美,塑造了英花这样一个善良、孝顺的女性,由于坚持心底的善,最终得到了幸福的结局。在艺术形式上,导演有很高的追求:樱桃园劳动这场戏,真实、自然,有生活气息,身段好看。手机、照相机等新事物自然地登上了戏曲舞台,看得出导演有意创造程式,比如戏里婆姨们刷朋友圈的一段舞蹈。
另外,也对传统程式进行了创造性作用,比如英花妈看朋友圈时的甩头动作接近戏曲的甩发功。这样的舞台呈现,也有赖于团队的共同努力及演员的出色表现。戏改编自真人真事,带公婆改嫁虽然是孝顺的、充满人情味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行为也是突破常规的,说明英花非常勇敢。目前作品是苦情戏,英花是一位传统道德下的优秀女性,在孝道与追求个人幸福之间为难,仿佛只有依靠一位善良的男性才能解决困境,能否在凸显她的坚强、果决、自立、自主这方面多着笔墨,使其既具备传统女性美德,也具备现代女性意识。樱桃园劳动这场戏在展现她自立的方面已有基础,如能更进一步,则作品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