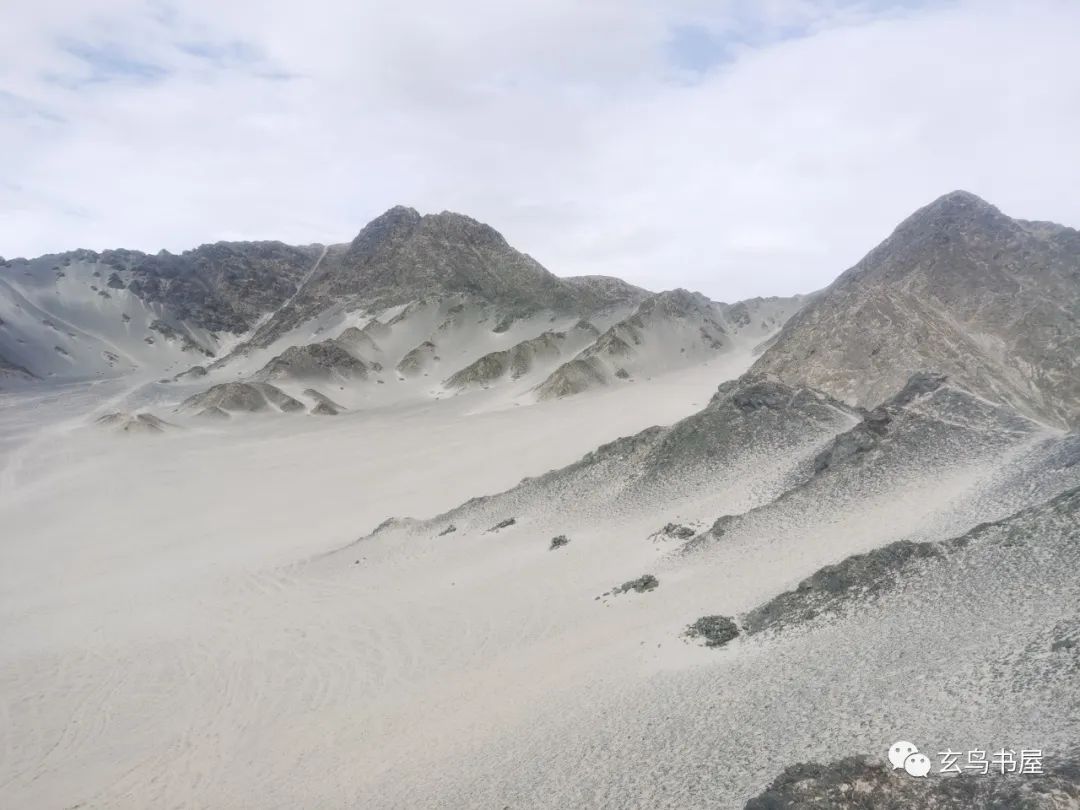
吕纬甫和魏连殳相当程度上就是曾经的鲁迅自己,或者说可能的自己,通过《在酒楼上》和《孤独者》这两篇小说,鲁迅自我精神分裂,进行了一番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在对自我处境经历的回顾和审视当中,他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自己的超越,并为自己之后的人生抉择和行动指明了方向。当然,这种审视和超越其实是并不彻底的。
废园象征:家园失落之存在处境
楼上
“空空如也”,任我拣得最好的座位;可以眺望楼下的废园。这园大概是不属于酒家的,我先前也曾眺望过许多回,有时也在雪天里。但现在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却很值得惊异了: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晴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如雾。……
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多次眺望的废园其实是故乡或
“精神家园”的象征。对于走出故乡,到外面世界接受了异质现代新文化的新知识人而言,故乡早已不是原来的故乡,精神家园早已荒芜,再也回不去了。“
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
这样的人生和精神的历程就是失去心灵故乡的过程,可是无家的处境是多么让人忧愁和伤感啊,漂泊的心灵又怎样才能得到安放呢!难道真如里尔克所言:
离开村子的人将永久漂泊
还有许多人会死在中途
而现实的处境则是社会政治黑暗腐败,此种现实给自己造成的内心感受就是如深冬雪意一般的寒冷。
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晴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
废园中这几老梅和山茶花,于废墟和严冬飞雪中展现出来的蓬勃顽强生命力的确让人惊异,此生命正来自于废墟中绽放生命的渴望和与黑暗压抑之非存在现实之对抗,显示出了极大的存在决心和勇气,乃是作者自我振作和坚持之精神人格之象征外化,其孤独和坚韧真有
“独钓寒江雪”之感。
掘坟:向死而在的死亡观
吕纬甫回故乡是为了完成两件母亲的心愿。其一是迁葬小兄弟的骨殖。
“我当时忽而很高兴,愿意掘一回坟……这些事我平生都没有经历过……我站在雪中,决然地指着他对土工说,‘掘开来!’”我实在是一个庸人,我这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稀奇,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但土工却毫不骇怪,就动手掘下去了。待到掘着圹穴,我便过去看,果然,棺木已经快要烂尽了,只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我的心颤动着,自去拔开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我想,这些都消尽了,向来听说最难烂的是头发,也许还有罢。我便伏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的看,也没有。踪影全无!”
我为何很高兴,愿意掘一回坟呢?为何
“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呢?因为这是对死亡也即“我到哪里去”的终极问题之探索,结果却是“什么也没有”,骨骼和最难烂的头发,“也没有。踪影全无!”我们知道,人死后埋在地里,骨骼和头发至少是可以保留上千年而不消失的,这里几十年之后就消失得踪影全无,显然不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事实,而是对死后的虚无认知之象征。人死后,肉体终归腐烂消散,回归大地,然后就什么也没有了,没有灵魂的永生,没有天堂地狱,没有轮回转世,彻底的虚无。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祝福》中祥林嫂的灵魂发问,亦即鲁迅潜意识之自问,在这里得到了确定的回答。然而此一回答有什么确切的依据吗?其实没有,但是按照鲁迅已经接受和信服了的科学唯物主义和经验实证主义形而上学,灵魂之存在既然无法证实,死后的世界谁也没有去过,那么无法被经验理性证实之认知当然就是不靠谱的妄想,迷信和自我欺骗了。其实,这种对科学理性的绝对真理性之信奉亦是一种现代迷信,跟祥林嫂之迷信并没有根本区别。迷信的对立面并非科学,而是正信,科学并非绝对真理,相反,缺乏反思而将自身绝对化的科学自身会成为迷信。
既然已经认为死后什么都没有,生命无法寄托于天堂和来世,那么此世的生存就成了朝向死亡之存在,意义只有在反抗虚无的当下行动中来获取,鲁迅自《狂人日记》之后的一系列文学写作,尤其最后十年的杂文写作,皆可看作以批判性话语直接介入并试图改变当下生存现实的行动。此种介入和改变与鲁迅自身生命意义问题关系重大。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鲁迅为何不专注于学术研究,不专心于所谓纯文学创作,而选择了在许多人看来不是很有价值的批判性的杂文写作。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
。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野草·题辞》
爱之死:顺从的悲剧
如果说掘坟意味着鲁迅对死亡之探索的话,那么顺姑的故事则意味着鲁迅对自身
“爱之死”的痛切反思。或许迄今为止也没有人意识到:顺姑某种意义上就是鲁迅自身,而她的悲剧源自于对包办婚姻这一非人道传统婚姻制度的顺从,取名“顺姑”之深意在此。
与朱安的婚姻给鲁迅造成了几乎终其一生的巨大痛苦和困扰。其问题的根源是他自己对传统婚姻制度的顺从,而顺从的原因则是是出于对母亲的
“孝”,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被母亲病重的谎言骗回来与朱安完婚,虽然极度痛苦,但却没有反抗,他自己后来的解释是“怕伤了母亲的心。”
同时还来自于对新伦理的顺从,如果按照旧伦理,弥补婚姻悲剧的办法还可是是纳妾,然而对接受了新伦理的新知识分子鲁迅来说,这是无法想象,更不可能付诸行动的。按照新伦理,鲁迅可以离婚,再恋爱结婚,然而自旧伦理看来,那不是离婚是休妻,这对活在旧伦理中的朱安来说无疑是毁灭性打击,故鲁迅不忍。所谓
“背着因袭的重担”,这重担既是现实的婚姻,是现实的人,也是传统的伦理。故鲁迅既顺母亲,顺从了包办婚姻传统伦理,又得“顺”一夫一妻制的新伦理,这是夹在新旧之间的,反叛不彻底,知行无法合一的鲁迅一代人特有的痛苦。
这桩无性无爱的婚姻给鲁迅造成了巨大的痛苦,既然
“顺”源自“孝”,悲剧的根源在于对母亲的安排,对传统的包办婚姻制度的顺从,那么走出无爱婚姻,摆脱痛苦的办法就是不再顺从。之后鲁迅能克服自身和社会的道德压力,走出接受许广平求爱这勇敢的一步,跟他这里对“顺从”之悲剧根源的反思是有绝大关系的。
鲁迅通过吕纬甫讲述的
“掘坟”和“顺姑之死”两个故事,完成了自身对生命存在之两大根本问题“爱与死”之反思。
生存问题:无力救己,如何救世
“模模胡胡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去。”
“你教的是‘子曰诗云’么?”我觉得奇异,便问。
“自然,你还以为教的是ABCD?”
如果对应于鲁迅自己,所谓
“教‘子曰诗云’”其实指的是辛亥革命后,他为了物质生存在袁世凯和段祺瑞时期的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的经历。
教
“子曰诗云”是不是就错,我们今天可以再讨论。但至少吕纬甫亦即鲁迅看来是没有意义而不愿意做的,但为了生存你还得做你反对的事情。那么这就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鲁迅这样的新知识分子多以救国救民救世为使命,但是如果连一己之生存都解决不了,你又谈何救世呢!你的救世方案又是否靠谱呢!至少必须具备不违背自己良心和理想价值观的方式解决自己生存的能力,然后才谈得上救世理想。
鲁迅后来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杂文写作,在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中顺便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样的天才,故生存依然是个问题。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要认清自己,如果没有那个能力,就不要有什么救世妄想。能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过好自己的生活,再顺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点社会责任,也就算不错了。
“子曰诗云”与“
ABCD
”:新真理的宏大叙事
鲁迅借把自身他者化为吕纬甫这么一个人物来返观自身的反思并不彻底,至少对自身追求之新真理是缺乏足够的批判反思的。比如,引进
“
ABCD
”所象征的西方现代文明,就完成这个文明和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而言,当然是核心的使命,但为何就一定要完全否定“子曰诗云”呢!就一定要去拆毁城隍庙的神像呢!吕纬甫当然不完全等同于鲁迅,然而,对吕纬甫身上的科学迷信,西学迷信,现代神话和进步神话,对在场形而上学,鲁迅是否有足够的警惕和反思,是否能够超越这种二元对立呢,这不能不是个问题。从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极端否定的态度来看,我们基本上可以说,他是没有超越的。
圆圈隐喻:三种意义上的圆圈和鲁迅的半圈
“我一回来,就想到我可笑。”他一手擎着烟卷,一只手扶着酒杯,似笑非笑地向我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和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这难说,大约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罢。”我也似笑非笑的说。“但是你为什么飞回来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