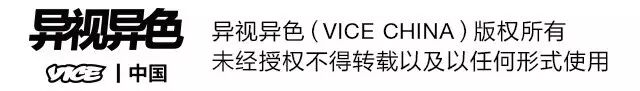热干面的英文名是 Hot Fuck Face
想知道这词儿是怎么来的吗?先看看下面这个视频:
HOW TO:AV大久保热干面



就像大部分老外提到中国只知道 “Beijing” 和 “Shanghai” 一样,有一个问题也困扰了我二十几年 —— 只要告诉大家我是湖北人,都会被默认为来自武汉。虽说不是地道的武汉人,也不居住在武汉,但我每到过年的时候还是得回武汉老家,跟操着一口武汉话、分不清到底是伯伯还是叔叔的亲戚们待上几天。小孩子最容易对不熟悉又走程序的东西感到抗拒,所以从小,我就对武汉这座城市感觉不友好。
高考完,班上80%同学都报考了武汉的学校,我以 “武汉太脏太破” 为由坚决拒绝了父母的要求,去了一千多公里外能看到蓝天白云的沿海城市。远离家乡的兴奋劲儿没维持多久,水土不服、语言不通、交友困难让我怀念起那个灰秃秃的地方。因为学校的湖北人实在太少,周围同学参加同乡会时,总有一种 “整个湖北省都没什么存在感” 的错觉。以至于但凡有人说出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都会自动把他列入知己名单中。

热干面和蛋花米酒是标配,旁边的武汉豆皮也是小吃之王
不过,思念家乡这种事儿,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咎于我的味蕾和胃。虽然在武汉待过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一年,但我吃过的热干面能绕武汉十圈。热干面不仅仅是湖北伢 “过早” 的一种选择,在高中阶段,它几乎也可以占据我 “过午”、“过晚” 的宝贵时间。哪怕曾经亲眼看到老板的猫悠闲地从摊在桌子的面条上踏过去,我们也依然保持对热干面忠贞不渝的爱,配合一碗蛋花米酒,淡定地在眼镜被热气熏上白雾时确保每一根面条都均匀地拌上了芝麻酱。
上大学之后,我愿意坐两小时的公交车去吃一碗正宗的热干面,因为食堂做的从来不放酸豆角和辣萝卜。宿舍里永远放着网购来的 “大汉口”,干拌面似的口感竟然征服了不少室友 —— 当然也有例外,有人坚决不吃热干面的理由是 “吃完面擦嘴感觉像刚吃完屎。”

伦敦中国超市的“大汉口” 0.95镑(8.2 rmb)一包
后来,离家的距离更远了。异国他乡,凡是遇到湖北人,“要不要一起去搞一碗热干面” 一定是搭讪的首选。不过这个套路在我第一次吃到用意大利面代替碱面的热干面之后就放弃了。但是不得不承认,当越来越多的人把星座和美食当成永恒的话题时,“热干面” 曾经无数次拯救了我的社恐症。
我对热干面的欲罢不能让不少人爱上了这种 “看上去很恶心” 的食物,却没有办法改变他们对武汉这座城市的看法。很多人拒绝我的邀请,因为害怕在武汉被公交司机骂、被卖面大妈骂,被城管骂、被一切可能得罪的路人骂。当然这种误解也赖我,湖北人如热干面一般 “速战速决” 的暴脾气总能在我身上完美地体现出来。
然而,“躁” 在我眼里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有些东西,只有在 “燥” 的坏境下才能被淋漓尽致地表达。内陆城市中,武汉的 “躁” 给像我一样不愿意安分守己、喜欢瞎几把折腾的年轻人来说,提供了一个无比包容的环境。这个想法是在我看到武汉一辆接一辆的涂鸦公交车时产生的。

去年,武汉27KM的街头艺术团队成员在武汉公交车上创作涂鸦

武汉公交车上的热干面 (图片由 Superen 提供)
武汉的大学很多,带来了一大批年轻人。再加上自古码头文化,南来北往,武汉人向来不拒绝新鲜玩意儿,这大概也是武汉市民喜欢围观凑热闹的原因之一。玩涂鸦的武汉朋友 Ray 就告诉我,在他做涂鸦时,总会有人跑来跟他聊天,有老人有年轻人,甚至经常有妈妈带着小孩在一旁边看边夸,“如果在其他城市,估计都报警了,武汉的包容才是新型文化最需要的软环境。”
因为喜欢在晚上骑车刷街或者 bombing,Ray 通常把热干面当晚饭,炸几条街之后,坐在江边吃才叫爽。Ray 小时候曾经跟家人拌嘴赌气离家出走,当时身上只有两块钱,彻夜骑车从青山到汉口,凌晨在广场和流浪汉为伴睡在长凳上。第二天累死街头之前买了一碗热干面,那是他一辈子吃到的最香的热干面,吃完就回家了。

武汉江边的涂鸦作品
在武汉这座城市离家出走可不是一个好选择,因为武汉真的太大了。武昌、汉口、汉阳,每个镇都有各自的中心,再加上长江和汉水分割了最市中心的地段,没有江底隧道和过江地铁之前,从一个镇到达另一个镇简直像短途旅行一样费劲。
Ray 已经做了十几年涂鸦,在国内算得上骨灰级 writer。说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经历是在2014年,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刚过去的时候。Ray 因为在武汉地铁2号线签 tag 被一些人当作恐怖分子暗号而报了警,差点儿被关进局子。不过最后,在刑警队长的交涉下,Ray 依照地铁条例只交了300块钱罚款就了事了。“销案后刑警队长掏出手机给我看了他和他老婆在古琴台涂鸦前的结婚照,我真的很感谢这些办案的警察,但那之后我就下决心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涂鸦,避免这些误会。”

Ray和他的涂鸦作品
几年前,可能每一个来过武汉的外地人对武汉最大的印象就是蓝色工地围挡,24小时洗马路的洒水车和永远修不好的路,但如今武汉大片的涂鸦墙已经成为了旅游景点。在 Ray 看来,涂鸦和 hip-hop 文化一脉相承,随着不同阶级、文化背景、性格爱好的人加入,涂鸦的核心精神已经越来越模糊,文化本身也变得多元化。“所以涂鸦发展到现在就应该包容,不要自己做这个流派就瞧不起其他流派的涂鸦作者。这一点上来看跟武汉的气场是非常吻合的。”
因为武汉的包容,Ray 可以在内环的长江边支起烧烤炉和帐篷,边游泳边钓鱼边涂鸦,盘街的奶奶会帮他赶走烧纸钱的人防止墙上的涂鸦作品被烧黑,没上过大学的他会被大学老师邀请把涂鸦课堂开在湖北美院壁画系。在武汉,Ray 和政府官员,跨国机构的老板成了朋友,也和涂鸦墙附近的流浪汉成了朋友。

“老汉口”涂鸦
按照 Ray 的说法,以涂鸦为代表的武汉亚文化发展得越来越好,但武汉朋克乐队 SMZB 的主唱吴维却觉得武汉的亚文化整体都越来越不好,就跟他现在住的地方周围的热干面一样 —— 做得越来越不好吃了。
“初中时家附近有一个叫三毛的人做的热干面很好吃,每天早上都是周围的邻居街坊去吃,人很多,所以经常要排队。有一次一个当地的片警看到很多人排队,就走到正在下面的三毛旁边叫他先给自己做一碗面,排队的街坊邻居都没说话,三毛一边烫着面,斜眼看了片警一眼后说了三个字 ‘排队去’,片警无奈地乖乖去排队了,其它人都笑了。”
只是现在,这些独立和反抗的精神都没有了。吴维眼中的武汉,各方面的特色越来越少,老字号店铺大部分都没了,变得和其他大城市越来越相似。《大武汉》这首歌是吴维写给1949年前的武汉,“她会得到自由,她会变得美丽,这里不会永远像一个监狱。”

吴维(左三)和他的SMZB
对于武汉城市的整体印象,除了 “超大” 之外,最吸引吴维的只有鲁磨路 —— 这里是武汉的独立文化中心,也就是为什么他选择把 Wuhan Prison 酒吧开在这里作为根据地。
不管是因为武汉天气 “燥” 还是武汉人性子 “躁”,武汉的年轻人可以整夜整夜在 VOX 酒吧疯狂嘶吼呐喊。1996年成立的生命之饼(后改名为 SMZB )是武汉第一只朋克乐队,也是中国最早的朋克乐队之一。成员来来走走,只有吴维和鼓手胡鹃留下。曾经,武汉朋克发源于生命之饼,而武汉也被称作中国的 “朋克之都”。去年是 SMZB 成立二十周年,这二十年里,武汉的朋克经历了什么,现在最朋克的地方在哪里,吴维回答我说,“就是只剩我们一只朋克乐队了。”

位于鲁磨路的 Wuhan Prison 酒吧 (图片来自 Wuhan Prison 官方微博)
因为生活、工作的原因,或者对朋克的热情减少,不少武汉的朋克乐队解散。《大武汉》里的 “反抗、争取” 可能在吴维开始做音乐之前就已经没有了。吴维说他不喜欢武汉,想离开但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
有人想离开,也有人想留下。比如马东杰,跟我来自一个城市,跟他认识二十年了,每一次见面还是会提到小学四年级他把一碗热干面扣别人脑袋上的光荣事迹。那时候热干面只要五毛钱,但是管饱一整天,所以每次想到趴在别人脑门上像蚯蚓一样的面条时,我仍觉得心疼。
2011年之前,东子只去过一次武汉。跟我80%的同学一样,因为离家近、学校多,高考完他报考了武汉的大学,“那时候武汉车多、人多、灰尘多,但是空气质量还不错,不像现在只能看清10米以内的东西。”
如今的东子是在酒吧会被粉丝认出的街舞新秀,去年他在武汉开了一家街舞培训机构,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正式把街舞作为自己的事业,“我的目的只是想让更多人知道街舞,融入其中,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
东子在上大学之后结识了很多跳街舞的朋友,但是慢慢发现有些人再也见不到了,大部分都去忙别的事情。东子也面临过工作还是跳舞的抉择,但最终选择了后者,他还是想把更多的事件放在舞蹈上。只不过很怀念跟大家一起练舞的日子,“练完后大家去吃宵夜,周边就只有一个面馆,只能吃热干面,但是蛮好吃。你能想象五个人吃了200多块钱的热干面吗?之后的几个星期都没再碰过面食。”

去年,ThugLife Wars Vol.12在武汉打响 “末日之战 ”
东子形容身边的武汉人聪明、重情义、讲胃口(武汉话)、充满正义感、拐。就像武汉发布的官方精神一样 —— 追求卓越,敢为人先。但是这一点不仅在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身上又体现,在包括他在内的外来90后人口中都是存在的,尤其是对于跳街舞的人来说。
虽然搬到了武汉,东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各个城市参加比赛或者担任裁判。每次回到武汉,都觉得这座城市有新的变化,尤其是这两年发展得太快了。“骂街的少了,文明了很多。” 不过最大的变化是武汉跳街舞的小孩子多起来,东子不再是家长眼中的 “小混混”,他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带着自己培养出来的孩子一起去参加比赛。

马东杰在 “末日之战” 上夺冠
上一次见东子是大三暑假,我的本科毕业作品是关于青少年街舞的发展,第一站就选择了武汉。作为一个内陆城市,虽然信息和资源都没有北上广那样发达,但也已经进入了中国领头的位置。东子经常代表武汉参加比赛,“总有人说,‘哇,武汉的街舞很强,宣传也很好。’ 我听到这话当然高兴了。” 东子把自己看作半个武汉人,因为这里的街舞氛围,让他融入得太快了。
我去了东子的舞房,十几个男生脖子上挂着毛巾,接近40度的天气,一练就是一下午。除了在武汉本地,他们也会去不同的城市参加比赛。跳街舞的人越来越多,但冠军永远只有一个,哪怕竞争这么激烈,不少人在海选时就会被淘汰,湖北伢也只会抱怨一句 “个斑马” 之后就在舞台边上跟着音乐接着 pop 起来。

马东杰代表武汉参加上海 BIS 国际街舞大赛夺冠
东子问我在北京过得怎么样,我跟他抱怨在这儿吃了一碗30块的热干面。“个婊,没有螃蟹还卖这么贵?” 他告诉我现在武汉的热干面已经不得了了,除了最传统的几种,还发明出了蟹脚面、鲜虾面、鲍鱼面......我突然意识到,武汉于我,恐怕早已不仅仅是靠绕其十圈的热干面连接在一起。当我发现这座很 “躁” 的城市如此包容我所热爱的东西,哪怕别人对她有误解,哪怕她还有很多不足,至少我对她的不友好正在慢慢变得友好。

更重要的是,蟹脚热干面看起来真的很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