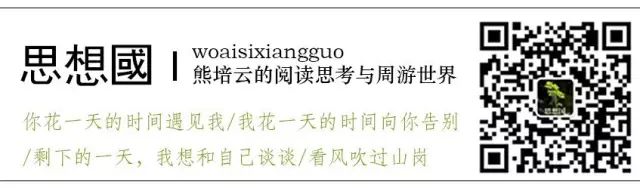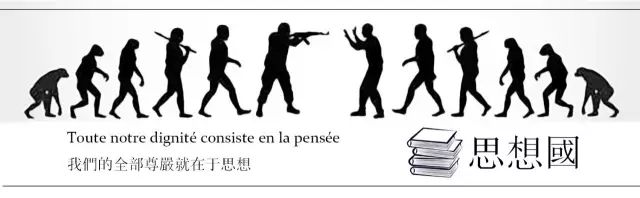

盼了一天的暴雨,到现在也没有下来,只是偶尔听到一点雷声。
前两天写了几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有读者在微信上留言:
“鲁迅的作品里只读他的小说,因为没有看到恨,只看到了慈悲。比如成年闰土的形象让我心酸;比如尤其喜欢的那篇《在酒楼上》,简直太不‘鲁迅’了。人,是有多面性的。文学的功效也有多种,或武器或安慰剂,普通读者各取所需……无论别人吹捧他还是批判他,我早已自动屏蔽掉了他所谓思想家、革命家的面目,只遇见自己喜爱的文学的鲁迅。”
由于当时匆忙,我只简单回了一句,大意是鲁迅的文学作品里是有慈悲的,但是他没有回到人的普遍意义上。只有阶级意识,他的慈悲就是不完整的。而这点在雨果和加缪那里或许有更好的答案。
上述读者的留言为我解释了很多人热爱鲁迅的另一个视角。一个人爱一个偶像,其实也只是爱其中的一部分,并不需要完美的形象。但人往往也真是奇怪,虽然并不要求鲁迅完美,但当你批评鲁迅时,他们又认定你破坏了心中的完美形象。也就是说这种完美形象是在有人批评鲁迅时在他们心中瞬间生成的。
当然,如有些读者所见,我现在批评鲁迅,也不是整体性否定他。对于文学的鲁迅,我自然是尊重的。我没有徐志摩的那种偏见,认为鲁迅的作品完全看不下去。比如说《阿Q正传》,我便觉得不错。这可能也和我偏爱隐喻式作品有关。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作品一经完成,通常就不受作者控制了。我觉得《阿Q正传》还不错,但并不喜欢鲁迅对它的解释,诸如刻画“国民性”云云。我素来以为,如果只是将阿Q及其精神胜利法当作嘲讽中国人的手段,这小说就是失败的,而且,对阿Q也不公正。因为精神胜利法既非阿Q所独有,也非中国人所独有,而是全人类共有。
我既已断言人是意义动物,那么人在逆境当中为自己的生活赋予某种积极意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这也是人们在社会心理学中常常谈到的自我补偿(compensation)。比如在弗洛伊德那里,被理解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这是指自我对本我的压抑,这种压抑是自我的一种全然潜意识的自我防御功能,是人类为了免除精神上的痛苦、紧张、焦虑、尴尬、罪恶感等心理,有意无意间进行的心理调适。比如,酸葡萄心理(把得不到的东西说成是不好的)、甜柠檬心理(如果手里只有柠檬,就说柠檬是甜的)以及幻想(Fantasy)等等。当一个人遇到现实困难而无力应付时,就利用幻想的方法使自己获得某种心理上平衡。这既能让相对弱小者获得某种自尊,也会增加他的安全感。
近百年前,奥尔特加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特别谈到这种心理。“大凡身体孱弱的人,都把理智生活看做是一种伟大的事情,以为哲学家的生活高过普通群众的生活无限倍。有一种蹉跎半生的人,总以为他们是‘穷而不滥’的人,那意思就是说,一有了钱,钱便染上不正的颜色。大凡身体有缺点的人,往往生出极有趣的理由化的现象来。”阿Q造出与赵太爷是本家,和中国人说自己是炎黄子孙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在伟大的人或者事物上附着意义。而这种虚荣也不是中国人所独有。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自豪,每个国家都大有人在。
对于这些内容,我个人觉得只要没有破坏群己权界,这种所谓的精神胜利法是无害的。我想起启蒙派知识分子的自傲。当他们群起嘲笑其他人愚蠢,合理化自己的进步事业之时,是不是也有些精神胜利法的意味呢?鲁迅在《俄文译本序》中说阿Q是为了画出沉默的中国人的灵魂,而事实上阿Q精神乃人类共有之特性。在此意义上,鲁迅的这篇小说是超国界与超阶级的。只是鲁迅自己可能并不买账,尤其是二、三十年代他彻底向左转,并且否定了“第三种人”的文学以后。
同样有趣的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许多人不得不为把阿Q的这种精神胜利法该归类于哪个阶级而感到苦恼。有人声称,无产阶级是没有这种坏毛病的,如果有的话,那也是资产阶级、统治阶级长期驯服的结果,所以这种精神胜利法本不属于阿Q,而是属于资本阶级。当说,这种想法,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以上是我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理解。接下来我说一说鲁迅的胜利法。
先引用《两地书》里的一段内容(实话说,在《鲁迅全集》里我最爱看的是许广平的文字)。
鲁迅在回许广平的信中说,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两大难关,一是歧路,二是穷途。如果遇到歧路怎么办呢?鲁迅说他自己不会像墨子一样恸哭而返,而是——“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
这的确是战士的鲁迅、赞美斯巴达的鲁迅、睚眦必报的鲁迅、爱憎分明的鲁迅。但是,在这段话里,爱却是没有的。否则为什么要夺老实人的食物呢?这是人性的幽暗吗?我这样说,有的读者也许会认为我咬文嚼字,太过苛刻了。
当然,没有人需要以身饲虎。但这段文字还是让我不由自主想起了胡适改写《西游记》,唐僧取经回来在天上割肉度群魔的章节。在胡适的那些文字里,我是真的读出了菩萨心肠。然而,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在鲁迅的小说里虽然有慈悲,但是在他与人论战的时候,求胜心似乎压倒了一切。当他以梁实秋“构陷”他的名义痛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时候,他其实也同样构陷过胡适。
1933年3月26日的《申报•自由谈》发表了一篇署名何家干的鲁迅的文章。标题是《出卖灵魂的秘诀》。胡适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说了一句“日本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而鲁迅却抓住这么一句话,将胡适骂成“日本的军师”,说他是在给日本人上条陈,出卖自己灵魂。
彻头彻尾的断章取义。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胡适有感于中日之间的仇恨日深,正好日人室伏高信发表文章批评中国搞“以夷制夷”,不奉行“中日亲善”,于是胡适连写了三篇文章作了回应。胡适认为在日本铁拳的压制下中日断无亲善可讲。如果日本想要亲善,征服中国人的心(获得中国人的友谊,不去仇恨日本),那么就应该结束武人专政,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胡适警告日本侵略中国,实际是带着日本人走上全体自杀的道路。
透过所有这些文字,我怎么也不明白有文豪之称的鲁迅会将胡适视为日本“陛下的臣子”。就事实而言,胡适很早就在日记中提到要警惕日本的侵略,待二战爆发,若不是胡适在美国积极斡旋,促成美国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卷入太平洋战争,中国战场究竟会打成怎样,蒋介石是否守得住重庆,就真不好说了。
我读二十世纪中国一些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文章,常常难免痛心。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曾有些文字让我击节赞叹。毛泽东早期文稿,鲁迅写在1907年前后的几篇论文,我在其中读得到满腔的赤诚。而一旦卷入斗争,有了一定的权力、地位和所属的社团,有了具体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对象,则纷纷变得陌生了。
鲁迅早期是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曾是人道主义者。他怀疑民主,警惕多数人的暴政,这无可非议。直至今天,就是在西方世界,也有很多关于对民主的质疑。鲁迅的小说里当然是有人道主义的。只是到了三十年代,当鲁迅慢慢成为多数人中的一员,人道主义似乎又被他抛到了脑后。
说到这里,我先讲讲前面提到的雨果和加缪。
雨果反对暴政,理解法国大革命,到了他那个时代甚至还为反对独裁用自己的稿费捐了一口雨果大炮,但是雨果并不赞美暴力。有两个细节尤其值得一提:一是他通过小说《九三年》表达了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东西,即人道主义。二是巴黎公社革命中,当巴黎公社试图以三比一的杀戮来对抗政府时,雨果通过一首诗表达了他的抗议,以表达自己奉行人道主义的决心。雨果说:
“被我所击败的人,我不会拳打脚踢。我以自己的权利去衡量他们的权利。如果我看到敌人被绑,我自己不感到自由。如果我把敌人的做法去还敬敌人,我也要请求他的饶恕,把膝盖磨破三分。”
这是雨果和他一生践行的人道主义。
接下来说加缪。加缪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迷失。但是后来他醒悟过来了,很快意识到问题。当他的论敌,萨特及其支持者梅洛•庞蒂滔滔不绝地对他说“暴力是政治所固有的,因此共产主义的暴力要优于资本主义,因为它至少承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时,加缪的反驳是,“任何属于集中营的,哪怕是社会主义的,都必须称之为集中营。”加缪无法容忍一种荒诞的事实,一边是四海皆兄弟,一边又在大张旗鼓地杀人。
这是加缪和他努力做到的明辨是非。
然而,抱团站稳了苏俄的立场后,鲁迅的人道主义到哪里去了呢?二十年代以“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反对林语堂的公平竞争与宽恕论,而在彻底奉行了阶级斗争理论之后,鲁迅的人道主义似乎完全让位于“同道主义”了。简单说,此时的鲁迅有怜悯,但不是放在普遍的人的意义之上,而只向眼泪洒向同一战壕的人。而这些人,有时候也只是抽象意义上的工农二字。至于具体的人,则“一个也不宽恕”。
而那时候也的确是个混乱的年代,就像我们在今天时常看到的。鲁迅同样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甚至恶语中伤。比如因为对文学的立场并不完全相同,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萨特曾经说,“杀死一个欧洲人,这是一举两得,即同时清除了一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当年的中国人似乎也可以用类似的句子来针对自己及他同时代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有过一段有关革命与人道主义的争论。和雨果不同的是,鲁迅在他的文章中公开鄙夷人道主义。1933年,在《“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中,鲁迅写到,“对于慈善者,人道主义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们不过用同情或财力,买得心的平安。这自然是对的。但倘非战士,而只劫取这一个理由来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买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钱的买卖。”
这样的说辞,我第一次读到它时已觉毛骨悚然。因为鲁迅不只是否定了人道主义,甚至也否定了“非战士”。如果不站在他一边就是冷酷的,接下来的问题是,个体没有不参加革命的自由吗?鲁迅的这番说辞,和罗伯斯庇尔时代的“你不要自由,我强迫你自由”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而对于人道主义,鲁迅不只是给予了否定,还加上了自己的诅咒。
《解放了的堂•吉诃德》是由瞿秋白译介的卢那察尔斯基的戏剧,讲述的故事是在革命之前,堂•吉诃德出于人道主义立场救出了革命者。然而当革命者大权在握,专制者入了牢狱,这位人道主义者又对这些新的被压迫者表达了同情,并希望结束新的压迫。在鲁迅看来,堂•吉诃德是愚蠢的,因为这样的人道主义者只会被奸人利用,帮着使世界继续留在黑暗中,他放蛇归壑,使敌人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在这些说辞里,阶级性彻底压倒了人性。
我不知道,在戏剧之外,在中国二十世纪的若干场革命当中,对于那些被革命侮辱与损害的人,那些被打倒的地主和资本家,鲁迅是否会为他们流下一滴同情的泪水。
在《解放了的堂•吉诃德》中,实施革命专制的德里戈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你看这把剑——看见罢?——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对此,鲁迅不但没有任何质疑,反而为指责像剧中堂•吉诃德一样行事的托尔斯泰派、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人非议当年革命的残暴,帮助反动派出国与安身——犯了和堂•吉诃德式的错误。
而鲁迅1930年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给我的印象是他已不再是个作家,而是一个指导作家冲锋陷阵的军官。如果从前他还信奉个人主义,而现在完全是另一幅模样。
站定了立场后,鲁迅能否接受新的批评?在《林克多序》中,鲁迅指责时人对苏联的批评,说“中国人实在有一点小毛病,就是不爱听别国的好处,尤其是清党之后,提起那日有建设的苏联。”鲁迅赞美苏联的革命,将资本家与地主视为敌人。他相信在苏联“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要先好利来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
鲁迅赞美的苏联是这样的——“那就是将‘宗教,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任何关于苏联的批评,在鲁迅那里,都是带有恶意的。“他们是大骗子,他们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
而在1932年写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中,鲁迅也一再强调,“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还来对我们说苏联怎么不好,好像它倒愿意苏联一下子就变成天堂,人们个个享福。现在竟这样子了,它失望了,不舒服了。——这真是恶鬼的眼泪。”
同样是在这篇文章中,为了论证帝国主义的害处,鲁迅用了“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的逻辑。“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
许多人为鲁迅的《战士和苍蝇》叫好。实话说,我读到这篇文章时感觉并不好。战士为什么不能被批评?批评者又如何该被矮化为苍蝇?
还是前面那句话,人若是进入战斗状态,理智就会慢慢丧失。
否则,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逻辑呢?在这里,我看到的不是守卫某种价值观,也不是守卫自己的理性,而只是守卫自己的爱憎以及附着其上的观点。
如我前面说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是限于己域,于人无害,而鲁迅的胜利法,则将中国人的时代理性越推越远。
为什么知识分子会狂热地痴迷于一种意识形态?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有很好的解释。在这本书里,阿隆看到了狂热的政治信仰给知识分子带来的虚妄,同时振聋发聩地指出——右派与左派,或者说法西斯伪右派和苏联伪左派难道没有在极权主义中相汇合吗?而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如同过去的所有革命一样,只是由一个精英集团通过暴力取代另一个精英集团。这样的革命并未呈现出任何非同寻常的特征,能使人借此欢呼“史前史的结束”。
这里我还要说另一本书,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班达认为知识分子的知性在于提供三种东西,即正义、真实和理性。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活动本质不追求实践目的,只希望在艺术的、科学的或形而上学沉思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简单说,他们旨在拥有非现世的善,即人类的普遍的价值。作为一种知性的存在,当他们盲目地听从政治的激情,漂浮于时代的巨流,最后就难免背弃知识分子的责任,取而代之的是革命战士的冲锋陷阵。
这样的时代是有诸葛亮而无知识分子。真理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战胜远在天边的敌人。就像巴雷斯所宣称的,“即使祖国错了,也一定要把它说成有理。”
“在今日的欧洲,已沒有一顆心灵不被种族的激情、阶级的激情或民族国家的激情所感染,而且常常是被这三种激情同时感染……即使在拥有庞大人口的远东,看上去似乎与这些运动无关,也产生了旨在羞辱他人的社会仇恨、政党精神和民族精神。政治激情在今天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普遍性。”
《知识分子的背叛》写于1927年,这也是班达对他所处的时代提出的最严重的警告。而它对于今天的世界与今天的中国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
法国真正走出大革命,和其后几代知识分子的反思是不分开的。回到今日中国现实,以我目力所及,有关中国革命的反思还远远不够。前面我谈到,决定一个国家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不是草根阶层的素质,而是精英阶层的素质。等我有了时间,我会在后面的文章里展开来谈。
至于这篇文章,就先写到这里吧。如果需要一个总结,那就是相较于鲁迅胜利法,我更喜欢阿Q胜利法。我不忍心去批评阿Q,,是我对自己的慈悲,而我忍不住去批评鲁迅,则是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将鲁迅那一代人所丢掉的慈悲捡起来。当然,这也是一种虚妄,一种精神胜利法。
| 阅 读 更 多 文 章
如何保持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 熊培云
再说几句鲁迅,今天的荒芜就比较完整了 | 熊培云
一个不道德的死胖子——鲁迅的逻辑 | 熊培云
也叹中华文化之花果飘零 | 熊培云
疏远谁也不要疏远自己,只有他会陪你度过一生 | 熊培云
每天向每天告别。不在蠢事上浪费时间 | 熊培云
《夜空中最亮的星》,无望到底的热泪盈眶 | 熊培云
此心安处,庙不可言 | 熊培云
巨兽N——为什么他们热衷群体作恶?| 熊培云
如果救母者被判无期,当年为何要抗日?| 熊培云
因为无法改变,索性一事无成 | 熊培云
当痛苦不期而至,如何理解《海边的曼彻斯特》| 熊培云
走在分水岭上的世界 | 熊培云
琥珀社会,城堡落成:向上是水泥,向下是沼泽 | 熊培云
正在溃散的又一次玫瑰之约 | 熊培云
我前半生的世界蒸蒸日上,我后半生的世界摇摇欲坠 | 熊培云
中国超稳定结构:有不公,为什么没有大动荡? | 熊培云
消散的一切又在心头凝结——新年致读者 | 熊培云
我担心的不是曹德旺跑了,而是整个精英阶层的消散 | 熊培云
愛是我生命里所有卑微的時辰 | 熊培云
射杀希特勒,二十年后的世界依旧腥风血雨 | 熊培云